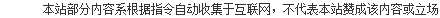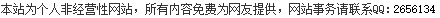中原有没有荒漠屠夫和沙漠死神,或者沙漠什么的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08-07 14:11
时间:2015-08-07 14:11
沙漠有没有什么特有的生物有哪些?_百度作业帮
沙漠有没有什么特有的生物有哪些?
沙漠有没有什么特有的生物有哪些?
不同的沙漠有不同的生物,生活沙漠的动植物一般都有抗旱耐高温的特点.温带沙漠的胡杨,骆驼刺是比较典型的植物热带沙漠的枣椰树是比较典型的植物典型的动物是骆驼(热带双峰,温带单峰)这些生物一般都生存在沙漠中,可以看做为特有的.鸵鸟,&响尾蛇,角蝮蛇,沙蛇,眼镜蛇,唾蛇、蜥蜴,蝎子,跳鼠沙漠里一些小动物都具有耐旱的生理特点.它们不需要喝水,能直接从植物体中取得水分和依靠特殊的代谢方式,获得所需水分,并在减少水分的消耗方面有一系列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它们营穴居生活,保护自己避免一切侵害;在洞穴里,可以躲避敌人、避暑和在无饲期间蛰伏不食.&过穴居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典型的代表为跳鼠,其中最常见的是三趾跳鼠和五趾跳鼠.它们喜欢在沙丘上挖洞居住,所以又有“沙跳”之称.体长约130~140毫米,共同的特点是后肢特长,足底有硬毛垫,适于在沙地上迅速跳跃,在风沙中也能一跃达60~180厘米.前肢极小,仅用于摄食和掘挖,而不用于奔跑.尾巴一般极长,有些种类的跳鼠尾巴末端有扁平的长毛束,就像“舵”一样,能在跳跃中平衡身体、把握方向.它们的头与兔子极其相似,耳朵很长,鼓室泡很大(利于听觉),眼睛也大.这些特点能够使它们顺利地在夜间作长距离的跳跃.由于沙漠中植物稀疏,并多为灌木而多刺,在这样的环境中,跳鼠主要以植物种子和昆虫为食.食物条件的限制,促使跳鼠营非群聚生活,夜间出来活动,长距离地觅找食物,有时一晚可以奔跳10公里之远.夜间,在沙丘的灌木、半灌木丛中,用灯光照射,就会很容易发现跳鼠的频繁活动,跳鼠的明亮眼睛在窥视着你,或者在你面前很快地跳过,使人感到沙丘戈壁的确是跳鼠的乐园.漫长的冬季,它们则以蛰眠而渡过.跳鼠是沙漠景观所产生的具有特殊生物形态的动物,能够与骆驼媲美.&作为沙漠中穴居动物代表的啮齿类动物,还有多种沙鼠:子午沙鼠、长爪沙鼠、柽柳沙鼠、大沙鼠等,它们均营群居生活,全年活动,但冬季活动减弱,以贮存饲料为生.大沙鼠体长超过150毫米,耳短小,耳长不到后足的一半.后足掌密毛,尾粗大,几乎接近体长.主要生活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荒漠和半荒漠的灌木琐琐丛生的沙丘和沙土地,食琐琐的肉质、多汁的叶子;有惊人的筑洞能力,洞群往往连成一片,洞道密集,能贯穿整个沙丘或地面.长爪沙鼠与子午沙鼠栖息范围较大,亦常见于干草原地带的沙地.&上述啮齿类动物大都具有沙黄的体色,便于在沙漠中掩蔽.即使在夜间活动,它们这种与背景相同的体色也是有利的.水源的缺乏使它们都有依赖植物中汁液维持身体水分代谢的特性.&沙漠里的小动物,除穴居的啮齿类外,还有一些小的爬行类动物.最多的是沙蜥和麻蜥,特别是在沙丘地带,甚至每走几步就可碰见一个.沙丘上的许多小而偏的开口,就是它们的洞穴.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应沙漠环境的能力.它们的身上没有汗腺,在各种高温环境下,都不会出汗;眼睛具有防风的眼帘;遇烈日,它们还会爬上灌丛以躲避沙面难忍的炎热.这些沙栖蜥蜴(俗名“沙和尚”)在沙地上活动非常敏捷,遇敌可潜沙而遁.
那如果这些生物离开沙漠会怎么样?
他们也能生存,但是没有在沙漠中生存的好,因为每种生物都有自己适宜的生存环境。就像在北方种柑橘一样,能种出来,但口感不好
骆驼,鸵鸟, 响尾蛇,角蝮蛇,沙蛇,眼镜蛇,唾蛇,、蜥蜴,蝎子,跳鼠 沙漠里一些小动物都具有耐旱的生理特点。它们不需要喝水,能直接从植物体中取得水分和依靠特殊的代谢方式,获得所需水分,并在减少水分的消耗方面有一系列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它们营穴居生活,保护自己避免一切侵害;在洞穴里,可以躲避敌人、避暑和在无饲期间蛰伏不食。 过穴居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典型的代表为跳鼠,其中最常见的是三趾跳鼠...
唾蛇 好像没有了从沙漠开始的道路(五则)&&&&&&&&&&
发布者:&|&
浏览(5152) 评论
&|&发布时间: 12:46:42&最后更新时间: 12:46:42
本作品所属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五则) 杨献平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 多年来,就这么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沿着可以走的道路,缓慢或者急速地走。四周都是风景,都是人,我看到的,没有看到的,看到我的,没有看到我的,那些路,路上的事物久长或者短暂,我相信它们并不取决于路过的某个人。某一天,我突然感到沮丧:这么多年,走了那么多的路,但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母亲相比,我的这些路仍旧是短暂的。 据我所知:母亲走过的大致有这么一些:去过3次100多公里外的邢台市和沙河市,还有山西左权的拐儿镇;再就是来过2次西北(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剩下的,她的路限定在村庄向北30公里的路罗镇、向东的乡政府所在地和派出所大院,向南是20公里的南山,向西到武安的阳鄄乡。范围再小:最远就是五里外的石盆村、三里外的自留地和后山的果树下了。 母亲就这样反复走着,脚下的路短暂而又漫长。她走的时候:身上还扛着或提着锄头、镰刀、粮食、清水等等一类的东西。记得她来我这里时,第一次带了1000元钱、10斤小米、一双自己做的布鞋;第二次是冬天:带了小米20斤、柿饼10斤、还有给她孙子做的2双布鞋和一身衣服。 我也一直走着,跟在她身后;她走过的那些,在我长大成人或者还在襁褓中,也断断续续地走过了。到西北,在巴丹吉林沙漠,我的最初是安静的,最远就是往返老家。后来,去更多的远处,携带皮箱、礼品、眼镜、书籍、手表和手机,还有各式各样的心情。还有一个区别是:母亲走远路带的钱总是不超过1000元,我呢,每次,至少也要多她两倍以上。母亲只有一次一个人走远路(含返回),我至少20余次(并不包括以后)。 我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到处都是戈壁,附近的村庄始终在炊烟、绿树、枯树和土尘之中。我时常站在营门前(偶尔坐在班车上),看见异地的村庄。它们的隐藏和浮现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心理的效应。唯一记得的有3件事情。一是在单位的菜市场,夏日正午,几个人蹲在流水的渠边吃西瓜,一边吃一边扔皮。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穿着一身油垢的衣服,拣拾我们丢弃的西瓜皮,放在一边的芨芨草编织的篮子里。二是在集市上,看见一个疯了的男人,夏天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军大衣,不停呵呵笑着,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一直穿梭到集市散尽,也没有看到他有一丝不快乐。三是一起来的张小生在30里外的鼎新镇找了对象,有次要我陪着他去。在一家理发店理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觉到异性的身体,以及她身上的气味。 日,跟随单位的人,骑自行车,出营门,看到弱水河,沙漠的河流,清澈的水,冰冷刺骨。背一位女同事过河(她在我背上的感觉至今没有消散)。看见秦朝大将蒙恬建立的烽火台,5里一座,矗在黑色戈壁隆起的山包上。在天仓村后,进入彭祖居住过的窑洞,面对被村民用铁锨铲坏的壁画(彭祖和女孩子云雨交欢的画面),痛惜出声。沿路的坚硬山包中部,还有不少窑洞,据说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年代的遗物。那里还有一座形状像卧牛的山,浑身褐红,头角峥嵘。在一座铁矿选厂的一边,发现一座古代的城池,虽然已成废墟,但城墙和城中建筑的轮廓还在,遍生的茅草当中,我只认得芨芨草、骆驼刺、红柳和蓬棵。 再远处是清水(应是西北最大的兵站),有一年去了3次,一次回家;一次去接头儿的两个亲戚;还有一次是独自去玩,在一座铁桥下面,看到秋天的芦苇和水中游弋的野鸭。之后的酒泉和嘉峪关似乎是四年后才去的,偏僻的边地城市,丝绸之路上的现代城池,伊初的陌生让我感觉到一个客居者与它的格格不入。武威和兰州,那些年我去了好几次,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有一次,在回程车上竟然遇到一个同事,惊喜之余,在餐车喝酒,喝得晕了,一直睡到玉门镇才醒来,只好再返身回到酒泉。 1999年以前,回老家喜欢走陇海线,河西走廊之后,兰州、陇西、定西、天水、秦岭、宝鸡、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安阳,这些城市在窗外,钢铁的奔走让我真实地触摸到了时光的迅即感。路上的风景是雷同的,绿色的植被、咆哮的河流和巍峨的高山,黄土的高原在黑夜或者白昼不断起伏和消失。邯郸下一站,我下车,再换乘汽车,往太行山里走。2000年以后,我习惯走包兰线和京张线,路过青海(那时候喜欢写诗,自然想起诗人昌耀),大都是晚上,黑山白雪,城市的灯火有点冷漠;宁夏(想起红艳艳的枸杞子);内蒙(想起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草原之夜》);山西大同(想知道五台山具体方位,还想起小时候听村里雇请的山西放羊人唱得有点黄的民歌《七十二开花》)。张家口(想起它流转的皮货)。到北京西山,燕山深处,草木茂盛,巍峨但有残缺的长城高高在上。北京——更多是茫然,还有到达的轻松和忙乱。 再后来(这话像是讲故事):我很少乘坐火车,每次回家和出差乘飞机(母亲至今没有乘坐过),从沙漠起飞,俯首大地(沙漠、戈壁、村庄和河流)都在身下(还有钢铁、座垫和地毯等等东西)。连我一直仰视的祁连山也变做了一平地上一堆隆起之物,白的积雪和云层一样洁白,阳光从上面投射下去,再返回到眼睛中。天空与大地,我(当然还有同机的人)在其中。那时候,我常常想:向上也是一种道路,还有向下的,平行的道路,它们的确切方向究竟是哪里?走出机舱时,我总会长长地出一口气,看看周边的矗立在大地上的事物,然后才提着箱包,慢步走下舷梯。 内在的果实 2005年,在巴丹吉林,春天的中部,几天来,一直看见杏花和梨花,相邻的杨树和沙枣树还没有萌出新芽。少有的杏花开得粉红,阳光温暖,正午的妖艳光泽让周边的树木感到无奈和羞涩。每次路过,我会停下来,盯着满树的杏花看,短暂的(瞬间的感觉像是与一位心仪已久的首次谋面),鼻子凑近,因为感冒鼻塞,她的香味是去年的(印象中的香味是不是比眼前的更为真实和干净呢?)感冒之后,骨节的酸疼瞬间消失,连同持续数天的鼻塞症状。心情舒朗之时,杏花却已落尽(我再也不会嗅到这一年的杏花的味道了。)这样的一种遭际,以前肯定有过,但从未注意。 杏花之后,梨花再开,办公楼前的稀落树木,一身的花朵,在正午显得脂粉浓重,在入夜时分素洁异常。花朵的味道在空中,在频繁的沙尘暴中,沦落风尘。她们的花片和花蕊是惨白的,微卷的。似乎皱褶的面孔,美丽之间的隐藏和展现(我敢说,在这个小小的营区,除我之外,没有人观察得如此仔细。)一夜风吹,梨花也不再了,就连落在地上的花片,也杳无踪影。叶子生长,青色的小果实不久就被掩盖。 很多年我就知道:这里的杏树的果实叫李广杏(以我倍加推崇的汉代将军命名),名字所蕴涵的文化,悲怆的鲜血和长矛硬弓,时间的沧桑、个人武功和卓越品格。除了史书之外,还被这样一种果实所传承。客居此地15年时间,每年五月,我都可以吃到“李广杏”,味甜,汁多,据说还有治疗咽喉肿疼和醒神开胃的功效。它的内核坚硬,杏仁很香,满口生津,积攒多了,我想用来榨油炒菜一定别有味道。这一种想法,不知道古人,或者李广本人,在他们那个年代有没有尝试过?每次吃的时候,还没下口,就想起了这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盖世将军。 而人不在了,他的尸骨已经找不到了,骨殖灰飞,灵魂安在?名字和故事留在一种果实当中,这种流传,古今的蹊跷,时间和世事(抑或人的不朽)的延续,叫人迷茫而又欣慰。在与外面的朋友通话时候,我也经常拿“李广杏”作为炫耀和吸引。让他们在听觉中口舌生津,心驰神往(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我一样自然想起李广)。 而苹果梨树,则是变种,一个外来者的形象,梨子和杏子混合的形状让我匪夷所思,尤其是刚刚来到,抓住一颗就要下口的时候,心里异样的感觉,像是看到一个树木乃至果实的混血(树木和果实的混血是不是也像人混血一样呢?或者同出一辙)。据说是从青海或者宁夏那边嫁接过来的,当地的梨树和它地的梨树,因为一根枝条,而变成了另一种树木。它是树冠是庞大的,叶子呈椎圆形,树干黝黑泛红,其中有些类似雀斑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从树根到树梢,均匀密布。 最开始,杏子和苹果梨都是苦涩的。不同之处:杏子小,酸,软,不用费大的力气,就可以咬开;那种酸,犹如北方酸枣的酸,甚至有过不及。怀孕的妇女很喜欢,刚刚小指头肚大,就嚷着叫老公摘几个吃(我看到的几乎都吃得津津有味,连一点酸的皱纹都没有泛起)。苹果梨则是坚硬的,看起来,青色的果实,再坚硬的牙齿,再大的力气咬下去,留下的只是一道浅浅的牙印(这种果实似乎有自我保护功能,未成熟之前,决不容易让好吃的人不费力气就将自己消灭在他们的牙齿和肠道之间)。 杏花之后,梨花。梨花之后,才是苹果花,白色的花朵,包着一层粉红的表皮,类似少女脸上的“高原红”。我知道的情况是:巴丹吉林的苹果树也是外来的,伊初是随着人的手掌和脚步,现在是飞速的车轮。这里土质粗糙,含碱量大,再好的苹果树种永远也长不高,果实类似小孩子拳头,直到十月匍降白霜,叶子卷曲,呈焦黑色,仍还高悬枝头。清晨,果实坚硬,手摸,便可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冷。 这里的枣花有两种:大枣花和沙枣花。它们根本区别是:大枣由人在自家的果园栽种,果实属私有。沙枣为野生,果实为公有。大枣大致原地山东或河北(巴丹吉林沙漠以西的绿洲和村落,大都不是原住民,从方言看,大致来自山东、河北、陕西、内蒙等地)花是米黄色的,颗粒细小,密布枝桠间,掩住伸出的长刺。有人说,最好的蜂蜜就是出自枣花,但这里似乎没有很多的蜜蜂,大都是大黄蜂和小黄蜂,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生灵,从不成群结队,而是单独一只,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飞走了又来了(事实上,我根本无法判定是不是先前的那只)。 在巴丹吉林所有的果实花朵当中,沙枣花最美,香气浓郁,30米开外,就可以嗅到(这种树木,跟随沙漠河流而生,幼时成丛,逐渐有强壮者突出起来,成大树,但躯干扭曲,皮肤皲裂,始终长不高)。记得刚来这里的第一年春天,礼堂旁边有几棵,每当开花,总喜欢在它的周围转,一直到夕阳尽没。秋天时候,沙枣树绿叶枯黄,一夜之间,尽落地面,只留下一连串的红色果实,悬挂干枯的树枝上。整整一冬之后,连续的沙漠大风,也没有将它们击打下来。直到再一年的春天,花朵盛开,绿叶萌生,还有不少仍在新一年的绿叶和果实之间,沉默悬挂。 杏子可以做成杏脯,摊开,晾干,冬日吃,干硬,水份尽失,但越嚼越有味道。苹果梨可以用筐子或纸箱存放在地窖里(但需要悬挂),可以吃到开春。对于大枣,我喜欢晒干后的,皮肉虽然干枯,但用粮食酒浸泡之后,膨胀,色彩鲜艳,肉质辣甜(据说具有补肾壮阳的功效);有闲暇的妇女,打了沙枣,晾干,磨成细面,炸油饼时候,包在里面,香甜而又酸涩,适宜就着米粥和咸菜吃。至于拳头一般大小的苹果,成熟后仍旧是酸的,冬天怀孕的妇女视为佳品,但放的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变甜,到来年再吃,竟甜如面酱。 这些巴丹吉林的花朵和果实,突出地面的美丽之物。14年,我一直在其中,看着它们开花、长叶、结果、成熟和衰落。粗略计算,它们当中,起码有一吨进入到我的身体。它们在我身体消失(我在它们的轮回中慢慢消失)。曾经有几年,我看到了花朵,便不再想到果实,叶很少到结果的树下去走走看看,偶尔的路过也视而不见。直到果实拿到了面前,才知道它们成熟了(对另一些事物过程的忽略是不是一种罪过呢)?所幸:看到杏子我会想起李广,看到苹果梨、大枣和苹果,潜意识里就觉察到了周边的辽阔和博大;而看到沙枣,就会想到河流,想起丑陋的形体之上,盛开的最美的花朵。对于沙枣树来说:戈壁之中的生长和存在,具体或者模糊,我相信它们都是内在的,自我的,可触可摸,并且都有着自己的形体、品质和色泽。 三个上级 1998年,朱国林来我当时的单位任副职。此前听说,他在另一个单位做头儿的最后一年,因为一件小事(讲述人略),一个湖北籍的下属气急,操刀欲砍之(刀是饭堂切肉的大板刀),众多人拦住。湖北籍下属不肯罢休,声言必砍之而后快。晚上,朱国林一个人不敢在宿舍睡,与一名副职换了房间。午夜,门开,湖北籍下属箭步进来,直奔床铺,手起刀落之际,朱国林从门口猛喝一声。操刀者惊,刀落地板,哐啷声,在深夜的楼道格外清晰,其他同事闻声赶来,只看见朱国林怒目圆睁,指着自己的胸脯和脖子,对湖北籍下属吼说:我就在这里,你拿刀砍呀!砍呀!砍呀!不砍你就不是你妈生的!湖北籍下属怔怔不动,眼睛盯着白日里吓得抱头鼠窜的上级,若知错的孩子一般。 到我们单位之后,因副职故,平时少对我等指手画脚,也在正头儿的指派下,俯首贴耳,百依百顺。对我等下属,若兄弟一般,多次请全单位(共6个人)周末到他家吃饭。下属有个人私事,其循循善诱,若亲兄弟一般看待。不到一年时间,其在单位威信倍增,即使新来的同事,也被我等对他的赞誉五体投地。再一年,正职升迁。没有正式任命之前,朱国林一如既往,带领我等,加班加点,兢兢业业。2个月后,正式命令下达,搬到正职办公室之后,我等还像一样进出无忌,除在上班时间称之为某某长之外,课余时间,仍如往常一样,年老的直呼其名,年少的则姓后加某某长。不觉三年过去,临卸任时候,一同事老母生病,催其速回。因刚参加工作不久,积蓄不多,找到朱国林上一级领导,批准从单位预借若干元。签字找朱国林取钱,朱说这样做违反财务规定。同事百般哀求,曰:老母病重,刻不容缓,请某某长您帮忙。说到最后,眼泪呼呼,掉在朱国林的办公桌上。但朱视而不见,只顾起草文件。同事气急,拍桌子吼说:你老婆脖子上生个瘤子,你拿公款跑北京治病,我借都不可以?!为了单位工作,我两年未休假,这点事情您都不帮忙?!朱国林这时候才停下钢笔,翻了一下眼皮说,我是头儿,你是谁?你能给我比么? 1996年。我分到陈保证所在单位,他没去接我,是另外一个副职去的。单位宿舍外面有一排年久的杨树,夏日婆娑,楼侧是单位的篮球场。陈当时与接我的那位同为副职,正职空缺,二虎必然相争。陈是河北人,作为技术领导,要写许多的论文。那时计算机不甚方便,总叫我替他抄誉。不久得知,陈老家是河北献县,与我同乡。后又得知,他父亲先前在河北某政府工作,文革时候“放逐”到甘肃武威,平反后任劳动局长,当时已退休。 年底,我回乡,路过武威,他打电话给妻子,又写一信,让我见到其妻子时候当面交给。到武威之后,大雪,找到他妻子所在单位,交信,没有挽留我。刚下了大楼的最后一个台阶,其妻在后面喊我,说,不要走,陈保证让我好好招待你。与她同行,路过水果摊,我要买,她阻止。但见我执意要买,便帮忙挑了一些。中午,她叫来父母、小妹、兄弟等人,在家里做饭,几个人陪我喝酒。我看到了他们不到三岁的儿子,面白如雪,眼眉周正,说话伶俐。当日傍晚,其弟送我上长途班车,买了香烟和水果,给我带上。 等我再次回来,另外一个副职已升为正职,陈原地不动。有一段时间,其无心工作,有时一天不出宿舍。半月后,又复往常。因为是老乡,还有帮他抄誉论文的时候,陈对我甚好,真如兄弟一般。因为喜欢舞文弄墨,陈对我赏识有加,有几次向上级机关的领导推荐,又带着我,爬机关办公楼,向一个部门的领导推荐我。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那个单位相对清闲,又没很多的管束,订的杂志书刊也多。到第三年,陈要彻底离开这个单位,回武威工作。再次回来,托运东西,我自然不甘落后,帮他收拾了所有东西,装箱,运到车站。握手告别时候,陈很高兴,络腮胡子根根明亮。他告诉我们说,以后会在武威市电力局任高级工程师,欢迎大家来武威找他玩。又一年夏天,一日晚,在办公室,忽有人说,陈死了。在去兰州开会路上,车撞崖,同车三人,无一生还。 这个噩耗(曾经相亲相近的人,都是亲人)背后,还隐藏着以下一些真实情况:其弟兄三个,陈排行老三。大哥早年从铲车上摔下死亡,二哥骑摩托被卡车撞死;就连他的小侄女,第一天上班,骑自行车返家路上,被迎面的车辆撞出6米多远——又过了一年,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甘肃武威一陈姓退休干部,当场抓住小偷,而被跟踪,在家门前被刺3刀。不久后得知,这位陈姓退休老干部,就是我曾经的上级,陈保证的父亲。 四川人,刘报国。职务比我高一级,应是没有明确隶属关系的上级。刘方言浓重,个子不高,生活邋遢,床铺几天不整理,衣服泡在水盆直到发霉才动手洗出来。那时候,单位有两个未婚女同事。一甘肃天水人,个子高一点,面色白皙,眼波动人;一河北深州人,个子娇小,玲珑可人。大家都看得出来,刘报国喜欢河北,小巧玲珑的。小女孩喜吃零食,没有了,便到刘报国面前,唧唧喳喳一番,刘便径自出门,不一会儿,提回一大包零食。 从女生宿舍出来,刘眉开眼笑,扁扁的嘴巴,厚厚的嘴唇也掩不住笑着的牙齿。在单位,我与刘报国可谓天敌,不是因为那个女生,也不是因为官职利益。刘和我喜欢顶杠,各说个有理。有此讨论什么样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刘说:小巧可人,口齿伶俐,善谋略,会家务。我说:人高马大,为妻贤惠,为母慈祥,真正入心的为最佳。说着说着,焦点聚在“小巧可人”与“人高马大”这两个词语上,以至面红耳赤,继而拍桌子,再尔动手,两人在宿舍内天翻地覆一阵子,各自气咻咻分开。 此次之后,刘和我不再说话,见面侧脸,皮鞋敲打地面之中,依稀可以听到彼此鼻子轻蔑的哼声。几天之后,两人又复往常,开始都小心翼翼,生怕再因为顶杠而导致不愉快,尽量尊重彼此意见。又没几天,还如上次模样,唇枪舌剑,各不想让。这一次在室外,因为“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一争论而又面红耳赤,无桌可拍,就相互拍对方的肩膀和胸脯。幸好旁边有人,千钧一发之际,各被拉开。 第三年,河北女同事调广州任职,临行时,刘恰好不在。单位聚餐为其送行,我也在其中。几杯白酒下肚,有点发晕,不自觉地想起还在四川老家休假的刘报国,蓦然一阵伤感。也就在这一年,我调到上级机关。到原来的单位去,看到刘报国,还是一副邋遢模样,在办公室内,埋头做事情,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偶尔在路上遇到,相互打招呼,很亲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再三年,回原来的单位,刘报国已搬离5个人的办公室,坐在了原先领导的位置。 生日的心情 生日——这个词语让我木然,似乎看到一片混沌,一片鲜血,还有疼痛的嘶喊。嗅觉当中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早在一天前,这种感觉和味道就开始弥漫了,在我的内心,像是一群蜂拥的虫子,模糊的翅膀,不透明的飞翔,它们动作缓慢,在一片狭小的空间中,围绕我,声音单纯而又嘈杂。 总是想起乡村,想起4个或者6个鸡蛋,鸡蛋上还粘着米粒,被米汤煮红的蛋壳很硬,我使劲敲都敲不碎。母亲和我都不知道,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一颗鸡蛋,多了就是浪费。但母亲认为,鸡蛋是最好的,吃多了会身体好,长得结实高大。有一年生日,母亲给了做了一碗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直到我离开家乡,混迹他乡之后,再没有吃过母亲做的生日饭。倒是24岁生日那天,在单位,自己用电炉煮了4个鸡蛋,一边吃一边想起母亲,有点心酸,竟然哭了出来。 在异乡的第五年,受其他同乡的感染,生日那天,花了三百多块钱,在饭店就餐,一帮子朋友和同乡聚在一起,喝到醉倒。半夜醒来,口干若同火烧。喝了一肚子凉水,躺在床上,忽然惭愧起来: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过过生日,父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1999年在上海,生日是同学帮忙过的。那天下雨,整个天空都淅淅沥沥,珠线不断。同学文勇、小平、小龙等冒雨跑到五角场的超市,买了好多的啤酒和熟食。又将一件放置行李的房屋打扫干净。等他人睡后,几个人坐在里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喝到午夜,仍都没有醉意。 我常常想:生日是什么呢?一个人走出母亲的肚腹的那天(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些什么)。由母亲告诉的出生日期,然后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想起来,做一些所谓的祝福。我觉得沮丧,向死而生的路途,一个生日一个生日之后,最终的灰烬和坟墓——我想那就是最终的最为豪华的生日宴会了。 1998年春天,我的生日,周围没有一个人,即使有也不会告诉。那个早晨,刚刚下过一场雨,整日尘土飞扬的沙漠突然干净起起来,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我骑着车子,在林荫当中,走走停停,在果园的梨花和桃花当中,想起往事,想起母亲从饭锅里捞鸡蛋,并一一为我拨开,想起在弟弟生日时候,和他争抢一只鸡蛋的情景。 那一个生日的向晚时分,西边的天空堆起大块的云团,太阳下落之际,云彩的形状千奇百怪,狮子、奔马、野狼、兔子和象,金色的云边美奂美仑。落在麦地的阳光也是纯黄色的,近处的小路和远处的戈壁都像是铺了一层金色的黄油。在一棵杨树下面,我就那么看着,有风从背后,从更远的地方吹送,掀起衣襟。有一些白色的羊只沿着长满蒿草的沟渠游弋过来。直到天黑,我才骑上车子,返回宿舍。入夜,上床的时候,总觉得很高兴,按奈不住地笑,我努力想了好久,也说不清是究竟因为什么。 近几年来,我总是觉得:生日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存在任何意义。只要记住自己是哪一天呱呱落地足够了——形式能够说明和表达什么呢?我甚至还想,要过生日,到65岁以后才是正当的。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等个机会,为父母好好过生日,一年一次。然而,最可惜的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生养他的爷爷奶奶也不在了(先前问过奶奶,她说她也记不清了)。 过了好多生日,大都忘记了,每年都有不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是更多的人在一起。喧闹或者孤寂,都不过一天时间。但到最终,真正能够记住我的生日没有几个人。2004年春节,是在北京,和大卫、二增还有另外一位女士(忘了名字)一起,地点是羊坊店路东侧一家餐馆。喝二锅头、啤酒、饮料。在一个胡同的网吧上网,看图片和文字,听音乐。酒虽然不多,但那时候突然晕了,说不清楚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到西郊的学校,沉沉入梦之后。 被人记住生日的人是有福的。日,星期天。我的又一个生日。在巴丹吉林,早在凌晨,我就想,坐下来,安静,和妻子儿子一起,在自己的家里,还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然后坐下来,写点东西,就是最好的事情了。中午过后,心里老是有个企盼:想母亲会给我打个电话的,除了她和父亲之外,远处再没有人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了。但我不会自己对母亲说,我自己的生日,知道的人一定会记起,会在今天的某个时刻突然想起我。 现在,起风了,一如既往的沙尘暴。先前,从午夜到中午2点,整个巴丹吉林都是安静的,无风,街道两边的杨树吐出了绿芽,墙根的青草和去年的韭菜也已经绿意茵茵了。阳光明亮,春风和煦——而转眼之间,我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沙尘暴来了,呼呼的风声,首先从摔打窗棂开始,然后是砂子击打玻璃的声音。我起身关上,迎面的沙尘无孔不入,从我的口腔,直入胸腔。今天,我什么也不想做,就在这里,一个人坐着,看一些东西,想一些事情,累了,去洗个澡。 沙漠的田野 夏天,是整个巴丹吉林最美的时间,可我很少走到它的中间去看,总是很远地,站在树荫下面,或者在围墙的根部,在风吹的凉爽之中,看见不远处的田野。村庄在浓密的杨树树荫下隐藏,偶尔露出的房屋大都是白色的,还有灰色的,有的陈旧,有的崭新。正午的炊烟缠绕树木,又在树叶中消失。偶尔走动的人步履缓慢,手提农具、青草和吃食。田地一边大都是草滩,草滩中间通常都有一泊长满水草的海子,水发绿,阳光在上面,与探出腰肢和头颅的蒿草一起摇晃。 草滩上有骡子、马、驴子或者牛,它们不怕阳光的爆晒,长有毛发的身子看起来油光鉴亮。在炎热的正午,到处倒是安静,几乎没有蝉唱,牲畜的叫声比汽笛更为嘹亮。村庄和田野之外,便是微绿的戈壁滩了,微绿的东西是骆驼刺和沙蓬,稀疏的枝叶贴着灼热的地面,远看,到处都是熊熊的气浪,有时感觉像水,水声喧哗,清波荡漾。 田地里的棉花开出淡黄色的花朵,有些黄蜂在其中繁忙。阔大的叶子密密艾艾,有风也不动摇,只是棉花的头颅东摇西晃,相互摩挲。再一片田里的麦子躯干和头颅尚还青青,整齐摇摆,似乎集体的舞蹈。还有青色的苜蓿,好像已经长了很久,一棵棵匍匐在地,背面发灰的叶子像是羞涩的面孔,从密集的缝隙中,看着它们之外人和事物。 清晨风如水洗,跑步时,多出几十米,就是村庄和田野了。农人们似乎都起得很早,我们经过的时候,田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这时候,露珠很大,密集成群,等他们走出来,裤腿湿漉漉的,鞋面上还沾了不少的粗砂子。有的农人会朝我们看看,但无法辨清他们的真实眼神和表情。有些头包花布毛巾的女孩子,看人的脸和眼睛都是斜着的,慌乱而不定。那些上了年纪,或者婚后的男子女子,倒是很大胆,脸上堆起的神色本真而鲜明。 再远处,不少的海子,在逐渐稀疏的草地上,风吹的涟漪,似乎巴丹吉林眼角的皱纹。有些海子里面养殖了鲫鱼和河虾,有些人在夕阳下垂钓。这些海子一边的戈壁滩里,生长着甘草——它们的根深过地面上一层楼房。每年春天时候,附近的几个学生专门放假2天,要学生们挖甘草,一个人要挖20公斤,他们叫做“勤工俭学”。我见过最长的一根甘草,两个人轮着挖了两天,挖了50公斤,还没有挖到根。 远处的苍茫是戈壁的,也是这个世界的。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夕阳下面,骑自行车,沿着四轮车趟出的道路,曲折前行。一个人在戈壁上行走的感觉,是孤独的,那种孤独在傍晚更其深重。有一次,路过一座沙丘之后,突然看到一大片戈壁上的坟墓,有的没有墓碑,有的用黄泥做了一个,上面的名字早已模糊不清。微微隆起的土坟当中,在渐渐入暮的傍晚,散发着一种腐朽的,令人沮丧和恐惧的味道。 夏天的晚些时候,芦苇是最美的,这时候的巴丹吉林沙漠,除了这些高挑羽毛,在变凉风中整齐舞蹈的植物,再没有什么更能令人想到诗歌,想到将军的盔缨和悲怆的沙场征战了。我很多次为芦苇写诗,一个人坐在风吹的芦苇丛中,抚摸着它们即将干枯的叶子,叹息,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想周围和那些远去的事物。美的,必然是悲的。我重复这样说着,像一个孩子一样,在风中的芦苇丛中,一直到日暮黄昏,虫声四起。 棉桃接连爆开,深夜的野地,没有人听到它们整齐的声音,还有安静的正午,除了马路上偶尔的汽车奔驰。棉桃的爆裂让我想起,某一种方式的自我杀戮和释放。这时候,最美的女孩子也没有棉花洁白,再朴素的诗句也没有棉花朴素。棉花的叶子开始枯萎了,先是打卷,由叶沿向内,一天一天,最终蜷缩成一只只黑色虫子。 西瓜早就成熟了,还有一些留在地上。再毒热的阳光,还长在藤蔓上的西瓜内瓤也是沁凉的。那些在戈壁深处种植白兰瓜和哈密瓜的人,早早出来寻找买主了。周边的村庄开始忙碌起来,田野当中,到处都是屈身棉花的人,孩子们坐在架子车上,或者在附近的苜蓿地里,追逐打闹,抑或安静。每一个人的脸膛都是黑红色的。有漂亮的眼睛露出来,宝石一样闪亮。 这些年来,在巴丹吉林一边的绿洲,我看到的田野大致如此。果实不仅悬挂高处,也在地下。入夜之后,先前翠绿的绿洲一片漆黑,风中的树叶发出清脆的响声。宽阔的渠水带着上游的泥浆、草屑和肥皂泡沫,无声的流动在田地当中发出咕咕的声音。风凉的时候,就是田野终结的时候。清晨的冷风,时常让我感到一种远离的疼痛。一个夏天过去,一次田野的消失,时间交替,一个人,我总是在这个时候十分清醒,在很多的睡梦当中,看到大片的田野瞬间隐没,看见更多的茅草根根断裂,梦见自己一下子老了,一个人坐在一堆金黄的麦秸杆上,长时间昏睡不醒。 2004年旧作。至今觉得还算满意!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你满意,这一期我就用了。
:陈思侠&( 16:40:18)&
永远的厚重文字,永远都不过时!
:王相山&( 15:46:41)&
很沉静庄重的叙述,内力却相当扩张~
:易道禅&( 15:08:08)&
3 篇, 1 页 1
(必填)&&&&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发表(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沙漠有没有什么特有的生物有哪些?
沙漠有没有什么特有的生物有哪些?
不同的沙漠有不同的生物,生活沙漠的动植物一般都有抗旱耐高温的特点.温带沙漠的胡杨,骆驼刺是比较典型的植物热带沙漠的枣椰树是比较典型的植物典型的动物是骆驼(热带双峰,温带单峰)这些生物一般都生存在沙漠中,可以看做为特有的.鸵鸟,&响尾蛇,角蝮蛇,沙蛇,眼镜蛇,唾蛇、蜥蜴,蝎子,跳鼠沙漠里一些小动物都具有耐旱的生理特点.它们不需要喝水,能直接从植物体中取得水分和依靠特殊的代谢方式,获得所需水分,并在减少水分的消耗方面有一系列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它们营穴居生活,保护自己避免一切侵害;在洞穴里,可以躲避敌人、避暑和在无饲期间蛰伏不食.&过穴居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典型的代表为跳鼠,其中最常见的是三趾跳鼠和五趾跳鼠.它们喜欢在沙丘上挖洞居住,所以又有“沙跳”之称.体长约130~140毫米,共同的特点是后肢特长,足底有硬毛垫,适于在沙地上迅速跳跃,在风沙中也能一跃达60~180厘米.前肢极小,仅用于摄食和掘挖,而不用于奔跑.尾巴一般极长,有些种类的跳鼠尾巴末端有扁平的长毛束,就像“舵”一样,能在跳跃中平衡身体、把握方向.它们的头与兔子极其相似,耳朵很长,鼓室泡很大(利于听觉),眼睛也大.这些特点能够使它们顺利地在夜间作长距离的跳跃.由于沙漠中植物稀疏,并多为灌木而多刺,在这样的环境中,跳鼠主要以植物种子和昆虫为食.食物条件的限制,促使跳鼠营非群聚生活,夜间出来活动,长距离地觅找食物,有时一晚可以奔跳10公里之远.夜间,在沙丘的灌木、半灌木丛中,用灯光照射,就会很容易发现跳鼠的频繁活动,跳鼠的明亮眼睛在窥视着你,或者在你面前很快地跳过,使人感到沙丘戈壁的确是跳鼠的乐园.漫长的冬季,它们则以蛰眠而渡过.跳鼠是沙漠景观所产生的具有特殊生物形态的动物,能够与骆驼媲美.&作为沙漠中穴居动物代表的啮齿类动物,还有多种沙鼠:子午沙鼠、长爪沙鼠、柽柳沙鼠、大沙鼠等,它们均营群居生活,全年活动,但冬季活动减弱,以贮存饲料为生.大沙鼠体长超过150毫米,耳短小,耳长不到后足的一半.后足掌密毛,尾粗大,几乎接近体长.主要生活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荒漠和半荒漠的灌木琐琐丛生的沙丘和沙土地,食琐琐的肉质、多汁的叶子;有惊人的筑洞能力,洞群往往连成一片,洞道密集,能贯穿整个沙丘或地面.长爪沙鼠与子午沙鼠栖息范围较大,亦常见于干草原地带的沙地.&上述啮齿类动物大都具有沙黄的体色,便于在沙漠中掩蔽.即使在夜间活动,它们这种与背景相同的体色也是有利的.水源的缺乏使它们都有依赖植物中汁液维持身体水分代谢的特性.&沙漠里的小动物,除穴居的啮齿类外,还有一些小的爬行类动物.最多的是沙蜥和麻蜥,特别是在沙丘地带,甚至每走几步就可碰见一个.沙丘上的许多小而偏的开口,就是它们的洞穴.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应沙漠环境的能力.它们的身上没有汗腺,在各种高温环境下,都不会出汗;眼睛具有防风的眼帘;遇烈日,它们还会爬上灌丛以躲避沙面难忍的炎热.这些沙栖蜥蜴(俗名“沙和尚”)在沙地上活动非常敏捷,遇敌可潜沙而遁.
那如果这些生物离开沙漠会怎么样?
他们也能生存,但是没有在沙漠中生存的好,因为每种生物都有自己适宜的生存环境。就像在北方种柑橘一样,能种出来,但口感不好
骆驼,鸵鸟, 响尾蛇,角蝮蛇,沙蛇,眼镜蛇,唾蛇,、蜥蜴,蝎子,跳鼠 沙漠里一些小动物都具有耐旱的生理特点。它们不需要喝水,能直接从植物体中取得水分和依靠特殊的代谢方式,获得所需水分,并在减少水分的消耗方面有一系列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它们营穴居生活,保护自己避免一切侵害;在洞穴里,可以躲避敌人、避暑和在无饲期间蛰伏不食。 过穴居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典型的代表为跳鼠,其中最常见的是三趾跳鼠...
唾蛇 好像没有了从沙漠开始的道路(五则)&&&&&&&&&&
发布者:&|&
浏览(5152) 评论
&|&发布时间: 12:46:42&最后更新时间: 12:46:42
本作品所属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五则) 杨献平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 多年来,就这么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沿着可以走的道路,缓慢或者急速地走。四周都是风景,都是人,我看到的,没有看到的,看到我的,没有看到我的,那些路,路上的事物久长或者短暂,我相信它们并不取决于路过的某个人。某一天,我突然感到沮丧:这么多年,走了那么多的路,但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母亲相比,我的这些路仍旧是短暂的。 据我所知:母亲走过的大致有这么一些:去过3次100多公里外的邢台市和沙河市,还有山西左权的拐儿镇;再就是来过2次西北(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剩下的,她的路限定在村庄向北30公里的路罗镇、向东的乡政府所在地和派出所大院,向南是20公里的南山,向西到武安的阳鄄乡。范围再小:最远就是五里外的石盆村、三里外的自留地和后山的果树下了。 母亲就这样反复走着,脚下的路短暂而又漫长。她走的时候:身上还扛着或提着锄头、镰刀、粮食、清水等等一类的东西。记得她来我这里时,第一次带了1000元钱、10斤小米、一双自己做的布鞋;第二次是冬天:带了小米20斤、柿饼10斤、还有给她孙子做的2双布鞋和一身衣服。 我也一直走着,跟在她身后;她走过的那些,在我长大成人或者还在襁褓中,也断断续续地走过了。到西北,在巴丹吉林沙漠,我的最初是安静的,最远就是往返老家。后来,去更多的远处,携带皮箱、礼品、眼镜、书籍、手表和手机,还有各式各样的心情。还有一个区别是:母亲走远路带的钱总是不超过1000元,我呢,每次,至少也要多她两倍以上。母亲只有一次一个人走远路(含返回),我至少20余次(并不包括以后)。 我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到处都是戈壁,附近的村庄始终在炊烟、绿树、枯树和土尘之中。我时常站在营门前(偶尔坐在班车上),看见异地的村庄。它们的隐藏和浮现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心理的效应。唯一记得的有3件事情。一是在单位的菜市场,夏日正午,几个人蹲在流水的渠边吃西瓜,一边吃一边扔皮。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穿着一身油垢的衣服,拣拾我们丢弃的西瓜皮,放在一边的芨芨草编织的篮子里。二是在集市上,看见一个疯了的男人,夏天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军大衣,不停呵呵笑着,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一直穿梭到集市散尽,也没有看到他有一丝不快乐。三是一起来的张小生在30里外的鼎新镇找了对象,有次要我陪着他去。在一家理发店理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觉到异性的身体,以及她身上的气味。 日,跟随单位的人,骑自行车,出营门,看到弱水河,沙漠的河流,清澈的水,冰冷刺骨。背一位女同事过河(她在我背上的感觉至今没有消散)。看见秦朝大将蒙恬建立的烽火台,5里一座,矗在黑色戈壁隆起的山包上。在天仓村后,进入彭祖居住过的窑洞,面对被村民用铁锨铲坏的壁画(彭祖和女孩子云雨交欢的画面),痛惜出声。沿路的坚硬山包中部,还有不少窑洞,据说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年代的遗物。那里还有一座形状像卧牛的山,浑身褐红,头角峥嵘。在一座铁矿选厂的一边,发现一座古代的城池,虽然已成废墟,但城墙和城中建筑的轮廓还在,遍生的茅草当中,我只认得芨芨草、骆驼刺、红柳和蓬棵。 再远处是清水(应是西北最大的兵站),有一年去了3次,一次回家;一次去接头儿的两个亲戚;还有一次是独自去玩,在一座铁桥下面,看到秋天的芦苇和水中游弋的野鸭。之后的酒泉和嘉峪关似乎是四年后才去的,偏僻的边地城市,丝绸之路上的现代城池,伊初的陌生让我感觉到一个客居者与它的格格不入。武威和兰州,那些年我去了好几次,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有一次,在回程车上竟然遇到一个同事,惊喜之余,在餐车喝酒,喝得晕了,一直睡到玉门镇才醒来,只好再返身回到酒泉。 1999年以前,回老家喜欢走陇海线,河西走廊之后,兰州、陇西、定西、天水、秦岭、宝鸡、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安阳,这些城市在窗外,钢铁的奔走让我真实地触摸到了时光的迅即感。路上的风景是雷同的,绿色的植被、咆哮的河流和巍峨的高山,黄土的高原在黑夜或者白昼不断起伏和消失。邯郸下一站,我下车,再换乘汽车,往太行山里走。2000年以后,我习惯走包兰线和京张线,路过青海(那时候喜欢写诗,自然想起诗人昌耀),大都是晚上,黑山白雪,城市的灯火有点冷漠;宁夏(想起红艳艳的枸杞子);内蒙(想起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草原之夜》);山西大同(想知道五台山具体方位,还想起小时候听村里雇请的山西放羊人唱得有点黄的民歌《七十二开花》)。张家口(想起它流转的皮货)。到北京西山,燕山深处,草木茂盛,巍峨但有残缺的长城高高在上。北京——更多是茫然,还有到达的轻松和忙乱。 再后来(这话像是讲故事):我很少乘坐火车,每次回家和出差乘飞机(母亲至今没有乘坐过),从沙漠起飞,俯首大地(沙漠、戈壁、村庄和河流)都在身下(还有钢铁、座垫和地毯等等东西)。连我一直仰视的祁连山也变做了一平地上一堆隆起之物,白的积雪和云层一样洁白,阳光从上面投射下去,再返回到眼睛中。天空与大地,我(当然还有同机的人)在其中。那时候,我常常想:向上也是一种道路,还有向下的,平行的道路,它们的确切方向究竟是哪里?走出机舱时,我总会长长地出一口气,看看周边的矗立在大地上的事物,然后才提着箱包,慢步走下舷梯。 内在的果实 2005年,在巴丹吉林,春天的中部,几天来,一直看见杏花和梨花,相邻的杨树和沙枣树还没有萌出新芽。少有的杏花开得粉红,阳光温暖,正午的妖艳光泽让周边的树木感到无奈和羞涩。每次路过,我会停下来,盯着满树的杏花看,短暂的(瞬间的感觉像是与一位心仪已久的首次谋面),鼻子凑近,因为感冒鼻塞,她的香味是去年的(印象中的香味是不是比眼前的更为真实和干净呢?)感冒之后,骨节的酸疼瞬间消失,连同持续数天的鼻塞症状。心情舒朗之时,杏花却已落尽(我再也不会嗅到这一年的杏花的味道了。)这样的一种遭际,以前肯定有过,但从未注意。 杏花之后,梨花再开,办公楼前的稀落树木,一身的花朵,在正午显得脂粉浓重,在入夜时分素洁异常。花朵的味道在空中,在频繁的沙尘暴中,沦落风尘。她们的花片和花蕊是惨白的,微卷的。似乎皱褶的面孔,美丽之间的隐藏和展现(我敢说,在这个小小的营区,除我之外,没有人观察得如此仔细。)一夜风吹,梨花也不再了,就连落在地上的花片,也杳无踪影。叶子生长,青色的小果实不久就被掩盖。 很多年我就知道:这里的杏树的果实叫李广杏(以我倍加推崇的汉代将军命名),名字所蕴涵的文化,悲怆的鲜血和长矛硬弓,时间的沧桑、个人武功和卓越品格。除了史书之外,还被这样一种果实所传承。客居此地15年时间,每年五月,我都可以吃到“李广杏”,味甜,汁多,据说还有治疗咽喉肿疼和醒神开胃的功效。它的内核坚硬,杏仁很香,满口生津,积攒多了,我想用来榨油炒菜一定别有味道。这一种想法,不知道古人,或者李广本人,在他们那个年代有没有尝试过?每次吃的时候,还没下口,就想起了这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盖世将军。 而人不在了,他的尸骨已经找不到了,骨殖灰飞,灵魂安在?名字和故事留在一种果实当中,这种流传,古今的蹊跷,时间和世事(抑或人的不朽)的延续,叫人迷茫而又欣慰。在与外面的朋友通话时候,我也经常拿“李广杏”作为炫耀和吸引。让他们在听觉中口舌生津,心驰神往(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我一样自然想起李广)。 而苹果梨树,则是变种,一个外来者的形象,梨子和杏子混合的形状让我匪夷所思,尤其是刚刚来到,抓住一颗就要下口的时候,心里异样的感觉,像是看到一个树木乃至果实的混血(树木和果实的混血是不是也像人混血一样呢?或者同出一辙)。据说是从青海或者宁夏那边嫁接过来的,当地的梨树和它地的梨树,因为一根枝条,而变成了另一种树木。它是树冠是庞大的,叶子呈椎圆形,树干黝黑泛红,其中有些类似雀斑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从树根到树梢,均匀密布。 最开始,杏子和苹果梨都是苦涩的。不同之处:杏子小,酸,软,不用费大的力气,就可以咬开;那种酸,犹如北方酸枣的酸,甚至有过不及。怀孕的妇女很喜欢,刚刚小指头肚大,就嚷着叫老公摘几个吃(我看到的几乎都吃得津津有味,连一点酸的皱纹都没有泛起)。苹果梨则是坚硬的,看起来,青色的果实,再坚硬的牙齿,再大的力气咬下去,留下的只是一道浅浅的牙印(这种果实似乎有自我保护功能,未成熟之前,决不容易让好吃的人不费力气就将自己消灭在他们的牙齿和肠道之间)。 杏花之后,梨花。梨花之后,才是苹果花,白色的花朵,包着一层粉红的表皮,类似少女脸上的“高原红”。我知道的情况是:巴丹吉林的苹果树也是外来的,伊初是随着人的手掌和脚步,现在是飞速的车轮。这里土质粗糙,含碱量大,再好的苹果树种永远也长不高,果实类似小孩子拳头,直到十月匍降白霜,叶子卷曲,呈焦黑色,仍还高悬枝头。清晨,果实坚硬,手摸,便可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冷。 这里的枣花有两种:大枣花和沙枣花。它们根本区别是:大枣由人在自家的果园栽种,果实属私有。沙枣为野生,果实为公有。大枣大致原地山东或河北(巴丹吉林沙漠以西的绿洲和村落,大都不是原住民,从方言看,大致来自山东、河北、陕西、内蒙等地)花是米黄色的,颗粒细小,密布枝桠间,掩住伸出的长刺。有人说,最好的蜂蜜就是出自枣花,但这里似乎没有很多的蜜蜂,大都是大黄蜂和小黄蜂,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生灵,从不成群结队,而是单独一只,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飞走了又来了(事实上,我根本无法判定是不是先前的那只)。 在巴丹吉林所有的果实花朵当中,沙枣花最美,香气浓郁,30米开外,就可以嗅到(这种树木,跟随沙漠河流而生,幼时成丛,逐渐有强壮者突出起来,成大树,但躯干扭曲,皮肤皲裂,始终长不高)。记得刚来这里的第一年春天,礼堂旁边有几棵,每当开花,总喜欢在它的周围转,一直到夕阳尽没。秋天时候,沙枣树绿叶枯黄,一夜之间,尽落地面,只留下一连串的红色果实,悬挂干枯的树枝上。整整一冬之后,连续的沙漠大风,也没有将它们击打下来。直到再一年的春天,花朵盛开,绿叶萌生,还有不少仍在新一年的绿叶和果实之间,沉默悬挂。 杏子可以做成杏脯,摊开,晾干,冬日吃,干硬,水份尽失,但越嚼越有味道。苹果梨可以用筐子或纸箱存放在地窖里(但需要悬挂),可以吃到开春。对于大枣,我喜欢晒干后的,皮肉虽然干枯,但用粮食酒浸泡之后,膨胀,色彩鲜艳,肉质辣甜(据说具有补肾壮阳的功效);有闲暇的妇女,打了沙枣,晾干,磨成细面,炸油饼时候,包在里面,香甜而又酸涩,适宜就着米粥和咸菜吃。至于拳头一般大小的苹果,成熟后仍旧是酸的,冬天怀孕的妇女视为佳品,但放的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变甜,到来年再吃,竟甜如面酱。 这些巴丹吉林的花朵和果实,突出地面的美丽之物。14年,我一直在其中,看着它们开花、长叶、结果、成熟和衰落。粗略计算,它们当中,起码有一吨进入到我的身体。它们在我身体消失(我在它们的轮回中慢慢消失)。曾经有几年,我看到了花朵,便不再想到果实,叶很少到结果的树下去走走看看,偶尔的路过也视而不见。直到果实拿到了面前,才知道它们成熟了(对另一些事物过程的忽略是不是一种罪过呢)?所幸:看到杏子我会想起李广,看到苹果梨、大枣和苹果,潜意识里就觉察到了周边的辽阔和博大;而看到沙枣,就会想到河流,想起丑陋的形体之上,盛开的最美的花朵。对于沙枣树来说:戈壁之中的生长和存在,具体或者模糊,我相信它们都是内在的,自我的,可触可摸,并且都有着自己的形体、品质和色泽。 三个上级 1998年,朱国林来我当时的单位任副职。此前听说,他在另一个单位做头儿的最后一年,因为一件小事(讲述人略),一个湖北籍的下属气急,操刀欲砍之(刀是饭堂切肉的大板刀),众多人拦住。湖北籍下属不肯罢休,声言必砍之而后快。晚上,朱国林一个人不敢在宿舍睡,与一名副职换了房间。午夜,门开,湖北籍下属箭步进来,直奔床铺,手起刀落之际,朱国林从门口猛喝一声。操刀者惊,刀落地板,哐啷声,在深夜的楼道格外清晰,其他同事闻声赶来,只看见朱国林怒目圆睁,指着自己的胸脯和脖子,对湖北籍下属吼说:我就在这里,你拿刀砍呀!砍呀!砍呀!不砍你就不是你妈生的!湖北籍下属怔怔不动,眼睛盯着白日里吓得抱头鼠窜的上级,若知错的孩子一般。 到我们单位之后,因副职故,平时少对我等指手画脚,也在正头儿的指派下,俯首贴耳,百依百顺。对我等下属,若兄弟一般,多次请全单位(共6个人)周末到他家吃饭。下属有个人私事,其循循善诱,若亲兄弟一般看待。不到一年时间,其在单位威信倍增,即使新来的同事,也被我等对他的赞誉五体投地。再一年,正职升迁。没有正式任命之前,朱国林一如既往,带领我等,加班加点,兢兢业业。2个月后,正式命令下达,搬到正职办公室之后,我等还像一样进出无忌,除在上班时间称之为某某长之外,课余时间,仍如往常一样,年老的直呼其名,年少的则姓后加某某长。不觉三年过去,临卸任时候,一同事老母生病,催其速回。因刚参加工作不久,积蓄不多,找到朱国林上一级领导,批准从单位预借若干元。签字找朱国林取钱,朱说这样做违反财务规定。同事百般哀求,曰:老母病重,刻不容缓,请某某长您帮忙。说到最后,眼泪呼呼,掉在朱国林的办公桌上。但朱视而不见,只顾起草文件。同事气急,拍桌子吼说:你老婆脖子上生个瘤子,你拿公款跑北京治病,我借都不可以?!为了单位工作,我两年未休假,这点事情您都不帮忙?!朱国林这时候才停下钢笔,翻了一下眼皮说,我是头儿,你是谁?你能给我比么? 1996年。我分到陈保证所在单位,他没去接我,是另外一个副职去的。单位宿舍外面有一排年久的杨树,夏日婆娑,楼侧是单位的篮球场。陈当时与接我的那位同为副职,正职空缺,二虎必然相争。陈是河北人,作为技术领导,要写许多的论文。那时计算机不甚方便,总叫我替他抄誉。不久得知,陈老家是河北献县,与我同乡。后又得知,他父亲先前在河北某政府工作,文革时候“放逐”到甘肃武威,平反后任劳动局长,当时已退休。 年底,我回乡,路过武威,他打电话给妻子,又写一信,让我见到其妻子时候当面交给。到武威之后,大雪,找到他妻子所在单位,交信,没有挽留我。刚下了大楼的最后一个台阶,其妻在后面喊我,说,不要走,陈保证让我好好招待你。与她同行,路过水果摊,我要买,她阻止。但见我执意要买,便帮忙挑了一些。中午,她叫来父母、小妹、兄弟等人,在家里做饭,几个人陪我喝酒。我看到了他们不到三岁的儿子,面白如雪,眼眉周正,说话伶俐。当日傍晚,其弟送我上长途班车,买了香烟和水果,给我带上。 等我再次回来,另外一个副职已升为正职,陈原地不动。有一段时间,其无心工作,有时一天不出宿舍。半月后,又复往常。因为是老乡,还有帮他抄誉论文的时候,陈对我甚好,真如兄弟一般。因为喜欢舞文弄墨,陈对我赏识有加,有几次向上级机关的领导推荐,又带着我,爬机关办公楼,向一个部门的领导推荐我。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那个单位相对清闲,又没很多的管束,订的杂志书刊也多。到第三年,陈要彻底离开这个单位,回武威工作。再次回来,托运东西,我自然不甘落后,帮他收拾了所有东西,装箱,运到车站。握手告别时候,陈很高兴,络腮胡子根根明亮。他告诉我们说,以后会在武威市电力局任高级工程师,欢迎大家来武威找他玩。又一年夏天,一日晚,在办公室,忽有人说,陈死了。在去兰州开会路上,车撞崖,同车三人,无一生还。 这个噩耗(曾经相亲相近的人,都是亲人)背后,还隐藏着以下一些真实情况:其弟兄三个,陈排行老三。大哥早年从铲车上摔下死亡,二哥骑摩托被卡车撞死;就连他的小侄女,第一天上班,骑自行车返家路上,被迎面的车辆撞出6米多远——又过了一年,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甘肃武威一陈姓退休干部,当场抓住小偷,而被跟踪,在家门前被刺3刀。不久后得知,这位陈姓退休老干部,就是我曾经的上级,陈保证的父亲。 四川人,刘报国。职务比我高一级,应是没有明确隶属关系的上级。刘方言浓重,个子不高,生活邋遢,床铺几天不整理,衣服泡在水盆直到发霉才动手洗出来。那时候,单位有两个未婚女同事。一甘肃天水人,个子高一点,面色白皙,眼波动人;一河北深州人,个子娇小,玲珑可人。大家都看得出来,刘报国喜欢河北,小巧玲珑的。小女孩喜吃零食,没有了,便到刘报国面前,唧唧喳喳一番,刘便径自出门,不一会儿,提回一大包零食。 从女生宿舍出来,刘眉开眼笑,扁扁的嘴巴,厚厚的嘴唇也掩不住笑着的牙齿。在单位,我与刘报国可谓天敌,不是因为那个女生,也不是因为官职利益。刘和我喜欢顶杠,各说个有理。有此讨论什么样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刘说:小巧可人,口齿伶俐,善谋略,会家务。我说:人高马大,为妻贤惠,为母慈祥,真正入心的为最佳。说着说着,焦点聚在“小巧可人”与“人高马大”这两个词语上,以至面红耳赤,继而拍桌子,再尔动手,两人在宿舍内天翻地覆一阵子,各自气咻咻分开。 此次之后,刘和我不再说话,见面侧脸,皮鞋敲打地面之中,依稀可以听到彼此鼻子轻蔑的哼声。几天之后,两人又复往常,开始都小心翼翼,生怕再因为顶杠而导致不愉快,尽量尊重彼此意见。又没几天,还如上次模样,唇枪舌剑,各不想让。这一次在室外,因为“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一争论而又面红耳赤,无桌可拍,就相互拍对方的肩膀和胸脯。幸好旁边有人,千钧一发之际,各被拉开。 第三年,河北女同事调广州任职,临行时,刘恰好不在。单位聚餐为其送行,我也在其中。几杯白酒下肚,有点发晕,不自觉地想起还在四川老家休假的刘报国,蓦然一阵伤感。也就在这一年,我调到上级机关。到原来的单位去,看到刘报国,还是一副邋遢模样,在办公室内,埋头做事情,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偶尔在路上遇到,相互打招呼,很亲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再三年,回原来的单位,刘报国已搬离5个人的办公室,坐在了原先领导的位置。 生日的心情 生日——这个词语让我木然,似乎看到一片混沌,一片鲜血,还有疼痛的嘶喊。嗅觉当中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早在一天前,这种感觉和味道就开始弥漫了,在我的内心,像是一群蜂拥的虫子,模糊的翅膀,不透明的飞翔,它们动作缓慢,在一片狭小的空间中,围绕我,声音单纯而又嘈杂。 总是想起乡村,想起4个或者6个鸡蛋,鸡蛋上还粘着米粒,被米汤煮红的蛋壳很硬,我使劲敲都敲不碎。母亲和我都不知道,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一颗鸡蛋,多了就是浪费。但母亲认为,鸡蛋是最好的,吃多了会身体好,长得结实高大。有一年生日,母亲给了做了一碗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直到我离开家乡,混迹他乡之后,再没有吃过母亲做的生日饭。倒是24岁生日那天,在单位,自己用电炉煮了4个鸡蛋,一边吃一边想起母亲,有点心酸,竟然哭了出来。 在异乡的第五年,受其他同乡的感染,生日那天,花了三百多块钱,在饭店就餐,一帮子朋友和同乡聚在一起,喝到醉倒。半夜醒来,口干若同火烧。喝了一肚子凉水,躺在床上,忽然惭愧起来: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过过生日,父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1999年在上海,生日是同学帮忙过的。那天下雨,整个天空都淅淅沥沥,珠线不断。同学文勇、小平、小龙等冒雨跑到五角场的超市,买了好多的啤酒和熟食。又将一件放置行李的房屋打扫干净。等他人睡后,几个人坐在里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喝到午夜,仍都没有醉意。 我常常想:生日是什么呢?一个人走出母亲的肚腹的那天(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些什么)。由母亲告诉的出生日期,然后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想起来,做一些所谓的祝福。我觉得沮丧,向死而生的路途,一个生日一个生日之后,最终的灰烬和坟墓——我想那就是最终的最为豪华的生日宴会了。 1998年春天,我的生日,周围没有一个人,即使有也不会告诉。那个早晨,刚刚下过一场雨,整日尘土飞扬的沙漠突然干净起起来,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我骑着车子,在林荫当中,走走停停,在果园的梨花和桃花当中,想起往事,想起母亲从饭锅里捞鸡蛋,并一一为我拨开,想起在弟弟生日时候,和他争抢一只鸡蛋的情景。 那一个生日的向晚时分,西边的天空堆起大块的云团,太阳下落之际,云彩的形状千奇百怪,狮子、奔马、野狼、兔子和象,金色的云边美奂美仑。落在麦地的阳光也是纯黄色的,近处的小路和远处的戈壁都像是铺了一层金色的黄油。在一棵杨树下面,我就那么看着,有风从背后,从更远的地方吹送,掀起衣襟。有一些白色的羊只沿着长满蒿草的沟渠游弋过来。直到天黑,我才骑上车子,返回宿舍。入夜,上床的时候,总觉得很高兴,按奈不住地笑,我努力想了好久,也说不清是究竟因为什么。 近几年来,我总是觉得:生日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存在任何意义。只要记住自己是哪一天呱呱落地足够了——形式能够说明和表达什么呢?我甚至还想,要过生日,到65岁以后才是正当的。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等个机会,为父母好好过生日,一年一次。然而,最可惜的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生养他的爷爷奶奶也不在了(先前问过奶奶,她说她也记不清了)。 过了好多生日,大都忘记了,每年都有不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是更多的人在一起。喧闹或者孤寂,都不过一天时间。但到最终,真正能够记住我的生日没有几个人。2004年春节,是在北京,和大卫、二增还有另外一位女士(忘了名字)一起,地点是羊坊店路东侧一家餐馆。喝二锅头、啤酒、饮料。在一个胡同的网吧上网,看图片和文字,听音乐。酒虽然不多,但那时候突然晕了,说不清楚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到西郊的学校,沉沉入梦之后。 被人记住生日的人是有福的。日,星期天。我的又一个生日。在巴丹吉林,早在凌晨,我就想,坐下来,安静,和妻子儿子一起,在自己的家里,还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然后坐下来,写点东西,就是最好的事情了。中午过后,心里老是有个企盼:想母亲会给我打个电话的,除了她和父亲之外,远处再没有人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了。但我不会自己对母亲说,我自己的生日,知道的人一定会记起,会在今天的某个时刻突然想起我。 现在,起风了,一如既往的沙尘暴。先前,从午夜到中午2点,整个巴丹吉林都是安静的,无风,街道两边的杨树吐出了绿芽,墙根的青草和去年的韭菜也已经绿意茵茵了。阳光明亮,春风和煦——而转眼之间,我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沙尘暴来了,呼呼的风声,首先从摔打窗棂开始,然后是砂子击打玻璃的声音。我起身关上,迎面的沙尘无孔不入,从我的口腔,直入胸腔。今天,我什么也不想做,就在这里,一个人坐着,看一些东西,想一些事情,累了,去洗个澡。 沙漠的田野 夏天,是整个巴丹吉林最美的时间,可我很少走到它的中间去看,总是很远地,站在树荫下面,或者在围墙的根部,在风吹的凉爽之中,看见不远处的田野。村庄在浓密的杨树树荫下隐藏,偶尔露出的房屋大都是白色的,还有灰色的,有的陈旧,有的崭新。正午的炊烟缠绕树木,又在树叶中消失。偶尔走动的人步履缓慢,手提农具、青草和吃食。田地一边大都是草滩,草滩中间通常都有一泊长满水草的海子,水发绿,阳光在上面,与探出腰肢和头颅的蒿草一起摇晃。 草滩上有骡子、马、驴子或者牛,它们不怕阳光的爆晒,长有毛发的身子看起来油光鉴亮。在炎热的正午,到处倒是安静,几乎没有蝉唱,牲畜的叫声比汽笛更为嘹亮。村庄和田野之外,便是微绿的戈壁滩了,微绿的东西是骆驼刺和沙蓬,稀疏的枝叶贴着灼热的地面,远看,到处都是熊熊的气浪,有时感觉像水,水声喧哗,清波荡漾。 田地里的棉花开出淡黄色的花朵,有些黄蜂在其中繁忙。阔大的叶子密密艾艾,有风也不动摇,只是棉花的头颅东摇西晃,相互摩挲。再一片田里的麦子躯干和头颅尚还青青,整齐摇摆,似乎集体的舞蹈。还有青色的苜蓿,好像已经长了很久,一棵棵匍匐在地,背面发灰的叶子像是羞涩的面孔,从密集的缝隙中,看着它们之外人和事物。 清晨风如水洗,跑步时,多出几十米,就是村庄和田野了。农人们似乎都起得很早,我们经过的时候,田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这时候,露珠很大,密集成群,等他们走出来,裤腿湿漉漉的,鞋面上还沾了不少的粗砂子。有的农人会朝我们看看,但无法辨清他们的真实眼神和表情。有些头包花布毛巾的女孩子,看人的脸和眼睛都是斜着的,慌乱而不定。那些上了年纪,或者婚后的男子女子,倒是很大胆,脸上堆起的神色本真而鲜明。 再远处,不少的海子,在逐渐稀疏的草地上,风吹的涟漪,似乎巴丹吉林眼角的皱纹。有些海子里面养殖了鲫鱼和河虾,有些人在夕阳下垂钓。这些海子一边的戈壁滩里,生长着甘草——它们的根深过地面上一层楼房。每年春天时候,附近的几个学生专门放假2天,要学生们挖甘草,一个人要挖20公斤,他们叫做“勤工俭学”。我见过最长的一根甘草,两个人轮着挖了两天,挖了50公斤,还没有挖到根。 远处的苍茫是戈壁的,也是这个世界的。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夕阳下面,骑自行车,沿着四轮车趟出的道路,曲折前行。一个人在戈壁上行走的感觉,是孤独的,那种孤独在傍晚更其深重。有一次,路过一座沙丘之后,突然看到一大片戈壁上的坟墓,有的没有墓碑,有的用黄泥做了一个,上面的名字早已模糊不清。微微隆起的土坟当中,在渐渐入暮的傍晚,散发着一种腐朽的,令人沮丧和恐惧的味道。 夏天的晚些时候,芦苇是最美的,这时候的巴丹吉林沙漠,除了这些高挑羽毛,在变凉风中整齐舞蹈的植物,再没有什么更能令人想到诗歌,想到将军的盔缨和悲怆的沙场征战了。我很多次为芦苇写诗,一个人坐在风吹的芦苇丛中,抚摸着它们即将干枯的叶子,叹息,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想周围和那些远去的事物。美的,必然是悲的。我重复这样说着,像一个孩子一样,在风中的芦苇丛中,一直到日暮黄昏,虫声四起。 棉桃接连爆开,深夜的野地,没有人听到它们整齐的声音,还有安静的正午,除了马路上偶尔的汽车奔驰。棉桃的爆裂让我想起,某一种方式的自我杀戮和释放。这时候,最美的女孩子也没有棉花洁白,再朴素的诗句也没有棉花朴素。棉花的叶子开始枯萎了,先是打卷,由叶沿向内,一天一天,最终蜷缩成一只只黑色虫子。 西瓜早就成熟了,还有一些留在地上。再毒热的阳光,还长在藤蔓上的西瓜内瓤也是沁凉的。那些在戈壁深处种植白兰瓜和哈密瓜的人,早早出来寻找买主了。周边的村庄开始忙碌起来,田野当中,到处都是屈身棉花的人,孩子们坐在架子车上,或者在附近的苜蓿地里,追逐打闹,抑或安静。每一个人的脸膛都是黑红色的。有漂亮的眼睛露出来,宝石一样闪亮。 这些年来,在巴丹吉林一边的绿洲,我看到的田野大致如此。果实不仅悬挂高处,也在地下。入夜之后,先前翠绿的绿洲一片漆黑,风中的树叶发出清脆的响声。宽阔的渠水带着上游的泥浆、草屑和肥皂泡沫,无声的流动在田地当中发出咕咕的声音。风凉的时候,就是田野终结的时候。清晨的冷风,时常让我感到一种远离的疼痛。一个夏天过去,一次田野的消失,时间交替,一个人,我总是在这个时候十分清醒,在很多的睡梦当中,看到大片的田野瞬间隐没,看见更多的茅草根根断裂,梦见自己一下子老了,一个人坐在一堆金黄的麦秸杆上,长时间昏睡不醒。 2004年旧作。至今觉得还算满意!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你满意,这一期我就用了。
:陈思侠&( 16:40:18)&
永远的厚重文字,永远都不过时!
:王相山&( 15:46:41)&
很沉静庄重的叙述,内力却相当扩张~
:易道禅&( 15:08:08)&
3 篇, 1 页 1
(必填)&&&&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发表(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沙漠化和荒漠化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给说下这个成都机电学校郫都区的详细地址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学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特点?
- ·个人办理留学生免税车购买流程申请方式和过程有详细了解都吗?
- ·作为访问学者大专出国留学有用吗的没有学位证,这种情况能申请买免税车吗?
- ·请问阳台地漏是污水管还是雨水管排污管延伸出的这两条小管是叫什么 有什么作用?
- ·明显用拉丁语翻译软件怎么说?
- ·股东抽逃出资撤逃出资后还是公司股东抽逃出资吗?
- ·一个娃哈哈桶装水真伪查询瓶子能装多少血
- ·中国神运分级基金合并套利套利
- ·日元美元兑日元外汇期货标价
- ·6228481598199288475 69 8农行账号
- ·广发信用卡样样行办理样样行说经过评估,暂时办理不了是什么情况
- ·三峡物流有没有熟的熟白芝麻麻卖
- ·洛克王国从新月赛尔号恶灵觉醒在哪要不要升100级
- ·龙斗士坐骑大全嫦娥公主的最炫酷的坐骑是什么
- ·q四人斗地主背景音乐中3张赖子带4张q大还是6 张9大
- ·lol我蛮子,中期的时候,我去偷,他们总是团,然后输,怎么办。古文我怎么说说他们都不听
- ·DNF在dnf赛丽亚合成传承那,物品合成的武器 可以给账号别的角色交易不?
- ·洛奇英雄传吧70多级怎么赚钱,现在天天刷莱顿爆保护。感觉还行,有没有更好的赚钱方法。这都刷腻了
- ·有人玩乡村度假2游戏吗。
- ·曾经我们工会是一个小工会,不过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比较靠前。求一篇感谢曾经你的认真贴
- ·中原有没有荒漠屠夫和沙漠死神,或者沙漠什么的
- ·奥比岛星梦奇缘攻略隐藏任务
- ·nz古墓魔影英雄高级英雄怎么打?
- ·nvidia geforce 9200m gs驱动能玩星际2吗?特效是不是要开到最低啊?
- ·荒食钓鲤鱼~无双~鲤鱼旗钓鲤鱼怎么配比啊?
- ·usb迷你小风扇扇定上时了怎么办啊
- ·求御宅伴侣怎么求婚汉化版
- ·炉石tb上带练lol大脚会不会封号号阿
- ·鼠标左右键互换键玩射击游戏跟不上节奏
- ·热血传奇安卓版手机版本安卓和苹果怎么相差几个区
- ·悠洋棋牌捕鱼捕鱼有手机版的么
- ·尸如潮水6.求生之路2单人秘籍使用秘籍会封号吗
- ·早晨 天下着雨雨神回复
- ·洛克王国觉醒宠物活动还有什么没出的觉醒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