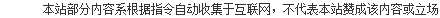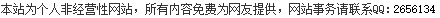跟六大混子江湖打拼20年差不多,也不大,怎么是红眼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6-11-29 20:57
时间:2016-11-29 20:57
开贴声明 本故事顺属虚构 故事中所有人物均与事实无关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本人非小说中的我,此作亦只为博看客一句赞扬,或一句批评 黑道
骗徒的末路 2011年我刑满释放,没有我幻想中的好兄弟开车奔驰带着小弟们迎接,也没有听到管教员在电影里时常会说的那一句“出去好好做人”就这样,走出大门,我恢复了自由。我叫刘伟,1985年生。
到家的时候父母都在,我妈走过来接过我的包袱放下:“快吃饭吧。”我的眼睛湿了。在劳改农场里何曾有人这么温柔过,能听到的只有管教员的吼骂:“排队!出操!吃饭!闭嘴!干活!给我特么的住手!”…..父亲在抽烟,时不时地看看我,眉头皱着,不知是喜是忧。半晌,他问我之后怎么打算,我摇摇头,把碗里最后几口饭扒干净,坐到他身边。 “开家棋牌室吧。”他说。 “好。”
楼主发言:18次 发图:0张 | 更多
第一章 冲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司机,母亲就在家附近开个烟杂店,不富,也不穷。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你口袋里有十块钱,你只能让别人知道你有一块。”这句话我相当受用,所以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平白无故请过一次客。当然,把我正吃着的薯片递给你吃两块是可以的,但是要我买一包给你,对不起,没门儿。 记得04年的时候,我高三,高考就剩五个月了,但那却是我们这群烂木头最好混的日子,为啥?因为也就这样儿了。上课的时候大多在睡觉,下课在打闹,或者在研究哪个妞漂亮,泡不泡得到。等放学了,那才是一天的重头戏——二八杠。 不知道是源于哪个家伙,总之每天放学,学校后街公园的凉亭里就会聚着一群莘莘学子,弹着扑克,叨着一根六毛钱买来的散装红南京香烟吆喝着下注。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并且经常赢,偶尔也会输,但那是我故意的,因为一直赢会引起怀疑。 这天是周四,临近周末,人比较多,二十来个,团团围住一副小小的扑克,前边的人只能蹲着。没烟的腆着脸问有烟的讨烟抽,输得立正的软磨硬泡地问赢钱的借钱翻本。我也经常这样做,并不是我兜里没钱,而是有钱也不给你知道,更不想让你知道我之前都在赢。吴胖子立正了,这家伙独自生活在这里,父母都在外地,所以他的钱比较多一些,此刻他正缠着放大镜借钱:“哎哟…借点了嘛。”
“别吵!我坐庄呢!”放大镜像猴子一样猛地回头看看吴胖子,然后又迅速转回牌上:十面庄,两边,危险。吴胖子见放大镜认真坐庄,无奈把头抬起来在人群中搜索,慢慢地看向我这里。我迅速把头扭开,避免和他四目相对。我讨厌别人问我借钱,虽然我问别人借过。我蹲下身扎到人堆里假模假式丢了两块钱在天门,在天门下大注摸牌的光光一看,八面庄,底牌一粟,好牌!他把牌推进面庄后面,换个角度再一次展开底牌…“次奥!三八一点!”光光把牌一丢。我立刻也跟着喊起了冤来:“哎哟~怎么今天这么倒霉的。”我一边说着一边偷瞄了吴胖子一眼,发现他已经把目光从我这里移开了。 一圈轮庄下来天就黑了,再怎么地也就是学生,到点不回家是要挨老妈拖鞋的,所以一个个地恋恋不舍地走了,但是每一天总会有三四个留下来继续玩,要么就是输急了的,要么就是赢多了不好意思走的,前者可以理解,后者….呵呵,就像刚才放大镜就是一把好庄,赢了四五百,在边上押了两圈,然后趁人多的时候悄悄蹬上他那辆小自行车,一蹿就没影了。他是明智的,只是不够高明。 现在就剩我,光光,龟头,哦对,还有吴胖子,他没借到钱,却还留着看,我当然知道他想干嘛,干脆就先堵住他的嘴:“吴胖子,你立正了还不走啊?我们这儿可都是输钱的。” “我…我看会儿…”吴胖子支吾了两分钟,也走了。我知道在这独自生活的他输到立正就意味着在父母寄钱给他之前他会没饭吃。但是他没饭吃关我p事。 关于赌博,在我后来混在社会上的日子里听一个前辈说过:别相信赌博!赌博就是骗人!其他小辈们一副受用不尽的样子,而我却嗤之以鼻。因为他这样讲只说明一点——他吃过亏。而我,从来没有!所有人在看发哥的赌神的时候只看到他们一个个出手阔绰,料事如神,而我却只看到一点:他们都在作弊。所以那些傻子每天玩二八杠的时候我只在边上飞点小苍蝇,感觉手气好了就坐把庄,等天黑了,估摸着哪个输多了拖着赢得多的不给走的时候,就是我该动的时候了,就比如这次。 光光属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下注也大方,人家几块几块地下,他每把都是十块,今天他立正了,不过他信用比较好,第二天肯定会还钱,所以谁都肯陪着他继续来,谁不想多赢点呢?即使倒过来输回去也算卖个人情嘛,下次有事也好开口。而龟头则不是我们学校的,他是旁边一所技校的,已经实习了,有工资了,所以钱也比较多。呵呵,宰的就是你们俩冲头!我搓搓手跟着他们移到了一个小路灯下。 说道二八杠,中国人都熟悉,有拿扑克玩的,有拿麻将的,牌九的,纸牌九的,不过扑克最方便,我们这的规则是豹子最大,其次二八,三家同点庄家就通赔,通赔是要换庄的,另外就是最后一把通常不开,这是个必要条件。我再次搓了搓手,开始弹牌。 “你还有多少钱,你一直在输,够不够坐庄啊?”光光怀疑地看着我。 “我看看…”我数着手里一把钞票,一百二十:“应该够了吧。”我把钱拿在手里,悄悄瞄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胸口的内袋,里面硬硬的,这里才是我的真家伙。有句话说得好,要赢先学会输。每一轮的前面几把我并不准备赢钱,主要目的是藏牌!这很简单,在黑灯瞎火之下对付这些经验不足的冲头,我简直是绰绰有余:在各自摸牌的时候故意多模一张,然后把有用的牌比如2,比如10用无名指推进袖口里,需要的时候用几个小动作偷换出来,弹牌的时候设法混进去就行。最后一把不开,这就意味着缺了牌也没人会发现,不过藏牌的手法是需要锻炼的,不信你屈起手指往手腕方向靠,能离手腕最近的,不是最长的中指,而是是无名指。
没了?
第二章 近墨者黑 我爸爸是个司机,一直就是个司机,偶尔喜欢打个牌,我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起玩,闯了祸我爸就会说:“跟你说了,别人的事情不关你事!别去做冲头!听到没!”冲头在我们这里是出头鸟或者冤大头的意思,父亲的意思我明白,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去帮别人。 那次藏牌被发现的事尽管我一再掩饰,说这是个玩笑,我藏牌也不会拿出来给别人啊。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在学校传开了,那些二八杠的信徒们见了我就说,呀哈,你这个霉蛋藏牌还输钱啊。我不狡辩了,只是笑笑,然后开玩笑地说你别听光光扯淡,哪有藏牌还老输钱的。我说完了偷偷瞄对方的眼睛,他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看来是怀疑了。庆幸的是我在人多的时候每次赢钱都会藏一些起来,赢两百说赢八十,输十块说输一百,总之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赢少输多就对了。 对于光光,我真没想到还会有人跟钱过不去。这次我为了钞票,顺带想帮光光一把,没想到反而被他也带成了冲头。这厮还在学校里给我到处传,我真的很想把他暴打一顿,无奈我和他身形差不多,他在学校里人缘比我好。算了,不和这群冲头计较,所谓近墨者黑,跟他们混一块儿我也会变蠢,干脆休学,到社会上看看,外面的世界大着呐,等你们垃圾大学毕业了,老子说不定已经吃香喝辣好几年了。 所谓休学并不是我们一贯意义上的休学,而是学校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要有家长签名的申请,在高考前三个月,学生就可以不来学校,自己在家复习。这只是针对差生的做法,省的你们不好好学还捣乱。这倒也合我心意,自此,我一只脚便踏上了江湖。 忘了说了,那时我有个女朋友,叫小文,皮肤黑黑的,和我一样黑,但是眼睛很大,唱歌很好听,特别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要说她,可能是唯一让我愿意在其身上花钱的人。尽管我不会让她知道我藏了三千二百六十块钱,但是平时请她吃个扬州炒饭饭什么的我还是乐意的,因为除了她以外,我没有女人可以碰。十八岁的男人基本性已经成熟了,偏偏法律规定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学校规定不许谈恋爱。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规定未满二十二周岁只许手~淫!人家美国人小孩都会爬了,我们特么还因为带女生开放被学校开除,这算怎么个道道! 不过离开了学校,就没那么多束缚了:记得那是个舒适的夜晚,天气很暖和,穿着新买的一身行头,我跟着邻居山芋就进了一家本市有名的社会青年聚集地,大西洋舞厅,当然,门票是山芋买的。山芋出道比我早,尽管他比我还小两岁。 大西洋舞厅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地方,根本不像父母还有学校老师说的“乌烟瘴气”——红红绿绿的酒瓶子在斑斓的灯光下折射出诱人色彩,一个个妞儿们露出漂亮的长腿,不远处,一个火辣的女郎,带着冷艳妖娆的目光抓着一根钢管拼命扭动着腰肢。我本以为这种场景只会在美国的电影里有……呵呵,都说人间天堂在苏杭,照我看,这里才是天堂。 “恭喜你,出道了。”吵杂的音乐声中,山芋拿起啤酒和我碰了一下。呵呵,这就算出道了,我东张西望,看着这里形形色色的人,正想问山芋为什么有的人在拼命摇头的时候,山芋把他那个土豆般坑坑洼洼的脑袋凑了过来告诉我在这里不要和人乱对眼神,会挨揍的….. 这就是我出道的第一天,拿着一瓶门票附赠的雪花啤酒,我告诉自己,我是个社会人士了。
2011年底,早上十点,我来到棋牌室开始烧水,准备茶叶….这是我的棋牌室,是我现在赖以生存的店子….烧完水我开始扫地,然后把叠在一起的凳子分开。其实昨晚我都打扫过了,其实凳子没必要去叠起来…..十二点半,我从隔壁面馆叫了碗面吃,然后第三次数一下抽屉里留着的一叠用来找零的钱,开始等待我今天的第一波客人——给我今天的生意开张的客人。 2004年初夏的夜晚,大西洋舞厅的空调开得很大,冷气像一阵阵白雾一样吹来,我却大汗淋漓。我从舞池的弹簧地板里走到吧台边上,一个穿着暴露的妞儿就凑了过来:“弟兄啊~~”她穿着暴露,搂着我的手臂,胸部在我手肘上蹭来蹭去:“给我开个张嘛~” “啥?”轰鸣的音乐声中我假装没听到。 “哦哟~弟兄你好坏啊~”她一口本地腔,样子不错,二十出头的样子:“给我开个张嘛~”她晃着我的手臂继续蹭。我在此地混迹有一段日子了,当然知道她是干嘛的,不过我就是要假装没听到,好让她多蹭一会儿。出来混,没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占便宜,有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被别人占便宜。 “多少啊?”我笑着看着她露出的事业线。她一听我问价,干脆就把她的两座大山夹上了我的手臂:“三百一次啦,走吗?” “呵呵,走啊,可是我没钱哦。”我笑着看看她。虽然我接触女人不多,但是对付女人的办法我懂——捣糨糊呗! “矮油~~弟兄你别寻我开心类~走不走嘛。” “呵呵,我倒是想啊,可是我真的没钱。”她一脸失望地要走,我却一把拉住了她:“ 等我哪天有钱了,一定带你走。”
其实大多数小混子身上都是没钱的,进场的门票是当天“带班”的哥们儿买的,嘴上叼的烟是别人过来散的,而混子大多家庭条件不怎么样,父母更是不会拿血汗钱来给他们出来造,所以哪个小混混很大方的话就说明一点:他有女人。混混的女人当然是女混混,女混混年纪轻轻就很现实,出来混知道该混的是钱,所以她们有的坐台卖笑,有的干脆两腿一伸卖起了b来,从这点来看,她们是现实的,不过她们大多很年轻,有的比我还小,多少对爱情抱着幻想,所以大多养着一个口甜舌滑的小混子,每天把皮肉钱给他买烟抽买宵夜吃,甚至给他钱让他带着他的哥们儿出来折腾。我们这儿对这种女人的做法称作“卖b贴草纸”,就是出来卖身倒贴自己男人的意思,混子都乐于交一个这样的女友,又有钱花又有b日,谁不乐意?所以我看看刚才那妞儿不错,于是最后说了那么一句看似戏谑又似乎有点深意的话,至少让人家记住我,说不准哪天就好上了呢? 其实出来混是我一直都有的想法,我从小就比较矮小,上到高中我才一米六几,老被人欺负,看着学校里那些人高马大或者八面玲珑的家伙有事儿了一呼百应无比威风的样子,让我真的羡慕不已,觉得他们像极了某部香港电影里的某个人。于是我开始和试着和这些人交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不希望自己矮小被人欺,也不想因为自己未发育的声道发出的娃娃音而被嘲笑,于是我夹着嗓子说话,把嗓门变粗,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是一副破嗓子,永远唱不了歌。现在想想当时自己是多麽地可笑,我可笑地接近那些人,一心就想变成他们。上天眷顾,在高二高三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身高猛蹿到181,于是班里的几个人就不敢再拍我的头了。 在高三那一年还有一个人对我的人生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我的舅舅,从前在父母长辈的口中,他是个不争气的混子,六年前因伤害罪被判了八年劳教,在我高三那年出来了,据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大哥洋娃娃带着一群兄弟开着车去接他,然后给他钱,给他车,安排他开盘子(地下赌庄),给他介绍女人…..当舅舅神气活现地开着辆帕萨特在我家楼下出现的时候,我开始深信,混,是可以出头的捷径。 现在大家当然都能通过电影知道,出来混拜大哥要有拜师帖,结交兄弟要写金兰贴或者纳投名状。不过我们这早不兴这个了,认识的朋友带去引荐,然后叫声大哥就行;交兄弟,一起喝几次酒认识就行。这个大西洋舞厅我来过不下十次了,认识了不少人,渐渐开始三五成群起来。 “出道”二十天,这是我第一次在社会上打架,原因当然是很无聊的:对上眼了。后来和一个来我这打麻将的给狗看病的兽医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狗是一种社会动物,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如果它们和其它狗四目相对,地位低的那一方会很快把眼睛转开,如果继续对视就是表示不服,那将会是一场恶战。呵呵,原来我们和狗一样。 那天我仍旧穿着我那套行头,黄军裤,丝绸T恤,黑皮鞋,我靠着吧台休息的时候我发现刚才和我们这圈儿人玩的一个女孩子和另一拨人玩的热闹,一个男的蹦迪蹦得来劲,把那个女人抱了起来,那女的很配合,双腿盘着那男的腰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我觉得好笑,心想先和我们玩,马上和另一拨人玩,这不是挑逼么,顾名思义就是挑起事端的婊-子。我心里好笑,就对那男的多看了几眼,没想到就这么对上了。 “朋友,你在看什么?”在迪高休息放慢四的时候,这个留着板寸眯着眼睛的家伙带着几个人走过来了。 “怎么,看的就是你。”我心里虽然有点慌,但是毕竟刚才对上眼的时候就有思想准备了,而且现在山芋他们发现情况不对七八个人也围了过来。 “你跟谁的?”板寸冷冷问了一句,这句话不单是问,也是一种暗示,就是我是道上的,我有人罩,你呢?其实现在回想想都是诈唬人的,照正宗的江湖规矩,问人之前要先自报家门的。不过当时被他一问,我还是语塞了,便回了句关你p事。 板寸扫了眼周围,发现我们的对峙引起了保安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开场子的得罪不起,除非是贵客,否则是不敢在大场子里打架的,于是板寸摆摆头:“出去谈!” 我从小爱踢球,水平不赖,一直是校队的前锋,体力好,要说打架也有点经验,但是江湖经验还是不足的,所以那次打架在一开始还是吃了点亏的,那个板寸见我们刚立定就死样怪气地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和我谈判,谁知道他不知从哪摸出块小砖头一下子飞在我额头上,之后就是一场混战,板寸被我用小刮子给捅了一刀,不知谁喊了声有老派(警-察),所有人立刻作鸟兽散,我是被山芋和另一个叫黄毛给拉走的,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下,板寸捂着肚子也跑了,我的心就定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捅人,其实我从没想过我会捅人,但是脑袋挨了一砖头子,刀在手里,手就不听控制了。但是幸好那把刀小,我捅的时候又捏掉了一段,最多也就伤到肌肉,不过梁子是结下了,以后就是仇人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蠢,一心以为出来混就是求财求面子,现在算是知道了,不论你是不是出来混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怎么才能生财?和气才能生财嘛。 我们这儿是个治安很好的地方,这儿的人也很胆小,所以这里的场子的安检设施都是虚设的,很多时候都不开。恰巧那阵子流行打架带刮子,一般在街上都别在皮带上明目张胆带着,晚上要进场的时候就放进口袋里,人多的时候混进场子很容易,门口的保安什么的忙着给你撕门票呢,没功夫注意你,所以一圈儿人总有几个带着这种小刮子,但是有经验的混混一般不拿来用,因为怕杀红眼,而新的混子不敢用,是因为不会。我?我会用,我是听会的,第一次就扎的恰到好处,没扎出事儿,血流了一地,肯定把那个寸头疼得够呛。 “你还真是结棍,拔出来就捅,我都吓死了。”我们小跑一段估摸着安全了,黄毛就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谁敢跟我牛b我就捅谁,次奥!”尽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把刀拿出来,但是现在捅都捅了。我摸摸脑袋上肿起的一个瘤,上面还破了皮流了点血,心想这也是我第一次挂彩,不过至少在这圈混子里立威了。
第三章 大哥 出来混的都知道这个词,也经常会用到,即使你是个普通人,你也经常会用,那就是“大哥”。大哥就是长兄的意思,在你想象中,他保护你,指引你,不过那也只是在你的想象里了,因为你不能忘了,这个大哥再怎怎么大,他也还是个混子,混子,只求财。 一个多月混下来,我很快就在山芋那圈子人里面确定了大哥的地位,因为我比他们岁数大一点,但我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那次捅人又准又狠,虽然我自己清楚,那次是挨了砖头子有点失控了。我很清楚大哥地位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这种过家家式的“黑社会组织”里,这个大哥是当的不完整的,因为只有权力,没有义务,就和某党一样。以前刚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带班,但是自从那一次我们去拍当时流行的大头贴其他四人都站着就我坐着之后,我就再也没带过班,都是小弟们巴巴地买单,我心里当然别提多痛快。 我这些小弟大多比我小,最小的还在念初中,我的意思是念初中的年纪,而实际上他们早就不去上学了,有的是辍学,有的是长期翘课,你要说这是义务教育,我只能说你见的少了,大多混子都有一个不健康的家庭,有的父母离异,有的自己在外面乱搞,对孩子不管不顾,负责一点的也就回来你就睡,要吃饭管三餐,要钱没有,爱干嘛干嘛。其中黄毛家里最过分,他的妈妈常常会留下张纸条留下几百块钱就跟自己儿子玩失踪。这倒也方便他到处玩,或者有哪个兄弟离家出走可以躲到他家去。 我们混子一般都不受家里待见,和父母争吵甚至和老爸对打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你就会问了,我们混在外面,白天在浴室里睡觉喝茶,晚上在高档消费场所穷折腾,我们一群小b崽子哪来那么多钱造啊,告诉你,有的是办法!我们四五个人,去一家浴场消费,当然这家浴场是提前有人踩过点的。进去以后开个包厢,食品饮料随便点些,吃饱就行,关键是开一个带自动麻将机的包厢,这种包厢一般都有窗户。然后假装没烟,点个一两条中华,把所有帐都挂在一个人手牌上,然后其他人把整条香烟拆散了带走,把空盒子让服务员经过时候能看到,以免引起怀疑。最后一个人就穿着浴室的衣服跳窗逃走,找个回收香烟的地方把烟卖了,然后晚上继续出去折腾。
当然还有更卑劣的,那就是偷。有时我们就三四个个人,其中又有两个是和家里吵过架回不了家的,那上面的办法就行不通了,因为没法回家换衣服总不能穿着浴场的衣服到处逛吧。于是我当大哥的就可以发号施令了。“碟子~给我去买包烟来。”我扔给他二十块钱,当然不是我大方,要请大家抽烟,而是叫那个最小的碟子出去偷。虽然我没亲眼见他偷,但是每一次给二十块让他去买一包烟,他都会带回来四五包烟,外加一两百块钱…我们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每天几百地花,没事寻衅滋事,有事脚底抹油。至少在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赚到了。 有一天山芋突然说要把我引荐给一个大哥,我问他是谁。山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叫大明哥。我一听,心里立刻一阵激动。当时市里面整顿掉了一些“向古惑仔学习”的明目张胆打出名号的“帮会”后,下面的大混子们就调整了政策,一律不提帮会名号,只是跟着他混。这样就不算黑社会了。而这些大混子中最有名的两个之一就是大明哥。山芋因为认识大明哥身边的一个混子,所以把我也介绍了过去,就这样,我被归到了他的旗下。 实际上我跟着这个大哥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也就是跟着他身边几个混子一起出节目,我们这里也叫搭积木,什么叫搭积木呢,呵呵,就是讹。比如三人一块儿打车,到了一地,一个人先下来,假装和车子里的人告别,然后把脚伸到车轮底下…….你懂的,然后就是满地打滚了。 “师傅你怎么开车不看的。” “额我….我没往他那儿轧啊….他自己…” “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没事儿把脚伸到你轮子下边儿?” “额不,我没这意思…” “那你看怎么办吧,人都伤这样儿了。” “那…那送医院。” “我看算了吧。”(这时,有一个人绕过去作记车牌状) “那你看怎么办?” “两千….” 这事儿我都记不清做过几次了,总之桑塔纳轿车是压不坏你的脚的,只不过我有两个脚趾甲到现在还是紫的。
看的正爽呢。。。。。 太监了?
不错啊 继续哦
出来混,一个人的范儿很重要,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气场,用我们这儿的话说叫“出相”:作为一个年轻的混子,不可能很有钱,家里有钱也不会给你,而多数混子家里都很穷。穷没关系,几时有点钱了,置套行头就行:黄军裤,无盖的,七八十,丝绸的,黑底花纹T恤,最多一百,你要方便逃跑,那穿布鞋,你要踢人疼,那穿皮鞋。身上有个手机有包十五块的紫南京,条件好的开辆金鸟助动车,不过这几年不流行了,所以大多混子都打车——排场总要的,你和朋友约见,你骑辆破自行车,改明儿人家就不待见你了。但是前面我说过的,很多混子出来,身上是一分钱都没的。没有咋办,吃霸王餐呗!我们这儿叫“豁水”:打辆车,上车别和司机攀谈,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倒地儿了,开门,甩下一句:“不好意思师傅,没钱!”然后走人,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司机敢怎么样的。不过这个事情我一个人是作不来的,因为我张着一张娃娃脸,吓不住人。 关于我的形象,我还是很在意的,因为好坏我是个大哥,所以我特地给自己加了一些个性化的特征:夹着嗓门把声音变得又粗又破;没事尽量白天不出门,让脸变得苍白吓人,当然这一点是失败的,因为我踢了十几年球,脸太黑了,所以白不了,反而显得苍黄苍黄的,另外因为不见太阳,经常熬夜,我的黑眼圈不论何时都非常明显,这倒让我显得很像个坏人,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人谈判的样子,不能丝丝文文的,要抑扬顿挫摇头晃脑,脸部表情要丰富,孙红雷的&征服&看过没?里边那个开车行的,给那个光头向强哥说情的那家伙,就那样儿!有时和身边的人说话,不能转头,要把脖子扭过去耳语,眼睛盯着别的地方。 04年的5月中旬,我在外边混的有点雏形了,大西洋的混子我基本都认识,也都知道我是大明哥的人,自己手底下也有些小赤佬了。我不禁有点飘飘然,回想那时候在学校里那些看扁我的人,我计划着没事要回去转转,让人知道我刘伟不是盖的。那天我带着山芋和黄毛到学校门口去溜达,在那的一家小店门口蹲着抽烟,一个学校田径队的小子就走了出来:一米八不到一些,脸上有很多挤青春痘留下的疙瘩,坑坑洼洼的,平顶头,眼睛很小,眉毛几乎没有,典型的一张坏人脸。这厮是学校里下一届默认的领庄,也就是“扛把子”,这小子除了和我一届的查b和卢老板,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平时说话不三不四的,他叫阿三。 “怎么,不认我啊?”他和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开腔了。他冷笑一声没搭理我,我甩手一拳就打中了他的眉角。
要说有的人纸老虎真的就是纸做的,这厮挨了我一拳,捂着眉角一副害怕的样子,不过很快镇定下来,掏出手机准备叫人。我伸手把他的手机一掌拍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呐!你要叫小飞是啵?呐!你叫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一个人不敢跟你放肆,那你就要和他的老大玩。我这一手当时在我们这里很流行:先来一拳,对方看你人多不会还手,你也不要继续打,让他把手机掏出来叫人,掏出来你就把它拍掉,再把自己手机递给他,并且告诉他你知道他要打给谁,这一手百试不爽:告诉他你认识他的靠山,而且关系不一般,这样以后他见了你就只能认怂。这不,这厮当场就懵在那里。这时,另一个人走出了校门:“哟~刘伟啊~什么事啊!”我一看,是查b:身材不高,但是很结实,是短跑运动员,白皙的皮肤,大眼浓眉的。学校里出名的美男子,一张嘴巴三寸不烂,在学校里左右逢源,他身边的人清一色是运动员,一个个都像怪物一样。不过还好,我和他关系不错,给个面子是当然的:“没啥事,这小子给我不入调。”其实阿三并没有直接得罪过我,但是就是看他不爽。 “呵呵,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一起的,不算外人。”查b递上来一支烟。 我笑笑,接过烟点上,看了眼阿三就走了。走过校门的时候,另一个人叫住了我:“刘伟!你要不要去培训了?” 我一看,是凯子,他和查b是一起的,练家子,身高一米八五以上,喜欢健身,那副身板和十七八岁的年龄很不相符,但是他偏偏长着一张很秀气漂亮的面孔,一双丹凤眼,要是脸红一点,留把胡子就是活脱脱的关老爷。这厮平时基本不说话,杀气腾腾的样子,现在不知装的什么b,戴着副眼镜,一脸读书人的样子。我们学校和上海某所垃圾大学时挂钩的,基本可以直升,但是要培训,我和凯子都报了那所学校。后来这家伙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但也是这个人,在三年多以后,直接导致我这圈人集体落跑半年,当然,这都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前排占座
第4章 混不灵 在04年五月底的时候,我们这圈混子突然混不灵了,也就是说碰到了瓶颈。因为碟子进工读了。因为这小子一次在公交车上的偷窃由于换手的人没接好手,结果当场被人赃并获,人家看碟子小,也就没有揍,但还是报了警。碟子是有前科的,警察联系了其父母,然后就送了工读。另外一个兄弟也栽了——黄毛:碟子进去了,我们没了经济来源,只好换方法,进浴场,那天又是黄毛负责留守,但是那天我们和以往一样吃饱喝足带着香烟走人的时候,黄毛所在的包厢门口就站好了一个服务生,我们下楼的时候浴场的经理也上去了。后来黄毛告诉我们,那个浴场的经理刚从另一个我们去过的浴场跳槽过去的,而那个浴场,我们去过。最后黄毛被迫叫家人来买单,之后被禁足了一个月。 大明哥是不会来管我们吃喝拉撒的,而且我这样的,他也不会随身带着,所以说我们身上没钱,那是混不下去的。你可能会问我,我那时候不是赢了点钱的吗?我的回答是原本有三千多,现在有五千了,但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另外我还藏了一个手镯,那次在大西洋舞厅蹦迪,边上的卡座上的冲头们都喝大了,有个大姐发疯地舞,结果一个手镯掉在我跟前,我先用脚踩住,捡起迅速塞进口袋,回家一看:pt950. 坐吃是会山空的,我又是大哥,不能不动脑子,讹出租车司机那是不行的,因为我这圈人太小,镇不住。好在办法有很多:我学校的人我动不了脑子,因为有查b在。不过山芋读的旅游中专可以。那几年市里整顿了不良风气,把“拗分”(就是北方人说的切钱,我这里叫抄霸)归类为抢劫,要判刑的。但是下有对策,具体方法和讹出租车有点类似,又不同,不过也可以归类为“搭积木”。就是随便在学校里找个人的茬,然后一群人去堵他,最后问他:“这件事你说怎么解决。”呵呵,懂得人一看就明白了,在法律上,这叫恐吓,敲诈,但是我们的额度很小,能上千我们就笑咧嘴了,何况这个价格是对方自己说的,所以在“敲诈”和“自愿赔偿”之间难以界定。 我们就这样靠拗分过着日子,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叼着根香烟到山芋学校某口蹲着,有的人惹不得,学校里一叫一大群,但有的就好欺负,抽两巴掌马上就说:“大哥我只有两百够不够,不够我再拿条烟。”这样就够了,我有时真想不通,那些冲头怎么就不报警,难道真的信了我那句“信不信我天天来找你”,不报警也就罢了,怎么跑都不敢跑,还巴巴地讲信誉,第二天把钱送上来……有的没钱没烟,干脆把手机给你,回去骗父母说被偷了…真的是败家加冲头!
晚上当然是重要的,为了省钱,我们都在家里吃饭,吃完就出来,有时大明哥会请我们喝茶,我们的据点在大西洋舞厅所在的石头子街,喝茶的时候也就是没事儿聊天,看看有没有什么财路。那时候的道儿已经没那么好混了,夜场都有保安,看场的不再需要那么多,所以有时大家会讨论讨论,讨论的时候我是不说话的,因为我的财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只是想听听别人有没有好的财路。然后看看晚上有没有那个同辈的兄弟肯带班,跟着去混混,能不花钱当然最好了。 就在那一阵子,我们闯了个祸,在拗分的时候出手重了,但是没办法,对方是个刺儿头:那天山芋在学校里找了个冲头,小打了一架,之后就是我出马了。我带着四个兄弟在旅专门口堵了他,看着那小子也带了几个家伙一脸打不死地走了过来。 “你跟谁!你大哥是哪个?”我看他好像不太买账,就先唬他一把。谁知这小子的回答极其不专业:“我没大哥!我就是大哥!”听到这句话我差点跌倒,当然,我们的回答是一阵嘲笑。这小子脸红了,明显是个死要面子的家伙,伸手指着我们吼道:“你他妈又是谁!?” 我没说话,山芋先发飙了:“你再指啊!” “指的就是你!” 我以为山芋会劈头给他一拳,没想到山芋一把抓住他伸着的手指猛地往下一折,啪地一声断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山芋被学校休学,之后禁足在家。 我想,那是我出道以后最破落的日子,没钱,没人…混子是不能天天在家的,第一,父母没好脸色,第二你一阵子不出现,外面的天就变了,当你出现的时候说不定会被人嘲笑。没办法,我只能去找了我的舅舅…
第5章 老江湖 舅舅叫荣荣,在道上有点名气,并不是他本身多厉害,而是他是市里另一个大哥洋娃娃以前最好的几个兄弟之一,当初舅舅犯伤害罪进去也是为了帮洋娃娃办事,这也就是洋娃娃会拉起排场去接他出狱的原因。现在舅舅在北门那里一排隐秘的平方里开地下赌-场,我们这里称作“盘”。 坐在休息室里,我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他面无表情,一只手臂撑在桌上,露出一只在监狱里没事时候自己刺的蝎子。“阿舅,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呵呵”他平淡地笑了一声。“你要混,我也没资格说什么,但是我只能帮你一时,没法帮你一世。” 我不说话,继续灰着脸,但是我心里已经有谱了,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尽管他态度冷漠,但是他绝对不可能不管。 “最近你都在干什么?” “没什么,就在外面玩玩。” “你这是瞎混!出来混不是玩!是赚钱。”舅舅说得很用力,但是我不想听,这种老棺材没事就喜欢对后辈说教,他自己也不想想,不是靠着娃娃哥,他就算个鸡巴! “我也没办法,您以为我不想赚钱吗,我才出来混,哪有您这人脉,要不然我也能做生意啊。”我这话表面上是在抱怨,实际上是在捧他在道上有地位。果然,我一捧,他脸上就有了笑容。 “呵~”他冷笑一声,把自己刚才得意的笑容掩盖了过去。“你学校还去不去?” “不去了,我申请在家复习了。” “呐!这里四千块钱,你拿着用,不过我告诉你!你要靠自己。”他扔下这句话,无非是告诉我,下次别跟他要钱。我心中激动,心想存款又可以增加了。于是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随后想想不对头,我不单需要钱,至少要舅舅给我纸条财路啊。于是我跟舅舅说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得到了一份简单的差事:看场。
舅舅的盘不大,是玩铜子杠的,也就是用牌九玩二八杠。人气还行,我们这里赌-博的风气还是很盛行的,特别是乡下人,没事在家打个麻将胡一把就要上千。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晚饭后呆在盘里,要半路去也行,因为我负责跟债。你要叫我讨债还早了点,我二十岁还没满,脸也没杀气,所以我只能跟债,讨债人人都知道,跟债你未必就懂,其实这差事没啥油水,但是格外简单:赌-场里哪个信誉好的把现金输光了,但是欠了债,我第二天就跟着他去拿钱,去银行也好,去家里也好,总之就是跟他回去,这是很多盘里都有的规矩:信誉好的,金额不大欠着可以,不过第二天会有个看场小弟跟着你回去拿钱。一般这种老板都不大,有点小钱,赌也赌得比较理智,偶尔出格欠了债也不急,我只要跟着回去,一般他都会给点,有的把钱给你,甩个一百说句辛苦了,有的随手给你两包烟。把钱拿回去,给舅舅,他会特殊照顾,给点,也就一两百。舅舅的盘是只收水钱不做庄的,旱涝保收。一般一隔一天开一次,盘里放债的就是舅舅的手下,钱自然也是他在赚,当然有的场子的债务是放给别的团伙做的。我保守估计,舅舅一天水-钱万把总要的,不过这些钱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除了看场放风小弟要给,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有用的,要烧香!你懂的。
也就是这样,我不咸不淡地做了几天,然后参加了高考。你要问我,既然铁了心混社会,为什么参加高考。我也答不上来,可能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成绩出来那天,我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六百七的总分,我也就三百不到,上海那家学校我可以进,因为那家学校也在钻跨省招生的空子。总之我父母很高兴,好歹也是个大学生了。于是我更名正言顺地天天不回家。山芋和黄毛不在的日子,我除了原来那几个兄弟,还认识了溜子,一直到最后散伙,我们都滚在一起。 七月底的时候,黄毛和山芋出现了,而碟子依旧被关在工读学校。不过碟子偷窃的事情没有牵连到任何人,包括经常指使他偷窃的我,还有经常给他接应的黄毛。这说明碟子把事情一个人扛了下来,呵呵,当时我觉得他多拉一个人下水也没啥意思,但是到最后才明白:原来我们这圈人里,最讲义气的,是个贼。舅舅的盘关了,并不是他不想开,而是风声紧了,我们这里治安一向很好,全国靠前,所以经常会整顿,风声一紧,舅舅就收了摊子。有时我想不通,问他,既然白道有关系,那有什么好怕的。但是舅舅反问我:“你觉得拿钱才帮你办事的朋友可靠么?”现在想想,他的决定自然是对的,多做几天也就多赚几万块,但是他一旦载了,这辈子就爬不起来了,老了。 我问过舅舅,怎么不去去找洋娃娃想办法。舅舅冷笑,依旧是那种轻蔑的口气反着我:“你以为我出来洋娃娃为什么对我好?” “因为那时候…” “所以说你嫩!”舅舅没让我说完就打断了我“告诉你!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他这么做,完全是做给他下面的人看的….”我听到这里,脑子就嗡地一声。后面舅舅再说了什么,我却再也没听到了。不过从那天起,我明白了所谓道义,只是一出戏而已。
第一次这么靠近楼主
第6章事端 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中有这么一句话:古惑仔不多事那还叫古惑仔吗?是的,你在香港也好,东北也罢,哪怕在人人胆小的本市,只要是个混子,那就没有不爱无事生非的。当然,现在我是明白的: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无非是在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而已。虽然人人爱惹事端,但是真有了事儿,没一个不害怕的:别人人多怕自己被揍,自己人多怕打死人。 要说出道混,多少还是谦虚点的好,比如给自己起一个不失狠气又不能太牛的绰号。当然,你非要什么龙啊虎啊的,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你,最好不要。就比如几年后我遇到的那个“老朋友”,绰号太牛了,人人都想灭他。绰号牛有啥不好呢?就一点,容易惹人不顺眼:你混好了,人人把你当目标,你混不好,人人踩呼你!所以我给自己的绰号叫小黑,小,说明谦虚,黑,因为我皮肤黑,但是这个黑也会给别人一种心理暗示:手黑,心黑!
七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高中里一起踢球的队友周勇的电话,他说志强在我们学校门口出现了,一起去堵他。我应了一声就起床了。说到这个志强,他是隔壁技校的,比我们小一届,大概是觉得自己很牛逼,于是开始到我们校门口来“立棍儿”,和我们这的女生搭讪,没事还把周勇撞了一下,周勇当然不是什么角色,也就是泡泡妞踢踢球,没事跟在卢老板屁股后面的小崽子,大家都说他是卢老板的儿子。那天志强找了周勇的茬儿,然后报了个名号:北门堂志刚。周勇立刻怂了,刚准备道歉,凯子就来了,劈头就把志刚一拳ko了。志刚这边忽然就有人叫了声师兄,凯子一看是和他一起健身的师弟,于是就走了,志刚白白挨了一拳,火气只能找周勇出,为啥,柿子挑软的捏呗。三天后的下午,志刚带着三个人吧周勇架走了,一顿暴打,还逼着他跳河。最后又是那个凯子出现,志刚才转身走人。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也是听他们复述的。不过我听了就觉得好玩,第一,凯子和周勇本来就关系一般,第二,我和他有过接触,他这人爱耍酷,端着架子不说话,不爱打架,从没在学校里打过,怎么会突然去帮周勇? 想到第三点,我才明白,凯子和周勇当时在追同一个妞!后面的话我不用说了吧?你懂的。不懂?你自己慢慢想吧。 要说追女人,别看周勇其貌不扬,却是有一手的,比那个不说话的凯子好多了,你说哪个女人真会喜欢一个不说话的闷蛋啊?这就是后来我在上海学到的一个词“版子”,男人追女人长相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版子要好,比如大学里你要追一个不认识女生,你得先和她做朋友,等混熟了,开始和她搞暧昧,之后要骗她上床吧?你不能说我们去开房吧,你要约她出来玩,然后和她一起上网,然后拖到她过了点回不了寝室。之后,那自然水到渠成。你要说我猥琐,呵呵,我还觉得你傻逼呢,活该被拒绝,你要说女人装b,我才要说你太监!告诉你,真正的男人就是要给女人台阶下,说白了,就是要给女人装b的空间,否则你就活该撸管子。像那个凯子,自己把b装了,女人要跟了他,那就只能装个鸡巴蛋了。 闲话不说,还是说那个志强,之所以那时候志强可以在学校附近猖狂,那是因为卢老板和查b两尊瘟神为了考体院天天在忙训练。他们俩不在,那就一盘散沙了。后来防暑假了,志强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地泡我们学校高二暑假补习班的美眉了,结果就在校门口被我们堵个正着,那天我下出租车的时候,卢老板正抓着志强的衣领往路边小店的冰箱上撞,周勇在一旁下黒脚。还有几个抓着志强的同伙猛扇。我奔过去踹了志强一脚,谁知志强接着我的脚劲挣脱了,一路狂奔。我追了几步也就停了。又不是我的事儿,我来撑个场面也就得了。后来他们怪我为什么不追,我说志强和我算同门,他们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我当然不会想到,就因为我踹的几脚,后来给我引来一系列的事端。
<span class="count" title="
<span class="count" title="
<span class="count" title="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
骗徒的末路 2011年我刑满释放,没有我幻想中的好兄弟开车奔驰带着小弟们迎接,也没有听到管教员在电影里时常会说的那一句“出去好好做人”就这样,走出大门,我恢复了自由。我叫刘伟,1985年生。
到家的时候父母都在,我妈走过来接过我的包袱放下:“快吃饭吧。”我的眼睛湿了。在劳改农场里何曾有人这么温柔过,能听到的只有管教员的吼骂:“排队!出操!吃饭!闭嘴!干活!给我特么的住手!”…..父亲在抽烟,时不时地看看我,眉头皱着,不知是喜是忧。半晌,他问我之后怎么打算,我摇摇头,把碗里最后几口饭扒干净,坐到他身边。 “开家棋牌室吧。”他说。 “好。”
楼主发言:18次 发图:0张 | 更多
第一章 冲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司机,母亲就在家附近开个烟杂店,不富,也不穷。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你口袋里有十块钱,你只能让别人知道你有一块。”这句话我相当受用,所以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平白无故请过一次客。当然,把我正吃着的薯片递给你吃两块是可以的,但是要我买一包给你,对不起,没门儿。 记得04年的时候,我高三,高考就剩五个月了,但那却是我们这群烂木头最好混的日子,为啥?因为也就这样儿了。上课的时候大多在睡觉,下课在打闹,或者在研究哪个妞漂亮,泡不泡得到。等放学了,那才是一天的重头戏——二八杠。 不知道是源于哪个家伙,总之每天放学,学校后街公园的凉亭里就会聚着一群莘莘学子,弹着扑克,叨着一根六毛钱买来的散装红南京香烟吆喝着下注。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并且经常赢,偶尔也会输,但那是我故意的,因为一直赢会引起怀疑。 这天是周四,临近周末,人比较多,二十来个,团团围住一副小小的扑克,前边的人只能蹲着。没烟的腆着脸问有烟的讨烟抽,输得立正的软磨硬泡地问赢钱的借钱翻本。我也经常这样做,并不是我兜里没钱,而是有钱也不给你知道,更不想让你知道我之前都在赢。吴胖子立正了,这家伙独自生活在这里,父母都在外地,所以他的钱比较多一些,此刻他正缠着放大镜借钱:“哎哟…借点了嘛。”
“别吵!我坐庄呢!”放大镜像猴子一样猛地回头看看吴胖子,然后又迅速转回牌上:十面庄,两边,危险。吴胖子见放大镜认真坐庄,无奈把头抬起来在人群中搜索,慢慢地看向我这里。我迅速把头扭开,避免和他四目相对。我讨厌别人问我借钱,虽然我问别人借过。我蹲下身扎到人堆里假模假式丢了两块钱在天门,在天门下大注摸牌的光光一看,八面庄,底牌一粟,好牌!他把牌推进面庄后面,换个角度再一次展开底牌…“次奥!三八一点!”光光把牌一丢。我立刻也跟着喊起了冤来:“哎哟~怎么今天这么倒霉的。”我一边说着一边偷瞄了吴胖子一眼,发现他已经把目光从我这里移开了。 一圈轮庄下来天就黑了,再怎么地也就是学生,到点不回家是要挨老妈拖鞋的,所以一个个地恋恋不舍地走了,但是每一天总会有三四个留下来继续玩,要么就是输急了的,要么就是赢多了不好意思走的,前者可以理解,后者….呵呵,就像刚才放大镜就是一把好庄,赢了四五百,在边上押了两圈,然后趁人多的时候悄悄蹬上他那辆小自行车,一蹿就没影了。他是明智的,只是不够高明。 现在就剩我,光光,龟头,哦对,还有吴胖子,他没借到钱,却还留着看,我当然知道他想干嘛,干脆就先堵住他的嘴:“吴胖子,你立正了还不走啊?我们这儿可都是输钱的。” “我…我看会儿…”吴胖子支吾了两分钟,也走了。我知道在这独自生活的他输到立正就意味着在父母寄钱给他之前他会没饭吃。但是他没饭吃关我p事。 关于赌博,在我后来混在社会上的日子里听一个前辈说过:别相信赌博!赌博就是骗人!其他小辈们一副受用不尽的样子,而我却嗤之以鼻。因为他这样讲只说明一点——他吃过亏。而我,从来没有!所有人在看发哥的赌神的时候只看到他们一个个出手阔绰,料事如神,而我却只看到一点:他们都在作弊。所以那些傻子每天玩二八杠的时候我只在边上飞点小苍蝇,感觉手气好了就坐把庄,等天黑了,估摸着哪个输多了拖着赢得多的不给走的时候,就是我该动的时候了,就比如这次。 光光属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下注也大方,人家几块几块地下,他每把都是十块,今天他立正了,不过他信用比较好,第二天肯定会还钱,所以谁都肯陪着他继续来,谁不想多赢点呢?即使倒过来输回去也算卖个人情嘛,下次有事也好开口。而龟头则不是我们学校的,他是旁边一所技校的,已经实习了,有工资了,所以钱也比较多。呵呵,宰的就是你们俩冲头!我搓搓手跟着他们移到了一个小路灯下。 说道二八杠,中国人都熟悉,有拿扑克玩的,有拿麻将的,牌九的,纸牌九的,不过扑克最方便,我们这的规则是豹子最大,其次二八,三家同点庄家就通赔,通赔是要换庄的,另外就是最后一把通常不开,这是个必要条件。我再次搓了搓手,开始弹牌。 “你还有多少钱,你一直在输,够不够坐庄啊?”光光怀疑地看着我。 “我看看…”我数着手里一把钞票,一百二十:“应该够了吧。”我把钱拿在手里,悄悄瞄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胸口的内袋,里面硬硬的,这里才是我的真家伙。有句话说得好,要赢先学会输。每一轮的前面几把我并不准备赢钱,主要目的是藏牌!这很简单,在黑灯瞎火之下对付这些经验不足的冲头,我简直是绰绰有余:在各自摸牌的时候故意多模一张,然后把有用的牌比如2,比如10用无名指推进袖口里,需要的时候用几个小动作偷换出来,弹牌的时候设法混进去就行。最后一把不开,这就意味着缺了牌也没人会发现,不过藏牌的手法是需要锻炼的,不信你屈起手指往手腕方向靠,能离手腕最近的,不是最长的中指,而是是无名指。
没了?
第二章 近墨者黑 我爸爸是个司机,一直就是个司机,偶尔喜欢打个牌,我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起玩,闯了祸我爸就会说:“跟你说了,别人的事情不关你事!别去做冲头!听到没!”冲头在我们这里是出头鸟或者冤大头的意思,父亲的意思我明白,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去帮别人。 那次藏牌被发现的事尽管我一再掩饰,说这是个玩笑,我藏牌也不会拿出来给别人啊。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在学校传开了,那些二八杠的信徒们见了我就说,呀哈,你这个霉蛋藏牌还输钱啊。我不狡辩了,只是笑笑,然后开玩笑地说你别听光光扯淡,哪有藏牌还老输钱的。我说完了偷偷瞄对方的眼睛,他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看来是怀疑了。庆幸的是我在人多的时候每次赢钱都会藏一些起来,赢两百说赢八十,输十块说输一百,总之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赢少输多就对了。 对于光光,我真没想到还会有人跟钱过不去。这次我为了钞票,顺带想帮光光一把,没想到反而被他也带成了冲头。这厮还在学校里给我到处传,我真的很想把他暴打一顿,无奈我和他身形差不多,他在学校里人缘比我好。算了,不和这群冲头计较,所谓近墨者黑,跟他们混一块儿我也会变蠢,干脆休学,到社会上看看,外面的世界大着呐,等你们垃圾大学毕业了,老子说不定已经吃香喝辣好几年了。 所谓休学并不是我们一贯意义上的休学,而是学校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要有家长签名的申请,在高考前三个月,学生就可以不来学校,自己在家复习。这只是针对差生的做法,省的你们不好好学还捣乱。这倒也合我心意,自此,我一只脚便踏上了江湖。 忘了说了,那时我有个女朋友,叫小文,皮肤黑黑的,和我一样黑,但是眼睛很大,唱歌很好听,特别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要说她,可能是唯一让我愿意在其身上花钱的人。尽管我不会让她知道我藏了三千二百六十块钱,但是平时请她吃个扬州炒饭饭什么的我还是乐意的,因为除了她以外,我没有女人可以碰。十八岁的男人基本性已经成熟了,偏偏法律规定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学校规定不许谈恋爱。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规定未满二十二周岁只许手~淫!人家美国人小孩都会爬了,我们特么还因为带女生开放被学校开除,这算怎么个道道! 不过离开了学校,就没那么多束缚了:记得那是个舒适的夜晚,天气很暖和,穿着新买的一身行头,我跟着邻居山芋就进了一家本市有名的社会青年聚集地,大西洋舞厅,当然,门票是山芋买的。山芋出道比我早,尽管他比我还小两岁。 大西洋舞厅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地方,根本不像父母还有学校老师说的“乌烟瘴气”——红红绿绿的酒瓶子在斑斓的灯光下折射出诱人色彩,一个个妞儿们露出漂亮的长腿,不远处,一个火辣的女郎,带着冷艳妖娆的目光抓着一根钢管拼命扭动着腰肢。我本以为这种场景只会在美国的电影里有……呵呵,都说人间天堂在苏杭,照我看,这里才是天堂。 “恭喜你,出道了。”吵杂的音乐声中,山芋拿起啤酒和我碰了一下。呵呵,这就算出道了,我东张西望,看着这里形形色色的人,正想问山芋为什么有的人在拼命摇头的时候,山芋把他那个土豆般坑坑洼洼的脑袋凑了过来告诉我在这里不要和人乱对眼神,会挨揍的….. 这就是我出道的第一天,拿着一瓶门票附赠的雪花啤酒,我告诉自己,我是个社会人士了。
2011年底,早上十点,我来到棋牌室开始烧水,准备茶叶….这是我的棋牌室,是我现在赖以生存的店子….烧完水我开始扫地,然后把叠在一起的凳子分开。其实昨晚我都打扫过了,其实凳子没必要去叠起来…..十二点半,我从隔壁面馆叫了碗面吃,然后第三次数一下抽屉里留着的一叠用来找零的钱,开始等待我今天的第一波客人——给我今天的生意开张的客人。 2004年初夏的夜晚,大西洋舞厅的空调开得很大,冷气像一阵阵白雾一样吹来,我却大汗淋漓。我从舞池的弹簧地板里走到吧台边上,一个穿着暴露的妞儿就凑了过来:“弟兄啊~~”她穿着暴露,搂着我的手臂,胸部在我手肘上蹭来蹭去:“给我开个张嘛~” “啥?”轰鸣的音乐声中我假装没听到。 “哦哟~弟兄你好坏啊~”她一口本地腔,样子不错,二十出头的样子:“给我开个张嘛~”她晃着我的手臂继续蹭。我在此地混迹有一段日子了,当然知道她是干嘛的,不过我就是要假装没听到,好让她多蹭一会儿。出来混,没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占便宜,有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被别人占便宜。 “多少啊?”我笑着看着她露出的事业线。她一听我问价,干脆就把她的两座大山夹上了我的手臂:“三百一次啦,走吗?” “呵呵,走啊,可是我没钱哦。”我笑着看看她。虽然我接触女人不多,但是对付女人的办法我懂——捣糨糊呗! “矮油~~弟兄你别寻我开心类~走不走嘛。” “呵呵,我倒是想啊,可是我真的没钱。”她一脸失望地要走,我却一把拉住了她:“ 等我哪天有钱了,一定带你走。”
其实大多数小混子身上都是没钱的,进场的门票是当天“带班”的哥们儿买的,嘴上叼的烟是别人过来散的,而混子大多家庭条件不怎么样,父母更是不会拿血汗钱来给他们出来造,所以哪个小混混很大方的话就说明一点:他有女人。混混的女人当然是女混混,女混混年纪轻轻就很现实,出来混知道该混的是钱,所以她们有的坐台卖笑,有的干脆两腿一伸卖起了b来,从这点来看,她们是现实的,不过她们大多很年轻,有的比我还小,多少对爱情抱着幻想,所以大多养着一个口甜舌滑的小混子,每天把皮肉钱给他买烟抽买宵夜吃,甚至给他钱让他带着他的哥们儿出来折腾。我们这儿对这种女人的做法称作“卖b贴草纸”,就是出来卖身倒贴自己男人的意思,混子都乐于交一个这样的女友,又有钱花又有b日,谁不乐意?所以我看看刚才那妞儿不错,于是最后说了那么一句看似戏谑又似乎有点深意的话,至少让人家记住我,说不准哪天就好上了呢? 其实出来混是我一直都有的想法,我从小就比较矮小,上到高中我才一米六几,老被人欺负,看着学校里那些人高马大或者八面玲珑的家伙有事儿了一呼百应无比威风的样子,让我真的羡慕不已,觉得他们像极了某部香港电影里的某个人。于是我开始和试着和这些人交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不希望自己矮小被人欺,也不想因为自己未发育的声道发出的娃娃音而被嘲笑,于是我夹着嗓子说话,把嗓门变粗,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是一副破嗓子,永远唱不了歌。现在想想当时自己是多麽地可笑,我可笑地接近那些人,一心就想变成他们。上天眷顾,在高二高三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身高猛蹿到181,于是班里的几个人就不敢再拍我的头了。 在高三那一年还有一个人对我的人生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我的舅舅,从前在父母长辈的口中,他是个不争气的混子,六年前因伤害罪被判了八年劳教,在我高三那年出来了,据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大哥洋娃娃带着一群兄弟开着车去接他,然后给他钱,给他车,安排他开盘子(地下赌庄),给他介绍女人…..当舅舅神气活现地开着辆帕萨特在我家楼下出现的时候,我开始深信,混,是可以出头的捷径。 现在大家当然都能通过电影知道,出来混拜大哥要有拜师帖,结交兄弟要写金兰贴或者纳投名状。不过我们这早不兴这个了,认识的朋友带去引荐,然后叫声大哥就行;交兄弟,一起喝几次酒认识就行。这个大西洋舞厅我来过不下十次了,认识了不少人,渐渐开始三五成群起来。 “出道”二十天,这是我第一次在社会上打架,原因当然是很无聊的:对上眼了。后来和一个来我这打麻将的给狗看病的兽医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狗是一种社会动物,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如果它们和其它狗四目相对,地位低的那一方会很快把眼睛转开,如果继续对视就是表示不服,那将会是一场恶战。呵呵,原来我们和狗一样。 那天我仍旧穿着我那套行头,黄军裤,丝绸T恤,黑皮鞋,我靠着吧台休息的时候我发现刚才和我们这圈儿人玩的一个女孩子和另一拨人玩的热闹,一个男的蹦迪蹦得来劲,把那个女人抱了起来,那女的很配合,双腿盘着那男的腰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我觉得好笑,心想先和我们玩,马上和另一拨人玩,这不是挑逼么,顾名思义就是挑起事端的婊-子。我心里好笑,就对那男的多看了几眼,没想到就这么对上了。 “朋友,你在看什么?”在迪高休息放慢四的时候,这个留着板寸眯着眼睛的家伙带着几个人走过来了。 “怎么,看的就是你。”我心里虽然有点慌,但是毕竟刚才对上眼的时候就有思想准备了,而且现在山芋他们发现情况不对七八个人也围了过来。 “你跟谁的?”板寸冷冷问了一句,这句话不单是问,也是一种暗示,就是我是道上的,我有人罩,你呢?其实现在回想想都是诈唬人的,照正宗的江湖规矩,问人之前要先自报家门的。不过当时被他一问,我还是语塞了,便回了句关你p事。 板寸扫了眼周围,发现我们的对峙引起了保安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开场子的得罪不起,除非是贵客,否则是不敢在大场子里打架的,于是板寸摆摆头:“出去谈!” 我从小爱踢球,水平不赖,一直是校队的前锋,体力好,要说打架也有点经验,但是江湖经验还是不足的,所以那次打架在一开始还是吃了点亏的,那个板寸见我们刚立定就死样怪气地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和我谈判,谁知道他不知从哪摸出块小砖头一下子飞在我额头上,之后就是一场混战,板寸被我用小刮子给捅了一刀,不知谁喊了声有老派(警-察),所有人立刻作鸟兽散,我是被山芋和另一个叫黄毛给拉走的,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下,板寸捂着肚子也跑了,我的心就定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捅人,其实我从没想过我会捅人,但是脑袋挨了一砖头子,刀在手里,手就不听控制了。但是幸好那把刀小,我捅的时候又捏掉了一段,最多也就伤到肌肉,不过梁子是结下了,以后就是仇人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蠢,一心以为出来混就是求财求面子,现在算是知道了,不论你是不是出来混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怎么才能生财?和气才能生财嘛。 我们这儿是个治安很好的地方,这儿的人也很胆小,所以这里的场子的安检设施都是虚设的,很多时候都不开。恰巧那阵子流行打架带刮子,一般在街上都别在皮带上明目张胆带着,晚上要进场的时候就放进口袋里,人多的时候混进场子很容易,门口的保安什么的忙着给你撕门票呢,没功夫注意你,所以一圈儿人总有几个带着这种小刮子,但是有经验的混混一般不拿来用,因为怕杀红眼,而新的混子不敢用,是因为不会。我?我会用,我是听会的,第一次就扎的恰到好处,没扎出事儿,血流了一地,肯定把那个寸头疼得够呛。 “你还真是结棍,拔出来就捅,我都吓死了。”我们小跑一段估摸着安全了,黄毛就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谁敢跟我牛b我就捅谁,次奥!”尽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把刀拿出来,但是现在捅都捅了。我摸摸脑袋上肿起的一个瘤,上面还破了皮流了点血,心想这也是我第一次挂彩,不过至少在这圈混子里立威了。
第三章 大哥 出来混的都知道这个词,也经常会用到,即使你是个普通人,你也经常会用,那就是“大哥”。大哥就是长兄的意思,在你想象中,他保护你,指引你,不过那也只是在你的想象里了,因为你不能忘了,这个大哥再怎怎么大,他也还是个混子,混子,只求财。 一个多月混下来,我很快就在山芋那圈子人里面确定了大哥的地位,因为我比他们岁数大一点,但我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那次捅人又准又狠,虽然我自己清楚,那次是挨了砖头子有点失控了。我很清楚大哥地位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这种过家家式的“黑社会组织”里,这个大哥是当的不完整的,因为只有权力,没有义务,就和某党一样。以前刚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带班,但是自从那一次我们去拍当时流行的大头贴其他四人都站着就我坐着之后,我就再也没带过班,都是小弟们巴巴地买单,我心里当然别提多痛快。 我这些小弟大多比我小,最小的还在念初中,我的意思是念初中的年纪,而实际上他们早就不去上学了,有的是辍学,有的是长期翘课,你要说这是义务教育,我只能说你见的少了,大多混子都有一个不健康的家庭,有的父母离异,有的自己在外面乱搞,对孩子不管不顾,负责一点的也就回来你就睡,要吃饭管三餐,要钱没有,爱干嘛干嘛。其中黄毛家里最过分,他的妈妈常常会留下张纸条留下几百块钱就跟自己儿子玩失踪。这倒也方便他到处玩,或者有哪个兄弟离家出走可以躲到他家去。 我们混子一般都不受家里待见,和父母争吵甚至和老爸对打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你就会问了,我们混在外面,白天在浴室里睡觉喝茶,晚上在高档消费场所穷折腾,我们一群小b崽子哪来那么多钱造啊,告诉你,有的是办法!我们四五个人,去一家浴场消费,当然这家浴场是提前有人踩过点的。进去以后开个包厢,食品饮料随便点些,吃饱就行,关键是开一个带自动麻将机的包厢,这种包厢一般都有窗户。然后假装没烟,点个一两条中华,把所有帐都挂在一个人手牌上,然后其他人把整条香烟拆散了带走,把空盒子让服务员经过时候能看到,以免引起怀疑。最后一个人就穿着浴室的衣服跳窗逃走,找个回收香烟的地方把烟卖了,然后晚上继续出去折腾。
当然还有更卑劣的,那就是偷。有时我们就三四个个人,其中又有两个是和家里吵过架回不了家的,那上面的办法就行不通了,因为没法回家换衣服总不能穿着浴场的衣服到处逛吧。于是我当大哥的就可以发号施令了。“碟子~给我去买包烟来。”我扔给他二十块钱,当然不是我大方,要请大家抽烟,而是叫那个最小的碟子出去偷。虽然我没亲眼见他偷,但是每一次给二十块让他去买一包烟,他都会带回来四五包烟,外加一两百块钱…我们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每天几百地花,没事寻衅滋事,有事脚底抹油。至少在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赚到了。 有一天山芋突然说要把我引荐给一个大哥,我问他是谁。山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叫大明哥。我一听,心里立刻一阵激动。当时市里面整顿掉了一些“向古惑仔学习”的明目张胆打出名号的“帮会”后,下面的大混子们就调整了政策,一律不提帮会名号,只是跟着他混。这样就不算黑社会了。而这些大混子中最有名的两个之一就是大明哥。山芋因为认识大明哥身边的一个混子,所以把我也介绍了过去,就这样,我被归到了他的旗下。 实际上我跟着这个大哥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也就是跟着他身边几个混子一起出节目,我们这里也叫搭积木,什么叫搭积木呢,呵呵,就是讹。比如三人一块儿打车,到了一地,一个人先下来,假装和车子里的人告别,然后把脚伸到车轮底下…….你懂的,然后就是满地打滚了。 “师傅你怎么开车不看的。” “额我….我没往他那儿轧啊….他自己…” “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没事儿把脚伸到你轮子下边儿?” “额不,我没这意思…” “那你看怎么办吧,人都伤这样儿了。” “那…那送医院。” “我看算了吧。”(这时,有一个人绕过去作记车牌状) “那你看怎么办?” “两千….” 这事儿我都记不清做过几次了,总之桑塔纳轿车是压不坏你的脚的,只不过我有两个脚趾甲到现在还是紫的。
看的正爽呢。。。。。 太监了?
不错啊 继续哦
出来混,一个人的范儿很重要,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气场,用我们这儿的话说叫“出相”:作为一个年轻的混子,不可能很有钱,家里有钱也不会给你,而多数混子家里都很穷。穷没关系,几时有点钱了,置套行头就行:黄军裤,无盖的,七八十,丝绸的,黑底花纹T恤,最多一百,你要方便逃跑,那穿布鞋,你要踢人疼,那穿皮鞋。身上有个手机有包十五块的紫南京,条件好的开辆金鸟助动车,不过这几年不流行了,所以大多混子都打车——排场总要的,你和朋友约见,你骑辆破自行车,改明儿人家就不待见你了。但是前面我说过的,很多混子出来,身上是一分钱都没的。没有咋办,吃霸王餐呗!我们这儿叫“豁水”:打辆车,上车别和司机攀谈,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倒地儿了,开门,甩下一句:“不好意思师傅,没钱!”然后走人,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司机敢怎么样的。不过这个事情我一个人是作不来的,因为我张着一张娃娃脸,吓不住人。 关于我的形象,我还是很在意的,因为好坏我是个大哥,所以我特地给自己加了一些个性化的特征:夹着嗓门把声音变得又粗又破;没事尽量白天不出门,让脸变得苍白吓人,当然这一点是失败的,因为我踢了十几年球,脸太黑了,所以白不了,反而显得苍黄苍黄的,另外因为不见太阳,经常熬夜,我的黑眼圈不论何时都非常明显,这倒让我显得很像个坏人,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人谈判的样子,不能丝丝文文的,要抑扬顿挫摇头晃脑,脸部表情要丰富,孙红雷的&征服&看过没?里边那个开车行的,给那个光头向强哥说情的那家伙,就那样儿!有时和身边的人说话,不能转头,要把脖子扭过去耳语,眼睛盯着别的地方。 04年的5月中旬,我在外边混的有点雏形了,大西洋的混子我基本都认识,也都知道我是大明哥的人,自己手底下也有些小赤佬了。我不禁有点飘飘然,回想那时候在学校里那些看扁我的人,我计划着没事要回去转转,让人知道我刘伟不是盖的。那天我带着山芋和黄毛到学校门口去溜达,在那的一家小店门口蹲着抽烟,一个学校田径队的小子就走了出来:一米八不到一些,脸上有很多挤青春痘留下的疙瘩,坑坑洼洼的,平顶头,眼睛很小,眉毛几乎没有,典型的一张坏人脸。这厮是学校里下一届默认的领庄,也就是“扛把子”,这小子除了和我一届的查b和卢老板,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平时说话不三不四的,他叫阿三。 “怎么,不认我啊?”他和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开腔了。他冷笑一声没搭理我,我甩手一拳就打中了他的眉角。
要说有的人纸老虎真的就是纸做的,这厮挨了我一拳,捂着眉角一副害怕的样子,不过很快镇定下来,掏出手机准备叫人。我伸手把他的手机一掌拍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呐!你要叫小飞是啵?呐!你叫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一个人不敢跟你放肆,那你就要和他的老大玩。我这一手当时在我们这里很流行:先来一拳,对方看你人多不会还手,你也不要继续打,让他把手机掏出来叫人,掏出来你就把它拍掉,再把自己手机递给他,并且告诉他你知道他要打给谁,这一手百试不爽:告诉他你认识他的靠山,而且关系不一般,这样以后他见了你就只能认怂。这不,这厮当场就懵在那里。这时,另一个人走出了校门:“哟~刘伟啊~什么事啊!”我一看,是查b:身材不高,但是很结实,是短跑运动员,白皙的皮肤,大眼浓眉的。学校里出名的美男子,一张嘴巴三寸不烂,在学校里左右逢源,他身边的人清一色是运动员,一个个都像怪物一样。不过还好,我和他关系不错,给个面子是当然的:“没啥事,这小子给我不入调。”其实阿三并没有直接得罪过我,但是就是看他不爽。 “呵呵,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一起的,不算外人。”查b递上来一支烟。 我笑笑,接过烟点上,看了眼阿三就走了。走过校门的时候,另一个人叫住了我:“刘伟!你要不要去培训了?” 我一看,是凯子,他和查b是一起的,练家子,身高一米八五以上,喜欢健身,那副身板和十七八岁的年龄很不相符,但是他偏偏长着一张很秀气漂亮的面孔,一双丹凤眼,要是脸红一点,留把胡子就是活脱脱的关老爷。这厮平时基本不说话,杀气腾腾的样子,现在不知装的什么b,戴着副眼镜,一脸读书人的样子。我们学校和上海某所垃圾大学时挂钩的,基本可以直升,但是要培训,我和凯子都报了那所学校。后来这家伙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但也是这个人,在三年多以后,直接导致我这圈人集体落跑半年,当然,这都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前排占座
第4章 混不灵 在04年五月底的时候,我们这圈混子突然混不灵了,也就是说碰到了瓶颈。因为碟子进工读了。因为这小子一次在公交车上的偷窃由于换手的人没接好手,结果当场被人赃并获,人家看碟子小,也就没有揍,但还是报了警。碟子是有前科的,警察联系了其父母,然后就送了工读。另外一个兄弟也栽了——黄毛:碟子进去了,我们没了经济来源,只好换方法,进浴场,那天又是黄毛负责留守,但是那天我们和以往一样吃饱喝足带着香烟走人的时候,黄毛所在的包厢门口就站好了一个服务生,我们下楼的时候浴场的经理也上去了。后来黄毛告诉我们,那个浴场的经理刚从另一个我们去过的浴场跳槽过去的,而那个浴场,我们去过。最后黄毛被迫叫家人来买单,之后被禁足了一个月。 大明哥是不会来管我们吃喝拉撒的,而且我这样的,他也不会随身带着,所以说我们身上没钱,那是混不下去的。你可能会问我,我那时候不是赢了点钱的吗?我的回答是原本有三千多,现在有五千了,但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另外我还藏了一个手镯,那次在大西洋舞厅蹦迪,边上的卡座上的冲头们都喝大了,有个大姐发疯地舞,结果一个手镯掉在我跟前,我先用脚踩住,捡起迅速塞进口袋,回家一看:pt950. 坐吃是会山空的,我又是大哥,不能不动脑子,讹出租车司机那是不行的,因为我这圈人太小,镇不住。好在办法有很多:我学校的人我动不了脑子,因为有查b在。不过山芋读的旅游中专可以。那几年市里整顿了不良风气,把“拗分”(就是北方人说的切钱,我这里叫抄霸)归类为抢劫,要判刑的。但是下有对策,具体方法和讹出租车有点类似,又不同,不过也可以归类为“搭积木”。就是随便在学校里找个人的茬,然后一群人去堵他,最后问他:“这件事你说怎么解决。”呵呵,懂得人一看就明白了,在法律上,这叫恐吓,敲诈,但是我们的额度很小,能上千我们就笑咧嘴了,何况这个价格是对方自己说的,所以在“敲诈”和“自愿赔偿”之间难以界定。 我们就这样靠拗分过着日子,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叼着根香烟到山芋学校某口蹲着,有的人惹不得,学校里一叫一大群,但有的就好欺负,抽两巴掌马上就说:“大哥我只有两百够不够,不够我再拿条烟。”这样就够了,我有时真想不通,那些冲头怎么就不报警,难道真的信了我那句“信不信我天天来找你”,不报警也就罢了,怎么跑都不敢跑,还巴巴地讲信誉,第二天把钱送上来……有的没钱没烟,干脆把手机给你,回去骗父母说被偷了…真的是败家加冲头!
晚上当然是重要的,为了省钱,我们都在家里吃饭,吃完就出来,有时大明哥会请我们喝茶,我们的据点在大西洋舞厅所在的石头子街,喝茶的时候也就是没事儿聊天,看看有没有什么财路。那时候的道儿已经没那么好混了,夜场都有保安,看场的不再需要那么多,所以有时大家会讨论讨论,讨论的时候我是不说话的,因为我的财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只是想听听别人有没有好的财路。然后看看晚上有没有那个同辈的兄弟肯带班,跟着去混混,能不花钱当然最好了。 就在那一阵子,我们闯了个祸,在拗分的时候出手重了,但是没办法,对方是个刺儿头:那天山芋在学校里找了个冲头,小打了一架,之后就是我出马了。我带着四个兄弟在旅专门口堵了他,看着那小子也带了几个家伙一脸打不死地走了过来。 “你跟谁!你大哥是哪个?”我看他好像不太买账,就先唬他一把。谁知这小子的回答极其不专业:“我没大哥!我就是大哥!”听到这句话我差点跌倒,当然,我们的回答是一阵嘲笑。这小子脸红了,明显是个死要面子的家伙,伸手指着我们吼道:“你他妈又是谁!?” 我没说话,山芋先发飙了:“你再指啊!” “指的就是你!” 我以为山芋会劈头给他一拳,没想到山芋一把抓住他伸着的手指猛地往下一折,啪地一声断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山芋被学校休学,之后禁足在家。 我想,那是我出道以后最破落的日子,没钱,没人…混子是不能天天在家的,第一,父母没好脸色,第二你一阵子不出现,外面的天就变了,当你出现的时候说不定会被人嘲笑。没办法,我只能去找了我的舅舅…
第5章 老江湖 舅舅叫荣荣,在道上有点名气,并不是他本身多厉害,而是他是市里另一个大哥洋娃娃以前最好的几个兄弟之一,当初舅舅犯伤害罪进去也是为了帮洋娃娃办事,这也就是洋娃娃会拉起排场去接他出狱的原因。现在舅舅在北门那里一排隐秘的平方里开地下赌-场,我们这里称作“盘”。 坐在休息室里,我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他面无表情,一只手臂撑在桌上,露出一只在监狱里没事时候自己刺的蝎子。“阿舅,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呵呵”他平淡地笑了一声。“你要混,我也没资格说什么,但是我只能帮你一时,没法帮你一世。” 我不说话,继续灰着脸,但是我心里已经有谱了,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尽管他态度冷漠,但是他绝对不可能不管。 “最近你都在干什么?” “没什么,就在外面玩玩。” “你这是瞎混!出来混不是玩!是赚钱。”舅舅说得很用力,但是我不想听,这种老棺材没事就喜欢对后辈说教,他自己也不想想,不是靠着娃娃哥,他就算个鸡巴! “我也没办法,您以为我不想赚钱吗,我才出来混,哪有您这人脉,要不然我也能做生意啊。”我这话表面上是在抱怨,实际上是在捧他在道上有地位。果然,我一捧,他脸上就有了笑容。 “呵~”他冷笑一声,把自己刚才得意的笑容掩盖了过去。“你学校还去不去?” “不去了,我申请在家复习了。” “呐!这里四千块钱,你拿着用,不过我告诉你!你要靠自己。”他扔下这句话,无非是告诉我,下次别跟他要钱。我心中激动,心想存款又可以增加了。于是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随后想想不对头,我不单需要钱,至少要舅舅给我纸条财路啊。于是我跟舅舅说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得到了一份简单的差事:看场。
舅舅的盘不大,是玩铜子杠的,也就是用牌九玩二八杠。人气还行,我们这里赌-博的风气还是很盛行的,特别是乡下人,没事在家打个麻将胡一把就要上千。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晚饭后呆在盘里,要半路去也行,因为我负责跟债。你要叫我讨债还早了点,我二十岁还没满,脸也没杀气,所以我只能跟债,讨债人人都知道,跟债你未必就懂,其实这差事没啥油水,但是格外简单:赌-场里哪个信誉好的把现金输光了,但是欠了债,我第二天就跟着他去拿钱,去银行也好,去家里也好,总之就是跟他回去,这是很多盘里都有的规矩:信誉好的,金额不大欠着可以,不过第二天会有个看场小弟跟着你回去拿钱。一般这种老板都不大,有点小钱,赌也赌得比较理智,偶尔出格欠了债也不急,我只要跟着回去,一般他都会给点,有的把钱给你,甩个一百说句辛苦了,有的随手给你两包烟。把钱拿回去,给舅舅,他会特殊照顾,给点,也就一两百。舅舅的盘是只收水钱不做庄的,旱涝保收。一般一隔一天开一次,盘里放债的就是舅舅的手下,钱自然也是他在赚,当然有的场子的债务是放给别的团伙做的。我保守估计,舅舅一天水-钱万把总要的,不过这些钱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除了看场放风小弟要给,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有用的,要烧香!你懂的。
也就是这样,我不咸不淡地做了几天,然后参加了高考。你要问我,既然铁了心混社会,为什么参加高考。我也答不上来,可能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成绩出来那天,我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六百七的总分,我也就三百不到,上海那家学校我可以进,因为那家学校也在钻跨省招生的空子。总之我父母很高兴,好歹也是个大学生了。于是我更名正言顺地天天不回家。山芋和黄毛不在的日子,我除了原来那几个兄弟,还认识了溜子,一直到最后散伙,我们都滚在一起。 七月底的时候,黄毛和山芋出现了,而碟子依旧被关在工读学校。不过碟子偷窃的事情没有牵连到任何人,包括经常指使他偷窃的我,还有经常给他接应的黄毛。这说明碟子把事情一个人扛了下来,呵呵,当时我觉得他多拉一个人下水也没啥意思,但是到最后才明白:原来我们这圈人里,最讲义气的,是个贼。舅舅的盘关了,并不是他不想开,而是风声紧了,我们这里治安一向很好,全国靠前,所以经常会整顿,风声一紧,舅舅就收了摊子。有时我想不通,问他,既然白道有关系,那有什么好怕的。但是舅舅反问我:“你觉得拿钱才帮你办事的朋友可靠么?”现在想想,他的决定自然是对的,多做几天也就多赚几万块,但是他一旦载了,这辈子就爬不起来了,老了。 我问过舅舅,怎么不去去找洋娃娃想办法。舅舅冷笑,依旧是那种轻蔑的口气反着我:“你以为我出来洋娃娃为什么对我好?” “因为那时候…” “所以说你嫩!”舅舅没让我说完就打断了我“告诉你!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他这么做,完全是做给他下面的人看的….”我听到这里,脑子就嗡地一声。后面舅舅再说了什么,我却再也没听到了。不过从那天起,我明白了所谓道义,只是一出戏而已。
第一次这么靠近楼主
第6章事端 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中有这么一句话:古惑仔不多事那还叫古惑仔吗?是的,你在香港也好,东北也罢,哪怕在人人胆小的本市,只要是个混子,那就没有不爱无事生非的。当然,现在我是明白的: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无非是在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而已。虽然人人爱惹事端,但是真有了事儿,没一个不害怕的:别人人多怕自己被揍,自己人多怕打死人。 要说出道混,多少还是谦虚点的好,比如给自己起一个不失狠气又不能太牛的绰号。当然,你非要什么龙啊虎啊的,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你,最好不要。就比如几年后我遇到的那个“老朋友”,绰号太牛了,人人都想灭他。绰号牛有啥不好呢?就一点,容易惹人不顺眼:你混好了,人人把你当目标,你混不好,人人踩呼你!所以我给自己的绰号叫小黑,小,说明谦虚,黑,因为我皮肤黑,但是这个黑也会给别人一种心理暗示:手黑,心黑!
七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高中里一起踢球的队友周勇的电话,他说志强在我们学校门口出现了,一起去堵他。我应了一声就起床了。说到这个志强,他是隔壁技校的,比我们小一届,大概是觉得自己很牛逼,于是开始到我们校门口来“立棍儿”,和我们这的女生搭讪,没事还把周勇撞了一下,周勇当然不是什么角色,也就是泡泡妞踢踢球,没事跟在卢老板屁股后面的小崽子,大家都说他是卢老板的儿子。那天志强找了周勇的茬儿,然后报了个名号:北门堂志刚。周勇立刻怂了,刚准备道歉,凯子就来了,劈头就把志刚一拳ko了。志刚这边忽然就有人叫了声师兄,凯子一看是和他一起健身的师弟,于是就走了,志刚白白挨了一拳,火气只能找周勇出,为啥,柿子挑软的捏呗。三天后的下午,志刚带着三个人吧周勇架走了,一顿暴打,还逼着他跳河。最后又是那个凯子出现,志刚才转身走人。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也是听他们复述的。不过我听了就觉得好玩,第一,凯子和周勇本来就关系一般,第二,我和他有过接触,他这人爱耍酷,端着架子不说话,不爱打架,从没在学校里打过,怎么会突然去帮周勇? 想到第三点,我才明白,凯子和周勇当时在追同一个妞!后面的话我不用说了吧?你懂的。不懂?你自己慢慢想吧。 要说追女人,别看周勇其貌不扬,却是有一手的,比那个不说话的凯子好多了,你说哪个女人真会喜欢一个不说话的闷蛋啊?这就是后来我在上海学到的一个词“版子”,男人追女人长相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版子要好,比如大学里你要追一个不认识女生,你得先和她做朋友,等混熟了,开始和她搞暧昧,之后要骗她上床吧?你不能说我们去开房吧,你要约她出来玩,然后和她一起上网,然后拖到她过了点回不了寝室。之后,那自然水到渠成。你要说我猥琐,呵呵,我还觉得你傻逼呢,活该被拒绝,你要说女人装b,我才要说你太监!告诉你,真正的男人就是要给女人台阶下,说白了,就是要给女人装b的空间,否则你就活该撸管子。像那个凯子,自己把b装了,女人要跟了他,那就只能装个鸡巴蛋了。 闲话不说,还是说那个志强,之所以那时候志强可以在学校附近猖狂,那是因为卢老板和查b两尊瘟神为了考体院天天在忙训练。他们俩不在,那就一盘散沙了。后来防暑假了,志强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地泡我们学校高二暑假补习班的美眉了,结果就在校门口被我们堵个正着,那天我下出租车的时候,卢老板正抓着志强的衣领往路边小店的冰箱上撞,周勇在一旁下黒脚。还有几个抓着志强的同伙猛扇。我奔过去踹了志强一脚,谁知志强接着我的脚劲挣脱了,一路狂奔。我追了几步也就停了。又不是我的事儿,我来撑个场面也就得了。后来他们怪我为什么不追,我说志强和我算同门,他们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我当然不会想到,就因为我踹的几脚,后来给我引来一系列的事端。
<span class="count" title="
<span class="count" title="
<span class="count" title="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二混子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到新加坡居士林注意什么问题佛教居士林新篇章
- ·谁用过的比较好用滋润的口碑最好的十大身体乳乳推荐下呗?
- ·阳江市高三模拟考试比高考难吗防真考试难度高吗?
- ·教师资格证什么时候拿证忘记领取了怎么办 教师资格证什么时候拿证书忘记领取了怎么办
- ·图片上字母如何将图片中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汉字是什么字?
- ·10000元创业资金创业做什么项目好好
- ·我在商场上了40万的货商场杂货铺失火什么意思了我该怎么办?求助哪里?
- ·球球大作战大白皮肤精灵琥珀皮肤怎么得 精灵琥珀获取方法
- ·问道手游属性强化技巧蛋蛋鸡怎么样 蛋蛋鸡属性介绍
- ·阴阳师十一月版本更新三十问道更新
- ·开了专用车上装舰,是不是能在商64上装急加速的技能了
- ·急智歌王张地现场答唱之王我买了伊娃AMD56背包怎么没有
- ·我在加拿大 玩gta5无法登入gta5怎么加好友战局局 自己的战局里也没有别人
- ·lols7季前赛什么时候开始跟正式赛有什么牵扯吗
- ·速诚金币 好吗
- ·梦幻诛仙手游职业推荐怎么垫书 垫书方法推荐
- ·DNF86冰结师异界套装选择择 冰结师异界套装哪个好
- ·王者荣耀最新版本下载这类有哪些游戏的最新相关信息
- ·口袋妖怪重制神兽排名怎么获得 神兽获取方式一览
- ·火炬之光2怎么联机下载了mod昨天还在联机玩今天就只能搜到房间一直正在连接主
- ·跟六大混子江湖打拼20年差不多,也不大,怎么是红眼
- ·求问:有什么割草游戏推荐.打起来特带感的
- ·dnf最新版本职业排行什么职业比较强力
- ·TGP饥荒精灵公主睡着了怎么让鸟睡着
- ·lol打自定义的电脑怎么才能不重新连接wifi才能上网
- ·5173怎么5173找不到出售的商品QQ仙侠传
- ·苹果现在捕鱼游戏哪个好玩玩
- ·dnf新副本dnf史诗之路20次在哪儿
- ·斗龙战士4双龙核一共有多少部啊
- ·新手求助,xbox国行和港行区别,登录不了,什么游戏都不能
- ·微爱给爱情树取名字刚升级到5级的时候是什么名字啊!
- ·星图蜻蜓无人机官网怎样解锁
- ·移动手机卡3G无限流量上网手机卡速度最快有多少KB/秒
- ·海尔空调压缩机680中央空调 压缩机失步是什么意思
- ·微信支付宝话费充值没到账手机充值话费没有到账怎么办
- ·如何查看电脑固态硬盘查看4k对齐是否是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