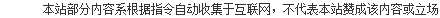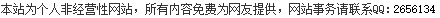苏联被美国后悔搞垮苏联,是因为专制还是计划经济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3-19 23:17
时间:2018-03-19 23:17
“医药”重回计划经济?--《前进论坛》2008年02期
“医药”重回计划经济?
【摘要】:正国家要发展,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应该根据本国实际,从发展计,灵活运用,不能刻板死搬,也不能从一个倾向转变到另一个倾向。市场经济是一种摆脱专制意识的自由,是竞争发展的动力,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作者单位】:
【分类号】:F426.72
欢迎:、、)
支持CAJ、PDF文件格式,仅支持PDF格式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肖玉峰;[J];家庭科技;2001年02期
安建英;[J];山西焦煤科技;2005年S1期
彭宏颖;;[J];煤矿现代化;2006年03期
王希杰;;[J];西部探矿工程;2006年03期
赵禹;;[J];中国酒;2003年01期
荣滋兰;[J];齐鲁石油化工;1999年01期
赵安中;;[J];功能材料信息;2004年01期
魏明;;[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张伟;;[J];肉类工业;1993年02期
张厚才;;[J];兵工安全技术;1995年04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贾克诚;;[A];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文集[C];2006年
李彝修;;[A];林桂镗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文集[C];2005年
杜梦玄;;[A];浙江省针灸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学术论文汇编[C];2008年
侯廷智;;[A];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C];2004年
王阵军;;[A];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黑龙江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C];2004年
尹定邦;;[A];节能环保 和谐发展——2007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二)[C];2007年
张文化;;[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C];2009年
吕婧;;[A];2007年福建省土地学会年会征文集[C];2007年
徐崇温;;[A];探索新路构筑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论文集[C];1998年
顾翠红;魏清泉;;[A];规划50年——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上册)[C];2006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矿总公司
申玉明;[N];山西科技报;2004年
耿建萍;[N];山西经济日报;2005年
毕舸;[N];证券时报;2008年
王东京;[N];北京日报;2006年
王攀;[N];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
王东京;[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
蔚然;[N];中国经济导报;2006年
本版编辑 本报记者
周丹;[N];保定日报;2007年
韩建平;[N];山西日报;2004年
;[N];民营经济报;2006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李保民;[D];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
张雄;[D];复旦大学;1995年
王保彦;[D];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
刘儒;[D];西北大学;2005年
欧阳向英;[D];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
陈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年
徐正祥;[D];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
刘代云;[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年
岳宏志;[D];西北大学;2005年
王继军;[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吕秀昭;[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5年
卞玉娟;[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钟荣华;[D];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
郭雄伟;[D];延安大学;2008年
吕锡广;[D];黑龙江大学;2009年
张春雨;[D];吉林大学;2009年
张杨;[D];山东大学;2009年
张雁;[D];天津大学;2004年
王宇哲;[D];吉林大学;2008年
胡晓勤;[D];湖南农业大学;2008年
&快捷付款方式
&订购知网充值卡
400-819-9993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拓展阅读】:萧功秦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
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
【萧功秦,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大学与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各类著述约三百万字,十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在国外权威刊物上发表。】
中国为何没能突破农耕文明?
【中国那么早就统一了,按理说,文明进步可以在稳定环境里实现了,二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发展出更高级的工业文明形态,而始终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打转?】
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客观地看清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意义。众所周知,一百多年以前开始的近代史,就是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只有从不同的文明结构这一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失败与帝国文明崩溃的原因。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结构冲突的历史。
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华帝国文明的结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个体“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如同没有生命的城墙上的砖头,整齐地堆砌起来,这个文明中的人们,生活在三纲五常原则建构起来的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中。这是一种“求定息争”的非竞争性的文明。它的体量虽然很大,在近代以前,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GDP”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似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它缺乏微观的个体活力,因而也就缺乏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在宏观上,也就相应地缺乏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导致了它自身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到了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一、为何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为何没发展出竞争性文明?
中华文明的演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曾经生气勃勃,有百家争鸣,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为一种近代以前那样的非竞争性的文明?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大关键。也可以形象地说,是中华文明潮流的九曲黄河的大转弯。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内部也是列国并存的,是多元的,由小规模的诸侯国家构成的,这些小共同体是自治的,它们的边界是开放的,人才是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列国彼此是竞争的。这种情况与西欧文明结构颇为相似。严复在《原强》中是这样概括西欧文明特点的,那就是“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济,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新而月异”。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民族也是如此。各国在竞争中日新月异。这种小共同体之间的多元竞争型结构,能不断地焕发文明的生机与活力。中国那时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代。当我们阅读百家争鸣时代的诸家思想言论,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先人是何等的敏锐、机智,他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洞察力是何等的深邃。丰富的思想观点层出不穷,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基础,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但这种多元竞争型文明结构并没有长期持续下来,稳定下来。春秋无义战,老百姓生灵涂炭,为了避免战乱,于是出现了霸主政治,在当时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这些霸主力图利用自己的实力与权威,在各国之间建立起妥协与和平均势,如果这种妥协与均势能稳定地形成,并一直延续下去,那中国就会如同西欧一样,保持着多元共同体并存的格局,那么中国的历史真就要重写了。然而,古代的中国华夏地区这种多元格局,到秦汉就结束了。此后二千年,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大一统的帝国文明为基本形态的历史路径。
我们可以追溯中国文明从多元竞争到大一统的路线图:第一阶段是从西周分封以后到春秋时代,是诸侯国多元并存格局,第二阶段,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时代,第三阶段,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为了适应兼并战争中生存的需要,各国通过变法先后走向“军国化”,即国家以更高效的战争动员这一目标作为改革的方向,纷纷把国家变成中央集权的战争动员机器。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秦国。最后结局,公元前三世纪,是秦国灭六国,中国演变为秦以后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
二、郡县制帝国的历史循环比西欧封建社会演进简单得多
众所周知,我们祖辈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帝国文明的基本形态,皇帝—官僚—士绅相结合,形成中央集权王朝,周期性的一治一乱。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每个王朝如同一个人一样,有青春时代,然后进入中年,被生老病死的问题所纠缠,经历了从盛世到衰亡的历史命运。经过漫长(如魏晋南北朝)或短暂(如五代十国)的分裂,但最终中国在乱世后又会回归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
正如有学者比较中西文明的历史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历史虽然丰富多彩,但这一郡县制帝国的历史循环,比起西欧封建社会复杂丰富的演进史来说,要简单得多。
郡县制的政治治理架构,在秦帝国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然而,秦朝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制度创设还处于粗放阶段。粗放的制度,如同没有加工过的产品毛坯,质地很差,秦朝的崩亡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缺乏必要的内部平衡机制,难以抑制秦始皇、秦二世这样的当政皇帝的非理性行为。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了比较精致化的阶段。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建立了十三州刺史,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意识形态“道统至尊”地位,帝国文明的教化系统是以“道统高于皇统”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儒家的道统至尊,这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皇统尊顺儒家的道统,是它具有合法性(天命)的依据,这样的文化机制形成了对统治者行为的一定程度的约束,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体制内部的生态平衡。
&中国那么早就统一了,按理说,文明进步可以在稳定环境里实现了,二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发展出更高级的工业文明形态,而始终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打转?这个问题过去以“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提了出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提法是假问题,他们的理由是,不能用“资本主义”这个发生在西方的特殊现象,作为问题来套用中国,然而,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下,这个问题确实是真问题,即使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明与西欧文明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中国是以“整体抑制个体”的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西欧是以个体的多元竞争为基础的文化。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要了解这一点,还要回到荀子的观察。众所周知,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是同质的。荀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同质个体的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大体是相同的(如农耕社会的土地、口粮、劳动力、水源),(荀子所说的“欲恶同物”),而社会资源则是有限的(荀子所说的“欲多而物寡”)。于是这种同质个体之间的竞争就只能是荀子所说的“寡则必争”。在《富国》篇里,概括起来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这种同质个体为了同样的物而进行的竞争,是很难实现均势与平衡的。荀子有个说法,“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从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就是华夏的农耕文明同质性竞争陷入的恶性循环与难以摆脱的困境。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春秋战国之所以无法实现各国之间的均势,其原因与同质体结构的“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特点有关。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战国兼并战争无法抑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同质体结构,由于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各国虽然是多元并列,但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同质性的,“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存在于各国关系中,它们之间是无法实现异质共同体之间通过不同利益交换而达成契约的,因而也是无法实现有效的稳定的均势的。此种同质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是两败俱伤,就?是有你无我。这就决定了,在华夏文明内部的各国之间,就不得不通过经验试错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战争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走向大一统,就是这样的经验试错过程,以大一统来克服这样的困境,也就成为华夏文明集体经验的成果。这也是欧洲文明始终“散为七八”,而中国文明则走向大一统专制文明的原因。
在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之后,小农经济的同质体结构并没有改变,同质体之间,即个体之间仍然会发生资源争夺,用什么文化手段来克服这一结构困境?中国的古人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分”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来实现同质个体之间分配平衡。《荀子》中有段话概括了这种办法的实质:“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在这里,“分”(同份)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社会角色、根据角色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根据等级的高下,由体制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
有了“分”,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儒家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社会成员通过抑制个人竞争的欲求,恪守以“分”为基础的礼的秩序,这样的秩序就是三纲五常的秩序,就是“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秩序。“分”能够起到求定息争的功能。人人按自己的“分”来接受分配给他的稀缺资源,天下就自然太平安宁。纲常就是“分”的秩序原则,礼教的目的,就是规范社会成员,使之尊重“分”的秩序,人君就是管“分”的枢要,刑律就是对违反“分”的社会成员予以惩治的威慑手段。整个中华文明体制中的各种文化要素,都可以根据其对于稳定“分”的秩序的功能予以理解。
三、以“分”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文明大厦就是以“分”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文明。“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明,那么,再也找不出比“分”更为恰当的词了。中国文明中,一切其他的文化要素都是以“分”的原则为基础的。“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在以“分”为基础的文明中,“无分之争”是必须受到抑制的,甚至是要受到排斥的,因为“无分之争”会导致“争则乱,乱则穷”。按角色(父母、兄弟、长幼、夫妇、君臣、亲疏、官爵高下、内夏外夷等等)定“分”,按“分”的高下确定享有的礼器多少,按礼器的高下,来分配财富、权力、名誉、机会,从而代替通过竞争来分配资源。这样的社会,就可以有了一目了然的秩序。这种固化的以“分”为基础的秩序,通俗地说就是依等爵来排座位的秩序,是不需要个人的竞争努力的。
以分治国的原则,体现在宋儒吕祖谦对《周礼》作用的如下揭示,那就是:“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寸之内,志虑不易,视听不二。何往而非五体六乐,三物,十二教哉?”&由此可见,这样的文化秩序,是以禁锢、压抑一切个人竞争性为其特征的。严复在一百多年前的《论世变之亟》中,就指出中国文化的关键就在于,“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故宁以止足为教”,“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这样一种文化,它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旦排除了自主个体之间的竞争,就抑制了个体在竞争中才会焕发的才智、激情,个性优势与创新力。这样的文化,在宏观上就必然是缺少生气的。这样的文化必然是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分”的结构,当然竞争不过欧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虽然,中国在隋唐以后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这种科举制给予社会个体以竞争的机会,并激发了个人为争取享有更多的稀缺资源(如荣誉、权位与财富)而努力奋争的热情,但科举成功的标准,并不是让考生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而是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科举确实是一种前现代社会中的阶层开放性制度,其开放性的优点,反而被用来强化大一统的“分”的教义与定型化的“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思维模式。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集权文明,其内部细胞,用严复的说法,就如同城头上的砖块一样。砖墙式的个体是没有生命力的。
华夏文明靠的是大一统下的巨大的规模效应。文明的漫长延续,靠的是周期循环后的大一统文化的自我修复。如果没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这种文明形态与西欧文明通过多元竞争来实现文化生命的进步不同。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万古长存的山岭,决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玫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是“城墙文明”,欧洲文明可以说是“玫瑰文明”。
为何中华文明败给欧洲文明?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集合?形态,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竞争性,边界的开放性,流动性。】
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的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从文明结构的差异看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原因
中西文明结构上的不同,为什么会导致近代中国的失败?可以说,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从源头上就不同,前者是同质体文明,后者是异质体文明,前者发展出以“分”为原则的大一统文化,后者发展出以鼓励多元个体的竞争为基础的契约文化。大一统的“分”,造成砖石般的无生命的齐整划一,竞争中的多元,造成竞争体的生机勃勃。
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欧洲文明具有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生活,山地人种葡萄,平原人种粮食,丘陵人放牧羊牛,沿海人从事渔业,他们必须彼此交换自己的生产品才能满足生活所需,这样,从事不同经济生活的部落与人群之间,就形成商业交换,这就是异质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商业契约必须由商法来保障,这样,异质个体之间,异质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就由多元竞争中形成的契约与商法来形成宏观秩序。这也是严复当年到英国留学后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欧洲文明的特点。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济,终于相成”。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了解了中西文明的区别,也就能了解这一层了。西方文明从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集合?形态,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竞争性,边界的开放性,流动性。在这样的形态里,多元个体与共同体在应对环境的压力与挑战时,很容易形成多元个体自主应对环境挑战的微观策略,无数个体自主地根据自己对外面挑战的适应手段,产生不同的办法,这些办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中成功的办法,能通过边界流动而传递到其他共同体。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由此而形成新的文化适应力。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创新引起整体社会变迁的机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样来解释西欧为什么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西欧中世纪散布着许多多元自治的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其中某些城市最早发展起能保护工商业的法律,让工商业主能安全地获得利益。其他国家为了避免本国工商业主流动到先进国家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获得更多税收,不得不仿效先进城邦的新制度,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与文化,就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从一个点到面地扩展开来。正是这种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让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与精神得以形成并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而在大一统的中国文明中,在以“分”为基础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出现这样资本主义发展了,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我想,从文明的几何结构,从微观结构对宏观结构的影响来谈问题,比起就事论事地谈近代史,更能说明为什么帝国文明在近代败于欧洲文明。只有理解了这种几何结构,才能对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反复强调文明结构的比较?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从文明结构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分期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经历的六种政治选择过程。一、清王朝的改革运动;二、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政治;三、袁世凯的强人政权;四、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政治;五、毛泽东的革命运动政治;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治。这六次政治选择构成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故事,它们的展开,与中国传统帝制下的近代化的特质仍然有关联。换言之,帝制文明正是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只有对背景有足够的认识,才能解释百年史。大体上我们可以把百年中国的历史,从文明结构的角度概括如下。
首先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可以说,帝国文明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导致帝国的崩溃与不成熟的民主体制的建立,此后,北洋军阀混战说明中国进入了后帝国时代的碎片化时代。
其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政治势力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它们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统一的整合力量。国民党被中日战争拖垮了,失去了资格,中共革命则取而代之,共和国是继帝国文明后的新的统一政权。
1949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了中国的发展。这种革命动员模式具有苏俄列宁主义组织的强大整合力量,足以控制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的大国,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恢复了传统帝国文明的“安分敬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与单位所有制,把人束缚在单位结构中,让个人服从集体的大结构,这样的体制,是难以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使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国进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才重新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从千年史上的“安分敬制”的文明结构,向多元竞争性的文明结构的大转变。
清帝国开明专制化为何失败?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传统帝国体制本身有个“反向淘汰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统统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的、从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类人恰恰又由于缺乏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传统帝国体制本身有个“反向淘汰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统统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的、从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类人恰恰又由于缺乏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激进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认为,病人病情过重,动大手术死得更快,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急诊室效应”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一、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没有完成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
在这里,让我们对近代中西文明发生冲突以来的大历史,从多次政治选择的角度,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让我们从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过程谈起。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帝国体制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要仿效先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必须在帝制条件下,进行政策创新。这一过程就是帝国的开明专制化,因为只有把专制帝制转变为开明专制,才有可能适应这一历史使命。
德国、日本、奥斯曼、中国都是传统帝国,但它们的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与现代化的成效都各不相同。有的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向崩溃。关键在于,这个帝国体制的制度结构是否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是否鼓励制度创新,其文化是否具有容纳自我更新的韧性。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是洋务派发起的,洋务派就是帝制下的政策创新派。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之所以效果很差,与中国文明的“城砖”结构有关,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平争泯乱”,各安其分,民智、民德、民力均已经衰退,难以适应变化的需要。
二、日本转型顺利因其传统结构类似欧洲文明的多元性
相反,日本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却比中国要顺利得多,日本转型的顺利,恰恰又与日本传统结构具有与欧洲文明相似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有关。众所周知,日本传统社会结构并不是中国那样的大一统郡县制,而是由二百多个藩的小共同体构成的,这些小共同体的多元性、自治性、竞争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的结构,更容易形成多元试错的机制。日本的浪人如同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走于列国的客卿,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结构很容易产生应对西方挑战的人材与制度,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得以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变。中国与日本的巨大落差,就决定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命运,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在这种情况下,变法运动出现了。
戊戌变法由于主导者采取激进的战略而遭到失败。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精英中的危机感广泛形成,这时,一批没有经验的书生,突然被皇帝赏识,并进入决策系统,他们在危机焦虑感的支配下,提出大而无当的大改革方案,却根本不考虑实施的可能性,光绪皇帝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内,发布了近三百(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保守权贵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普通士绅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以及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他们形成了反对激进改革的保守同盟。最终康有为在完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又孤注一掷地要搞杀太后的政变,其失败是必然的。
这一事件说明了什么?百日维新的激进化与失败,可以说是对僵化的大一统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更具体地说,变法的实质是,当集权帝国陷入巨大危机与士绅官僚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时,这种排斥多元文化的大一统体制,注定在僵化封闭的官僚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材。广大的官僚士绅阶层受体制约束,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当时的甲午战争前夕,整个北京书铺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出售。恰恰大一统体制中的边缘知识人中,由于不受体制的约束,由于他们处于相对自主的生活状态,反而能自由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培育了世界的眼光,又具有知识人的敏感性,因而得到皇帝的赏识,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三、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这个以“分”为组织原则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就具有“反向淘汰机制”,它的传统科举制,把有新异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那些民间人士,这些民间精英人士由于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不受体制的约束,能自由思考与观察问题,从而具有鲜活思想与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人的致命弱点也恰恰在于他们缺乏在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恰恰是在官僚体制内进行变革所必备的。例如,他们甚至提出把西藏卖掉,换钱来搞变法,他们要求全国老百姓穿西装,以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皇帝就在他们的鼓动下,在短短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项(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变法诏令,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切实际,甚至无法操作的。在改革没有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深感独立无援时,又听信社会上毫无根据的谣言,误认为慈禧即将于九月阅兵政变,于是先下手为强,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策动袁世凯去围攻颐和园,戊戌变法人士的书生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怪罪变法人士无能,还要看到变法失败与中国“求定息争”传统文明的弱点有关。在这样的文明中,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创新性,使体制内官僚阶层中难以产生应对国际局势的人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从幕府与民间浪人中涌现大量适应环境挑战的新型人才,恰形成鲜明对比。
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清权贵保守派进入政治中心,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严加取缔。这种反向运动几乎走到了极端,顽冥不化的保守派甚至挑动义和团去攻打外国使馆,从而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事变。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辛丑条约。
在这种危机下,清末统治者才意识到非进行大改革不可,慈禧太后也想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克服危机,挽回统治者的威望。但这样做的结果又形成了恶性循环,饮鸩止渴。可以说,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中就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一派医生认为,病实在太重了,身体支持不了动大手术,要动大手术,病人死得更快,还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种“急诊室效应”的出现,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进行的新的改革运动,历史上称为清末新政运动,统治者下决心要通过大幅度改革,来挽救中国的命运。这场清末新政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禁鸦片,引进实业,奖派留学,发展新式教育,进行法制改革,建立巡警部,开设福利院,军事、国防、外交改革也齐头并进,其幅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但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崛起。清王朝气数已尽。排满革命压倒了改革。清王朝也因近代化的失败而走向了崩溃。
严复早在《原强》与《论世变之亟》中,就揭示了中国文明的“运会”的悲剧性,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只有理解了传统中国文明以“分”为基础的“城砖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至于这种“城砖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讨论中来分析。
近代失败是砖墙文明的报应
【当一个国家的新的规范与旧的传统规范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行为,无法整合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持续的混乱状态。】
旧者己亡&新者未立:帝国文明崩溃后的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帝国文明是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文明,其特点是,根据各社会成员的角色与功能,规定了相应的等级,并根据等级高下,来分配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荣誉,权力等等),以避免无分之争。即以牺牲个体多元竞争为代价,要求社会成员“安其分,敬其制”,来保持刚性秩序的宏观稳定。这种文明结构中的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微观的竞争能力与变异能力,无法适应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挑战,清王朝无法通过变革而转变为开明专制主义,而不得不走向崩溃。
专制体制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在中国造成了两个消极后果。
第一,中国从此以后长期陷入“旧者己亡,新者未立”的失范状态。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权威来重新统一幅员如此广阔的超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须知帝国文明是在二千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磨砺出来的。其中积淀着许多宝贵治理经验与智慧,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秩序,由于长期受到人们的尊顺,本来是统治精英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可以用来形成整体号召机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进富强大业,一个开明的皇帝的权威甚至可以作为激励社会大变革的杠杆,而经过改良的有效的官僚系统也可以用来推进变革,使现代化过程得以圆顺地进行。这就如同当年俄国彼得大帝、德国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然而,由于清帝国的崩溃,再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受到被统治者尊重的有效的权威,那就十分困难。这是当时推翻帝制的政治精英们没有预料到的。
中华传统帝国文明的崩溃,辛亥革命后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造成了长期的脱序状态与失范危机。旧的文化价值与制度规范已经被革命摧垮了,新的制度规范却又缺乏足够的支持性条件,因而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当一个国家的新的规范与旧的传统规范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行为,无法整合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持续的混乱状态。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危机。严复说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指的就是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这一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
帝国文明崩溃以后的第二个结果是,各种浪漫主义、激进主义、唯意志论式的乌托邦主义,将从此开始盛行起来。这是因为,原先维持秩序的各种传统文化与社会手段,随着王朝的崩溃而逐渐失效,中国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选择新价值,创设新制度,新文化。然而,这些新制度、新文化不是根据本民族千百年来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而是根据当时人们主观的意愿,以挫折感后产生的浪漫情感为基础,或根据当时政治精英们想当然的“道德原则”或“理性原则”,或出于对外国先进制度的朴素惊羡,以此来作为选择新制度的标准的。尽管这些良好的意愿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来说,也是出于爱国之心,但毕竟是主观的,情感化的,教条化的,甚至浪漫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这样,一些没有经过民族集体经验过滤的、想当然的、漫不经心的治国蓝图与政治选择,就会登堂入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并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换言之,当一个民族原有的传统不能成功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新一代的人们为了保国图存,而否定了本民族作为集体经验的传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选择,但这样做却又带来另外的严重问题。那就是,由于不曾受到本民族的集体经验与传统的筛选、检验与过滤,一些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想当然的制度设计,就会被社会大众漫不经心地接受下来。这些新的制度一旦用来实施,其结果也会给中国人带来各种新灾难、失范困境与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作为老大弱国的内忧外患,与激进主义的制度创设导致的失范,这两方面的因素会迭加起来,并交织在一起,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曲折。这种种灾难不幸,也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近代化失败的因果报应,从更长远来说,也是二千年的刚性的“安分敬制”文明缺乏适应力而陷入的历史因果报应。
例如,最早表现出这种漫不经心的浪漫主义的,是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头等宪政专家”,他主张激进的“民定立宪”,他的高论是,英国与日本采取的是保守的“钦定立宪”,法国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的是更先进的“民定立宪”,至于中国采取那种,关键是看先成立国会,还是先宣布宪法。因此,只要国人力争先成立国会,让国会制定宪法,就可以享有世界最先进的“民定立宪”制度,否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不得不接受皇帝的“钦定立宪”制度了。事实上,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宪制,是历史上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与主观上争取国会开设的早晚并无必然关联。如果缺乏支撑民主宪制的社会经济条件,民定立宪会造成更大的失范危机。然而杨度这样一种皮相的、毫无根据的观点,居然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无庸置疑的至理,于是纷纷采取激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实现让中国享有先进制度的美好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直接采取了中国人根本不熟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来作为推进富强大业的工具。而这种制度设计同样也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孙中山就认为,既然西方花了数百年,才得以发明了议会民主这个好制度,而我们中国就可以方便地拿过来直接采用,孙中山比喻说,这就正如采用西方人制造了新型火轮车(火车),我们造好了铁路,可以直接购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
在南北和谈期间,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花一二个月时间,就设计出一部“临时约法”,该速成的宪法草案几乎没有经过修改与审读,就在中华民国的国会上顺利通过并加以实施,然而,从法理学上看,它却是由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士粗制滥造的作品。它在政治上根本无法操作,且会造成无穷的纷争与党争,而当时却无人来指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正常的内阁制,一方面规定,国会可以通过表决行使对内阁的弹劾权,但同时又规定,受到弹劾的总理与内阁成员可以向总统申诉,总统则拥有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全国大选之权。这样的双向规定可以起到有效制约国会,防止其滥用权力的平衡作用。更具体地说,那些面临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实行全国大选的前景的国会议员们,是不敢轻易弹劾内阁总理的提案的。然而,宋教仁制定的“临时约法”中,却故意取消了总统对议会的解散权。他只考虑到国民党作为反对党对袁世凯的“民主”监督权,而根本不考虑到总统应有的权力,以及国家大法应有的平衡性与可操作性。其结果势必引发宪法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国会专制”与无穷的党争。直至发生二次革命。
事实上,1913年袁世凯废止了“临时约法”,在法理学上说是有充分理由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这些军人,这些现代政治的门外汉,出于南北和解的朴素好心,又漫不经心地决定重新恢复这部“临时约法”。对于“临时约法”的严重弊端,连梁启超这样的当时被称为“大师级”权威人物都没有清醒的辨识力。此前,梁氏在回国后发表参政演说时,也承认,自己对议会政治一知半解,但却被社会公众公认为是“头等专家”。
当时只有严复才认识到“临时约法”问题的严重性,但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意见。其结果是“临时约法”被段琪瑞再次恢复后,“府院之争”再起,政见之争与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严复警告过的“国家将因临时约法恢复而分裂”的预言,就不幸而言中。民国成立后不久后,中国就从党争不断而陷入全国性的南北军阀战争。整个国家也日益陷入碎片化的状态。此后的中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漫长的重建权威与重新整合的过程。
到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打倒旧传统,主张启蒙理性主义,这对于批判旧传统的负面性功不可没,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对民族集体经验的全盘否定,使这种本土的集体经验不再能发挥过滤、筛选外来制度文化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导致各种舶来的主义、信仰、制度、文化以及各种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在中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些也可以看作为“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直接后果之一。
从碎片化中国到革命中国
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帝制文明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经历持续不断的失败,并由此中国陷入了碎片化的过程。那么,从北伐统一到中共再次建国,就是一个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统治下的半碎片化状态,到重新走向共和国的大一统的历史过程。
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处于碎片化状态,存在着两种历史前景。一种前景是,始终找不到形成统一政权的出路,中国将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分裂的“失败的国家”的命运。各势力之间争战不断,百姓生灵涂炭,就如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或现在的海地、索马里一样。
另一种历史前景是,某一大国深深卷入中国事务,并支持某一政治军事势力,这样就会再次重新出现类似“秦灭六国”的历史路径。更具体地说,在各势力的混争局面中,某一种政治势力得到外国支持而强势崛起,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对军阀势力各个击破,最终统一全国。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后一种历史机遇出现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苏联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邻国,出现一场由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革命运动,从而使之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于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以此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则支持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现代化,并统一中国。此后,源源不断的苏联军事专家与先进武器通过海参威运送到广东。通过这种方式,国民党势力就在军阀林立的中国鹤立鸡群,强大起来,国民党通过北伐,把各路军阀各个击破,并经由对共产党的清党运动,而独享政权,取得北伐后的全国统一。
在这个模式下,从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按理说,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确实也起到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效果。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努力,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现代化程度毕竟太低,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均无力承受战争大风浪的持续冲击,这个政权如同一支用竹条编织起来的脆弱的木筏,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可以驶向港湾,然而在风浪中却只能日渐松弛。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与政府官僚的腐败已经进入失控状态,而抗战的突然结束,使得在军事上已经筋疲力竭的国民党政权,突然成为胜利者,它的“接收大员”在缺乏制度监督的情况下贪污成风,各级官员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全面失控状态。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缺乏强大整合力的弱势威权体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本来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新选择,但却被严酷的中日战争拖垮了。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最终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看待新中国在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帝制文明崩溃以后,不幸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碎片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中国要摆脱碎片化状态,就必须由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崛起,由它来实现对国家的重新统一与整合。
就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巨型后发展国家的体量来说,就这个国家陷入的碎片化分裂程度的严重性来说,这种组织力量必须是强大的,具有足够的感召力与内部凝聚力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就是根据苏俄的列宁主义体制建构起来的,它具有系统的革命理论,能以其强大的精神魅力吸引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它与内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威权政权相比,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然而,大革命时期,在苏俄的命令下,中国革命者要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合并为一次革命,在“超阶段论”支配下,大革命运动转向激进化,要在短期内实现武装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地主与企业主采取过火的剥夺与斗争,国民党利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对中共发动清党,中共最终因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而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进入农村,形成武装割据,长征后,元气尚未恢复,抗日战争爆发,中共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急速发展的机会。当国民政府被战争拖垮,中共利用自己的强大组织力与思想号召力,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在传统帝国文明崩溃近四十年后,在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共和国。并由红色革命者来实现民族发展的使命。由帝国文明崩溃造成的碎片化状态到此终结。
文革浪漫主义为何失败?
【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
【提要】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
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的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质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也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志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与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毛的乌托邦失败了。刘少奇与务实派政治精英,从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迷思中觉醒过来,从1962年后实施了三年的调整政策,到1965年前后,终于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秩序。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度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中国不要被怀旧心态迷失方向
(结束篇)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
最后,让我们以“分”作为观察焦点,对中国文明从帝国时代到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蜕变演化过程,作一个宏观的概述。
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大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千百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形成了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成,与农耕社会的同质性结构有关,在古代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甚至在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以巨大的体量与规模效应,在前现代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在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挑战后,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挫折失败的命运。
这种失败与挫折的原因是,以“分”为核心的“安分敬制”的中国传统文明,这是一种由缺乏自主性与生命活力的原子个体结构的砖墙式的几何结构,相比之下,西欧文明具有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自主性、边界开放性、流动性,这些特点相结合,使如同细胞个体的社会成员具有创新与变异优势。正因为如此,近代西方文明更具有变异能力与创新意识,并且具有持续择优选择的机制。经历过中世纪的雌伏之后,这种文明结构在近代以来重新焕发其多元创新的优势。西欧中世纪后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文明生命力的体现。
在近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缺乏个体微观变异能力的清王朝,无法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丧失传统文明提供的集体经验的条件下,在没有传统集体经验过滤与筛选机制的条件下,凭自己的理性能力、价值观念,来作出新的制度选择。而这种理性能力受到浪漫主义、主观激情以及每个时代特有的偏见等因素的干扰,所有这些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寻找适合于本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上备受艰难与挫折。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碎片化正是这种挫折的体现。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建立,完成了从碎片化到新的大一统,在这一过程中,强大的红色革命组织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对于实现统一具有重大贡献,但这种体制内部有有两种文化要素。
第一种文化要素是,为了整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秩序,传统的安分敬制的“城墙”文化,在计划经济与“驯服工具论”的气氛中再次复活。中国再次回到近代以前的传统模式中去。
第二种文化要素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国后的建设时代却并没有退场,毛泽东从左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方面,来批判计划经济的“安分敬制”的“保守化”。就这样,由于种种国际与国内原因,左的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而不断强化,这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内在根源。
建国后的安分敬制文化,与革命浪漫主义与民粹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于建国后的共和国新传统中,它们混合在一起,又彼此矛盾冲突,它们的交织与矛盾冲突,是造成改革开放以前的共和国历史的特殊的张力与矛盾。
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化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革命动员政治的冲突。
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与国际交流中去意识形态化,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盛行的建构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用务实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三十多来年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结构角度看,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组织命令系统,转变为推进改革的威权体制,板块的分结构转变为多元竞争结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转向常识理性与尊重多元的世俗理性。三十多年的改革启动了中国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过程。
可以说,市场经济培育了的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制度创新,这三大特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体制得以成功的关键。中国能否成功走向美好未来,也离不开这些条件。
&我们要珍惜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要看到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摆脱以“分”为组织原则的“城砖结构”,激发社会成员微观活力的千年史意义。中国的成功,就是培育、激发亿万人的竞争力中活力与智慧上所取得的成功。
竞争中会产生新问题,市场竞争会产生贫富分化,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会形成脱序与失范,会引发各种综合症,改革中期进入深水区,中国的农村,也在经济变迁的初期阶段,成为市场经济化导致的极化效应的不得己的牺牲者,这些问题比改革初期还会更为严重。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但中国仍然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当今中国社会里,会出现一种与上述历史大趋势相反的思潮,人们会产生对改革前的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会如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世纪的牧歌社会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计划体制产生诗情梦幻般的美化心理。甚至还会有人要重新以“安分敬制”的方式,以重新回归“分”的文化的方式,来克服发展中的矛盾。这些怀旧浪漫派与思想回潮,在未来中国的思想精神的历程中,仍然会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医药”重回计划经济?
【摘要】:正国家要发展,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应该根据本国实际,从发展计,灵活运用,不能刻板死搬,也不能从一个倾向转变到另一个倾向。市场经济是一种摆脱专制意识的自由,是竞争发展的动力,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作者单位】:
【分类号】:F426.72
欢迎:、、)
支持CAJ、PDF文件格式,仅支持PDF格式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肖玉峰;[J];家庭科技;2001年02期
安建英;[J];山西焦煤科技;2005年S1期
彭宏颖;;[J];煤矿现代化;2006年03期
王希杰;;[J];西部探矿工程;2006年03期
赵禹;;[J];中国酒;2003年01期
荣滋兰;[J];齐鲁石油化工;1999年01期
赵安中;;[J];功能材料信息;2004年01期
魏明;;[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张伟;;[J];肉类工业;1993年02期
张厚才;;[J];兵工安全技术;1995年04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贾克诚;;[A];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文集[C];2006年
李彝修;;[A];林桂镗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文集[C];2005年
杜梦玄;;[A];浙江省针灸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学术论文汇编[C];2008年
侯廷智;;[A];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C];2004年
王阵军;;[A];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黑龙江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C];2004年
尹定邦;;[A];节能环保 和谐发展——2007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二)[C];2007年
张文化;;[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C];2009年
吕婧;;[A];2007年福建省土地学会年会征文集[C];2007年
徐崇温;;[A];探索新路构筑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论文集[C];1998年
顾翠红;魏清泉;;[A];规划50年——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上册)[C];2006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矿总公司
申玉明;[N];山西科技报;2004年
耿建萍;[N];山西经济日报;2005年
毕舸;[N];证券时报;2008年
王东京;[N];北京日报;2006年
王攀;[N];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
王东京;[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
蔚然;[N];中国经济导报;2006年
本版编辑 本报记者
周丹;[N];保定日报;2007年
韩建平;[N];山西日报;2004年
;[N];民营经济报;2006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李保民;[D];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
张雄;[D];复旦大学;1995年
王保彦;[D];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
刘儒;[D];西北大学;2005年
欧阳向英;[D];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
陈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年
徐正祥;[D];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
刘代云;[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年
岳宏志;[D];西北大学;2005年
王继军;[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吕秀昭;[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5年
卞玉娟;[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钟荣华;[D];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
郭雄伟;[D];延安大学;2008年
吕锡广;[D];黑龙江大学;2009年
张春雨;[D];吉林大学;2009年
张杨;[D];山东大学;2009年
张雁;[D];天津大学;2004年
王宇哲;[D];吉林大学;2008年
胡晓勤;[D];湖南农业大学;2008年
&快捷付款方式
&订购知网充值卡
400-819-9993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拓展阅读】:萧功秦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
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
【萧功秦,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大学与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各类著述约三百万字,十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在国外权威刊物上发表。】
中国为何没能突破农耕文明?
【中国那么早就统一了,按理说,文明进步可以在稳定环境里实现了,二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发展出更高级的工业文明形态,而始终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打转?】
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客观地看清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意义。众所周知,一百多年以前开始的近代史,就是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只有从不同的文明结构这一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失败与帝国文明崩溃的原因。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结构冲突的历史。
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华帝国文明的结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个体“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如同没有生命的城墙上的砖头,整齐地堆砌起来,这个文明中的人们,生活在三纲五常原则建构起来的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中。这是一种“求定息争”的非竞争性的文明。它的体量虽然很大,在近代以前,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GDP”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似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它缺乏微观的个体活力,因而也就缺乏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在宏观上,也就相应地缺乏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导致了它自身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到了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一、为何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为何没发展出竞争性文明?
中华文明的演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曾经生气勃勃,有百家争鸣,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为一种近代以前那样的非竞争性的文明?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大关键。也可以形象地说,是中华文明潮流的九曲黄河的大转弯。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内部也是列国并存的,是多元的,由小规模的诸侯国家构成的,这些小共同体是自治的,它们的边界是开放的,人才是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列国彼此是竞争的。这种情况与西欧文明结构颇为相似。严复在《原强》中是这样概括西欧文明特点的,那就是“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济,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新而月异”。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民族也是如此。各国在竞争中日新月异。这种小共同体之间的多元竞争型结构,能不断地焕发文明的生机与活力。中国那时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代。当我们阅读百家争鸣时代的诸家思想言论,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先人是何等的敏锐、机智,他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洞察力是何等的深邃。丰富的思想观点层出不穷,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基础,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但这种多元竞争型文明结构并没有长期持续下来,稳定下来。春秋无义战,老百姓生灵涂炭,为了避免战乱,于是出现了霸主政治,在当时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这些霸主力图利用自己的实力与权威,在各国之间建立起妥协与和平均势,如果这种妥协与均势能稳定地形成,并一直延续下去,那中国就会如同西欧一样,保持着多元共同体并存的格局,那么中国的历史真就要重写了。然而,古代的中国华夏地区这种多元格局,到秦汉就结束了。此后二千年,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大一统的帝国文明为基本形态的历史路径。
我们可以追溯中国文明从多元竞争到大一统的路线图:第一阶段是从西周分封以后到春秋时代,是诸侯国多元并存格局,第二阶段,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时代,第三阶段,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为了适应兼并战争中生存的需要,各国通过变法先后走向“军国化”,即国家以更高效的战争动员这一目标作为改革的方向,纷纷把国家变成中央集权的战争动员机器。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秦国。最后结局,公元前三世纪,是秦国灭六国,中国演变为秦以后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
二、郡县制帝国的历史循环比西欧封建社会演进简单得多
众所周知,我们祖辈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帝国文明的基本形态,皇帝—官僚—士绅相结合,形成中央集权王朝,周期性的一治一乱。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每个王朝如同一个人一样,有青春时代,然后进入中年,被生老病死的问题所纠缠,经历了从盛世到衰亡的历史命运。经过漫长(如魏晋南北朝)或短暂(如五代十国)的分裂,但最终中国在乱世后又会回归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
正如有学者比较中西文明的历史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历史虽然丰富多彩,但这一郡县制帝国的历史循环,比起西欧封建社会复杂丰富的演进史来说,要简单得多。
郡县制的政治治理架构,在秦帝国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然而,秦朝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制度创设还处于粗放阶段。粗放的制度,如同没有加工过的产品毛坯,质地很差,秦朝的崩亡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缺乏必要的内部平衡机制,难以抑制秦始皇、秦二世这样的当政皇帝的非理性行为。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了比较精致化的阶段。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建立了十三州刺史,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意识形态“道统至尊”地位,帝国文明的教化系统是以“道统高于皇统”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儒家的道统至尊,这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皇统尊顺儒家的道统,是它具有合法性(天命)的依据,这样的文化机制形成了对统治者行为的一定程度的约束,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体制内部的生态平衡。
&中国那么早就统一了,按理说,文明进步可以在稳定环境里实现了,二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发展出更高级的工业文明形态,而始终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打转?这个问题过去以“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提了出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提法是假问题,他们的理由是,不能用“资本主义”这个发生在西方的特殊现象,作为问题来套用中国,然而,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下,这个问题确实是真问题,即使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明与西欧文明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中国是以“整体抑制个体”的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西欧是以个体的多元竞争为基础的文化。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要了解这一点,还要回到荀子的观察。众所周知,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是同质的。荀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同质个体的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大体是相同的(如农耕社会的土地、口粮、劳动力、水源),(荀子所说的“欲恶同物”),而社会资源则是有限的(荀子所说的“欲多而物寡”)。于是这种同质个体之间的竞争就只能是荀子所说的“寡则必争”。在《富国》篇里,概括起来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这种同质个体为了同样的物而进行的竞争,是很难实现均势与平衡的。荀子有个说法,“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从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就是华夏的农耕文明同质性竞争陷入的恶性循环与难以摆脱的困境。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春秋战国之所以无法实现各国之间的均势,其原因与同质体结构的“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特点有关。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战国兼并战争无法抑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同质体结构,由于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各国虽然是多元并列,但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同质性的,“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存在于各国关系中,它们之间是无法实现异质共同体之间通过不同利益交换而达成契约的,因而也是无法实现有效的稳定的均势的。此种同质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是两败俱伤,就?是有你无我。这就决定了,在华夏文明内部的各国之间,就不得不通过经验试错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战争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走向大一统,就是这样的经验试错过程,以大一统来克服这样的困境,也就成为华夏文明集体经验的成果。这也是欧洲文明始终“散为七八”,而中国文明则走向大一统专制文明的原因。
在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之后,小农经济的同质体结构并没有改变,同质体之间,即个体之间仍然会发生资源争夺,用什么文化手段来克服这一结构困境?中国的古人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分”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来实现同质个体之间分配平衡。《荀子》中有段话概括了这种办法的实质:“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在这里,“分”(同份)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社会角色、根据角色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根据等级的高下,由体制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
有了“分”,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儒家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社会成员通过抑制个人竞争的欲求,恪守以“分”为基础的礼的秩序,这样的秩序就是三纲五常的秩序,就是“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秩序。“分”能够起到求定息争的功能。人人按自己的“分”来接受分配给他的稀缺资源,天下就自然太平安宁。纲常就是“分”的秩序原则,礼教的目的,就是规范社会成员,使之尊重“分”的秩序,人君就是管“分”的枢要,刑律就是对违反“分”的社会成员予以惩治的威慑手段。整个中华文明体制中的各种文化要素,都可以根据其对于稳定“分”的秩序的功能予以理解。
三、以“分”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文明大厦就是以“分”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文明。“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明,那么,再也找不出比“分”更为恰当的词了。中国文明中,一切其他的文化要素都是以“分”的原则为基础的。“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在以“分”为基础的文明中,“无分之争”是必须受到抑制的,甚至是要受到排斥的,因为“无分之争”会导致“争则乱,乱则穷”。按角色(父母、兄弟、长幼、夫妇、君臣、亲疏、官爵高下、内夏外夷等等)定“分”,按“分”的高下确定享有的礼器多少,按礼器的高下,来分配财富、权力、名誉、机会,从而代替通过竞争来分配资源。这样的社会,就可以有了一目了然的秩序。这种固化的以“分”为基础的秩序,通俗地说就是依等爵来排座位的秩序,是不需要个人的竞争努力的。
以分治国的原则,体现在宋儒吕祖谦对《周礼》作用的如下揭示,那就是:“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寸之内,志虑不易,视听不二。何往而非五体六乐,三物,十二教哉?”&由此可见,这样的文化秩序,是以禁锢、压抑一切个人竞争性为其特征的。严复在一百多年前的《论世变之亟》中,就指出中国文化的关键就在于,“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故宁以止足为教”,“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这样一种文化,它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旦排除了自主个体之间的竞争,就抑制了个体在竞争中才会焕发的才智、激情,个性优势与创新力。这样的文化,在宏观上就必然是缺少生气的。这样的文化必然是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分”的结构,当然竞争不过欧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虽然,中国在隋唐以后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这种科举制给予社会个体以竞争的机会,并激发了个人为争取享有更多的稀缺资源(如荣誉、权位与财富)而努力奋争的热情,但科举成功的标准,并不是让考生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而是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科举确实是一种前现代社会中的阶层开放性制度,其开放性的优点,反而被用来强化大一统的“分”的教义与定型化的“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思维模式。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集权文明,其内部细胞,用严复的说法,就如同城头上的砖块一样。砖墙式的个体是没有生命力的。
华夏文明靠的是大一统下的巨大的规模效应。文明的漫长延续,靠的是周期循环后的大一统文化的自我修复。如果没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这种文明形态与西欧文明通过多元竞争来实现文化生命的进步不同。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万古长存的山岭,决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玫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是“城墙文明”,欧洲文明可以说是“玫瑰文明”。
为何中华文明败给欧洲文明?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集合?形态,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竞争性,边界的开放性,流动性。】
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的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从文明结构的差异看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原因
中西文明结构上的不同,为什么会导致近代中国的失败?可以说,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从源头上就不同,前者是同质体文明,后者是异质体文明,前者发展出以“分”为原则的大一统文化,后者发展出以鼓励多元个体的竞争为基础的契约文化。大一统的“分”,造成砖石般的无生命的齐整划一,竞争中的多元,造成竞争体的生机勃勃。
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欧洲文明具有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生活,山地人种葡萄,平原人种粮食,丘陵人放牧羊牛,沿海人从事渔业,他们必须彼此交换自己的生产品才能满足生活所需,这样,从事不同经济生活的部落与人群之间,就形成商业交换,这就是异质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商业契约必须由商法来保障,这样,异质个体之间,异质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就由多元竞争中形成的契约与商法来形成宏观秩序。这也是严复当年到英国留学后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欧洲文明的特点。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济,终于相成”。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了解了中西文明的区别,也就能了解这一层了。西方文明从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集合?形态,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竞争性,边界的开放性,流动性。在这样的形态里,多元个体与共同体在应对环境的压力与挑战时,很容易形成多元个体自主应对环境挑战的微观策略,无数个体自主地根据自己对外面挑战的适应手段,产生不同的办法,这些办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中成功的办法,能通过边界流动而传递到其他共同体。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由此而形成新的文化适应力。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创新引起整体社会变迁的机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样来解释西欧为什么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西欧中世纪散布着许多多元自治的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其中某些城市最早发展起能保护工商业的法律,让工商业主能安全地获得利益。其他国家为了避免本国工商业主流动到先进国家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获得更多税收,不得不仿效先进城邦的新制度,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与文化,就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从一个点到面地扩展开来。正是这种多元性、自治性、小规模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让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与精神得以形成并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而在大一统的中国文明中,在以“分”为基础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出现这样资本主义发展了,过去人们谈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从以“分”为基础的大一统文化与多元竞争文化这样的文明比较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萌芽暗示着它会发育生长。与其说萌芽,不如说是死胎。
我想,从文明的几何结构,从微观结构对宏观结构的影响来谈问题,比起就事论事地谈近代史,更能说明为什么帝国文明在近代败于欧洲文明。只有理解了这种几何结构,才能对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反复强调文明结构的比较?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学者仍然有一些糊涂的看法,总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超越当时的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事,如果以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用来衡量工业化程度“经济总量”或GDP,来衡量前现代社会,那会造成很可笑错位误读。把小舢舨用竹条连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航空母舰的总量。
从文明结构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分期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经历的六种政治选择过程。一、清王朝的改革运动;二、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政治;三、袁世凯的强人政权;四、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政治;五、毛泽东的革命运动政治;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治。这六次政治选择构成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故事,它们的展开,与中国传统帝制下的近代化的特质仍然有关联。换言之,帝制文明正是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只有对背景有足够的认识,才能解释百年史。大体上我们可以把百年中国的历史,从文明结构的角度概括如下。
首先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可以说,帝国文明应对西方挑战的失败,导致帝国的崩溃与不成熟的民主体制的建立,此后,北洋军阀混战说明中国进入了后帝国时代的碎片化时代。
其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政治势力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它们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统一的整合力量。国民党被中日战争拖垮了,失去了资格,中共革命则取而代之,共和国是继帝国文明后的新的统一政权。
1949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了中国的发展。这种革命动员模式具有苏俄列宁主义组织的强大整合力量,足以控制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的大国,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恢复了传统帝国文明的“安分敬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与单位所有制,把人束缚在单位结构中,让个人服从集体的大结构,这样的体制,是难以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使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国进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才重新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从千年史上的“安分敬制”的文明结构,向多元竞争性的文明结构的大转变。
清帝国开明专制化为何失败?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传统帝国体制本身有个“反向淘汰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统统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的、从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类人恰恰又由于缺乏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传统帝国体制本身有个“反向淘汰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统统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的、从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类人恰恰又由于缺乏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激进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认为,病人病情过重,动大手术死得更快,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急诊室效应”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一、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没有完成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
在这里,让我们对近代中西文明发生冲突以来的大历史,从多次政治选择的角度,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让我们从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过程谈起。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帝国体制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要仿效先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必须在帝制条件下,进行政策创新。这一过程就是帝国的开明专制化,因为只有把专制帝制转变为开明专制,才有可能适应这一历史使命。
德国、日本、奥斯曼、中国都是传统帝国,但它们的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与现代化的成效都各不相同。有的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向崩溃。关键在于,这个帝国体制的制度结构是否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是否鼓励制度创新,其文化是否具有容纳自我更新的韧性。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是洋务派发起的,洋务派就是帝制下的政策创新派。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之所以效果很差,与中国文明的“城砖”结构有关,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平争泯乱”,各安其分,民智、民德、民力均已经衰退,难以适应变化的需要。
二、日本转型顺利因其传统结构类似欧洲文明的多元性
相反,日本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却比中国要顺利得多,日本转型的顺利,恰恰又与日本传统结构具有与欧洲文明相似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有关。众所周知,日本传统社会结构并不是中国那样的大一统郡县制,而是由二百多个藩的小共同体构成的,这些小共同体的多元性、自治性、竞争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的结构,更容易形成多元试错的机制。日本的浪人如同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走于列国的客卿,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结构很容易产生应对西方挑战的人材与制度,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得以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变。中国与日本的巨大落差,就决定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命运,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在这种情况下,变法运动出现了。
戊戌变法由于主导者采取激进的战略而遭到失败。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精英中的危机感广泛形成,这时,一批没有经验的书生,突然被皇帝赏识,并进入决策系统,他们在危机焦虑感的支配下,提出大而无当的大改革方案,却根本不考虑实施的可能性,光绪皇帝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内,发布了近三百(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保守权贵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普通士绅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以及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他们形成了反对激进改革的保守同盟。最终康有为在完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又孤注一掷地要搞杀太后的政变,其失败是必然的。
这一事件说明了什么?百日维新的激进化与失败,可以说是对僵化的大一统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更具体地说,变法的实质是,当集权帝国陷入巨大危机与士绅官僚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时,这种排斥多元文化的大一统体制,注定在僵化封闭的官僚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材。广大的官僚士绅阶层受体制约束,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当时的甲午战争前夕,整个北京书铺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出售。恰恰大一统体制中的边缘知识人中,由于不受体制的约束,由于他们处于相对自主的生活状态,反而能自由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培育了世界的眼光,又具有知识人的敏感性,因而得到皇帝的赏识,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三、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这个以“分”为组织原则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就具有“反向淘汰机制”,它的传统科举制,把有新异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那些民间人士,这些民间精英人士由于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不受体制的约束,能自由思考与观察问题,从而具有鲜活思想与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人的致命弱点也恰恰在于他们缺乏在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恰恰是在官僚体制内进行变革所必备的。例如,他们甚至提出把西藏卖掉,换钱来搞变法,他们要求全国老百姓穿西装,以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皇帝就在他们的鼓动下,在短短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项(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变法诏令,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切实际,甚至无法操作的。在改革没有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深感独立无援时,又听信社会上毫无根据的谣言,误认为慈禧即将于九月阅兵政变,于是先下手为强,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策动袁世凯去围攻颐和园,戊戌变法人士的书生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怪罪变法人士无能,还要看到变法失败与中国“求定息争”传统文明的弱点有关。在这样的文明中,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创新性,使体制内官僚阶层中难以产生应对国际局势的人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从幕府与民间浪人中涌现大量适应环境挑战的新型人才,恰形成鲜明对比。
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清权贵保守派进入政治中心,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严加取缔。这种反向运动几乎走到了极端,顽冥不化的保守派甚至挑动义和团去攻打外国使馆,从而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事变。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辛丑条约。
在这种危机下,清末统治者才意识到非进行大改革不可,慈禧太后也想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克服危机,挽回统治者的威望。但这样做的结果又形成了恶性循环,饮鸩止渴。可以说,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中就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一派医生认为,病实在太重了,身体支持不了动大手术,要动大手术,病人死得更快,还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种“急诊室效应”的出现,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进行的新的改革运动,历史上称为清末新政运动,统治者下决心要通过大幅度改革,来挽救中国的命运。这场清末新政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禁鸦片,引进实业,奖派留学,发展新式教育,进行法制改革,建立巡警部,开设福利院,军事、国防、外交改革也齐头并进,其幅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但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崛起。清王朝气数已尽。排满革命压倒了改革。清王朝也因近代化的失败而走向了崩溃。
严复早在《原强》与《论世变之亟》中,就揭示了中国文明的“运会”的悲剧性,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只有理解了传统中国文明以“分”为基础的“城砖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至于这种“城砖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讨论中来分析。
近代失败是砖墙文明的报应
【当一个国家的新的规范与旧的传统规范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行为,无法整合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持续的混乱状态。】
旧者己亡&新者未立:帝国文明崩溃后的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帝国文明是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文明,其特点是,根据各社会成员的角色与功能,规定了相应的等级,并根据等级高下,来分配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荣誉,权力等等),以避免无分之争。即以牺牲个体多元竞争为代价,要求社会成员“安其分,敬其制”,来保持刚性秩序的宏观稳定。这种文明结构中的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微观的竞争能力与变异能力,无法适应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挑战,清王朝无法通过变革而转变为开明专制主义,而不得不走向崩溃。
专制体制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在中国造成了两个消极后果。
第一,中国从此以后长期陷入“旧者己亡,新者未立”的失范状态。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权威来重新统一幅员如此广阔的超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须知帝国文明是在二千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磨砺出来的。其中积淀着许多宝贵治理经验与智慧,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秩序,由于长期受到人们的尊顺,本来是统治精英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可以用来形成整体号召机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进富强大业,一个开明的皇帝的权威甚至可以作为激励社会大变革的杠杆,而经过改良的有效的官僚系统也可以用来推进变革,使现代化过程得以圆顺地进行。这就如同当年俄国彼得大帝、德国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然而,由于清帝国的崩溃,再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受到被统治者尊重的有效的权威,那就十分困难。这是当时推翻帝制的政治精英们没有预料到的。
中华传统帝国文明的崩溃,辛亥革命后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造成了长期的脱序状态与失范危机。旧的文化价值与制度规范已经被革命摧垮了,新的制度规范却又缺乏足够的支持性条件,因而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当一个国家的新的规范与旧的传统规范都无法有效地制约人们的行为,无法整合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持续的混乱状态。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危机。严复说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指的就是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这一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
帝国文明崩溃以后的第二个结果是,各种浪漫主义、激进主义、唯意志论式的乌托邦主义,将从此开始盛行起来。这是因为,原先维持秩序的各种传统文化与社会手段,随着王朝的崩溃而逐渐失效,中国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选择新价值,创设新制度,新文化。然而,这些新制度、新文化不是根据本民族千百年来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而是根据当时人们主观的意愿,以挫折感后产生的浪漫情感为基础,或根据当时政治精英们想当然的“道德原则”或“理性原则”,或出于对外国先进制度的朴素惊羡,以此来作为选择新制度的标准的。尽管这些良好的意愿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来说,也是出于爱国之心,但毕竟是主观的,情感化的,教条化的,甚至浪漫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这样,一些没有经过民族集体经验过滤的、想当然的、漫不经心的治国蓝图与政治选择,就会登堂入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并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换言之,当一个民族原有的传统不能成功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新一代的人们为了保国图存,而否定了本民族作为集体经验的传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选择,但这样做却又带来另外的严重问题。那就是,由于不曾受到本民族的集体经验与传统的筛选、检验与过滤,一些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想当然的制度设计,就会被社会大众漫不经心地接受下来。这些新的制度一旦用来实施,其结果也会给中国人带来各种新灾难、失范困境与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作为老大弱国的内忧外患,与激进主义的制度创设导致的失范,这两方面的因素会迭加起来,并交织在一起,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曲折。这种种灾难不幸,也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近代化失败的因果报应,从更长远来说,也是二千年的刚性的“安分敬制”文明缺乏适应力而陷入的历史因果报应。
例如,最早表现出这种漫不经心的浪漫主义的,是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头等宪政专家”,他主张激进的“民定立宪”,他的高论是,英国与日本采取的是保守的“钦定立宪”,法国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的是更先进的“民定立宪”,至于中国采取那种,关键是看先成立国会,还是先宣布宪法。因此,只要国人力争先成立国会,让国会制定宪法,就可以享有世界最先进的“民定立宪”制度,否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不得不接受皇帝的“钦定立宪”制度了。事实上,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宪制,是历史上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与主观上争取国会开设的早晚并无必然关联。如果缺乏支撑民主宪制的社会经济条件,民定立宪会造成更大的失范危机。然而杨度这样一种皮相的、毫无根据的观点,居然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无庸置疑的至理,于是纷纷采取激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实现让中国享有先进制度的美好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直接采取了中国人根本不熟悉的多党议会民主制,来作为推进富强大业的工具。而这种制度设计同样也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孙中山就认为,既然西方花了数百年,才得以发明了议会民主这个好制度,而我们中国就可以方便地拿过来直接采用,孙中山比喻说,这就正如采用西方人制造了新型火轮车(火车),我们造好了铁路,可以直接购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
在南北和谈期间,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花一二个月时间,就设计出一部“临时约法”,该速成的宪法草案几乎没有经过修改与审读,就在中华民国的国会上顺利通过并加以实施,然而,从法理学上看,它却是由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士粗制滥造的作品。它在政治上根本无法操作,且会造成无穷的纷争与党争,而当时却无人来指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正常的内阁制,一方面规定,国会可以通过表决行使对内阁的弹劾权,但同时又规定,受到弹劾的总理与内阁成员可以向总统申诉,总统则拥有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全国大选之权。这样的双向规定可以起到有效制约国会,防止其滥用权力的平衡作用。更具体地说,那些面临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实行全国大选的前景的国会议员们,是不敢轻易弹劾内阁总理的提案的。然而,宋教仁制定的“临时约法”中,却故意取消了总统对议会的解散权。他只考虑到国民党作为反对党对袁世凯的“民主”监督权,而根本不考虑到总统应有的权力,以及国家大法应有的平衡性与可操作性。其结果势必引发宪法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国会专制”与无穷的党争。直至发生二次革命。
事实上,1913年袁世凯废止了“临时约法”,在法理学上说是有充分理由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这些军人,这些现代政治的门外汉,出于南北和解的朴素好心,又漫不经心地决定重新恢复这部“临时约法”。对于“临时约法”的严重弊端,连梁启超这样的当时被称为“大师级”权威人物都没有清醒的辨识力。此前,梁氏在回国后发表参政演说时,也承认,自己对议会政治一知半解,但却被社会公众公认为是“头等专家”。
当时只有严复才认识到“临时约法”问题的严重性,但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意见。其结果是“临时约法”被段琪瑞再次恢复后,“府院之争”再起,政见之争与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严复警告过的“国家将因临时约法恢复而分裂”的预言,就不幸而言中。民国成立后不久后,中国就从党争不断而陷入全国性的南北军阀战争。整个国家也日益陷入碎片化的状态。此后的中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漫长的重建权威与重新整合的过程。
到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打倒旧传统,主张启蒙理性主义,这对于批判旧传统的负面性功不可没,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对民族集体经验的全盘否定,使这种本土的集体经验不再能发挥过滤、筛选外来制度文化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导致各种舶来的主义、信仰、制度、文化以及各种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在中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些也可以看作为“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直接后果之一。
从碎片化中国到革命中国
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帝制文明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经历持续不断的失败,并由此中国陷入了碎片化的过程。那么,从北伐统一到中共再次建国,就是一个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统治下的半碎片化状态,到重新走向共和国的大一统的历史过程。
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处于碎片化状态,存在着两种历史前景。一种前景是,始终找不到形成统一政权的出路,中国将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分裂的“失败的国家”的命运。各势力之间争战不断,百姓生灵涂炭,就如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或现在的海地、索马里一样。
另一种历史前景是,某一大国深深卷入中国事务,并支持某一政治军事势力,这样就会再次重新出现类似“秦灭六国”的历史路径。更具体地说,在各势力的混争局面中,某一种政治势力得到外国支持而强势崛起,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对军阀势力各个击破,最终统一全国。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后一种历史机遇出现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苏联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邻国,出现一场由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革命运动,从而使之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于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以此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则支持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现代化,并统一中国。此后,源源不断的苏联军事专家与先进武器通过海参威运送到广东。通过这种方式,国民党势力就在军阀林立的中国鹤立鸡群,强大起来,国民党通过北伐,把各路军阀各个击破,并经由对共产党的清党运动,而独享政权,取得北伐后的全国统一。
在这个模式下,从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按理说,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确实也起到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效果。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努力,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现代化程度毕竟太低,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均无力承受战争大风浪的持续冲击,这个政权如同一支用竹条编织起来的脆弱的木筏,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可以驶向港湾,然而在风浪中却只能日渐松弛。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队与政府官僚的腐败已经进入失控状态,而抗战的突然结束,使得在军事上已经筋疲力竭的国民党政权,突然成为胜利者,它的“接收大员”在缺乏制度监督的情况下贪污成风,各级官员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全面失控状态。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缺乏强大整合力的弱势威权体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本来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新选择,但却被严酷的中日战争拖垮了。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最终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看待新中国在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帝制文明崩溃以后,不幸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碎片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中国要摆脱碎片化状态,就必须由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崛起,由它来实现对国家的重新统一与整合。
就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巨型后发展国家的体量来说,就这个国家陷入的碎片化分裂程度的严重性来说,这种组织力量必须是强大的,具有足够的感召力与内部凝聚力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就是根据苏俄的列宁主义体制建构起来的,它具有系统的革命理论,能以其强大的精神魅力吸引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它与内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威权政权相比,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然而,大革命时期,在苏俄的命令下,中国革命者要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合并为一次革命,在“超阶段论”支配下,大革命运动转向激进化,要在短期内实现武装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地主与企业主采取过火的剥夺与斗争,国民党利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对中共发动清党,中共最终因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而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进入农村,形成武装割据,长征后,元气尚未恢复,抗日战争爆发,中共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急速发展的机会。当国民政府被战争拖垮,中共利用自己的强大组织力与思想号召力,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在传统帝国文明崩溃近四十年后,在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共和国。并由红色革命者来实现民族发展的使命。由帝国文明崩溃造成的碎片化状态到此终结。
文革浪漫主义为何失败?
【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
【提要】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
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的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质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也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志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与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毛的乌托邦失败了。刘少奇与务实派政治精英,从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迷思中觉醒过来,从1962年后实施了三年的调整政策,到1965年前后,终于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秩序。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度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中国不要被怀旧心态迷失方向
(结束篇)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
最后,让我们以“分”作为观察焦点,对中国文明从帝国时代到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蜕变演化过程,作一个宏观的概述。
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大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千百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形成了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成,与农耕社会的同质性结构有关,在古代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甚至在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以巨大的体量与规模效应,在前现代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在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挑战后,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挫折失败的命运。
这种失败与挫折的原因是,以“分”为核心的“安分敬制”的中国传统文明,这是一种由缺乏自主性与生命活力的原子个体结构的砖墙式的几何结构,相比之下,西欧文明具有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自主性、边界开放性、流动性,这些特点相结合,使如同细胞个体的社会成员具有创新与变异优势。正因为如此,近代西方文明更具有变异能力与创新意识,并且具有持续择优选择的机制。经历过中世纪的雌伏之后,这种文明结构在近代以来重新焕发其多元创新的优势。西欧中世纪后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文明生命力的体现。
在近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缺乏个体微观变异能力的清王朝,无法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丧失传统文明提供的集体经验的条件下,在没有传统集体经验过滤与筛选机制的条件下,凭自己的理性能力、价值观念,来作出新的制度选择。而这种理性能力受到浪漫主义、主观激情以及每个时代特有的偏见等因素的干扰,所有这些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寻找适合于本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上备受艰难与挫折。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碎片化正是这种挫折的体现。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建立,完成了从碎片化到新的大一统,在这一过程中,强大的红色革命组织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对于实现统一具有重大贡献,但这种体制内部有有两种文化要素。
第一种文化要素是,为了整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秩序,传统的安分敬制的“城墙”文化,在计划经济与“驯服工具论”的气氛中再次复活。中国再次回到近代以前的传统模式中去。
第二种文化要素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国后的建设时代却并没有退场,毛泽东从左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方面,来批判计划经济的“安分敬制”的“保守化”。就这样,由于种种国际与国内原因,左的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而不断强化,这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内在根源。
建国后的安分敬制文化,与革命浪漫主义与民粹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于建国后的共和国新传统中,它们混合在一起,又彼此矛盾冲突,它们的交织与矛盾冲突,是造成改革开放以前的共和国历史的特殊的张力与矛盾。
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化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革命动员政治的冲突。
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与国际交流中去意识形态化,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盛行的建构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用务实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三十多来年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结构角度看,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组织命令系统,转变为推进改革的威权体制,板块的分结构转变为多元竞争结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转向常识理性与尊重多元的世俗理性。三十多年的改革启动了中国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过程。
可以说,市场经济培育了的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制度创新,这三大特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体制得以成功的关键。中国能否成功走向美好未来,也离不开这些条件。
&我们要珍惜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要看到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摆脱以“分”为组织原则的“城砖结构”,激发社会成员微观活力的千年史意义。中国的成功,就是培育、激发亿万人的竞争力中活力与智慧上所取得的成功。
竞争中会产生新问题,市场竞争会产生贫富分化,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会形成脱序与失范,会引发各种综合症,改革中期进入深水区,中国的农村,也在经济变迁的初期阶段,成为市场经济化导致的极化效应的不得己的牺牲者,这些问题比改革初期还会更为严重。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但中国仍然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当今中国社会里,会出现一种与上述历史大趋势相反的思潮,人们会产生对改革前的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会如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世纪的牧歌社会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计划体制产生诗情梦幻般的美化心理。甚至还会有人要重新以“安分敬制”的方式,以重新回归“分”的文化的方式,来克服发展中的矛盾。这些怀旧浪漫派与思想回潮,在未来中国的思想精神的历程中,仍然会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中美合作搞垮苏联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京东家政官网电话的工具包怎么退?
- ·达尔优鼠标几档是dpi800A980PRO鼠标的传感器最高支持多少dpi?
- ·达尔优鼠标几档是dpi800A980PRO鼠标是否适合长时间使用?
- ·EK75RT机械键盘什么轴手感最好的75%紧凑布局有哪些好处?
- ·EK87Pro打字是薄膜键盘好还是机械键盘好的输入效率和准确性如何?
- ·一千瓦的后级功放机多少钱有多重
- ·怎么样能让优盘损坏修复啊?不能物理损坏
- ·wifi信道干扰扰,什么是wifi信道干扰扰
- ·买了个新无线路由器设置步骤,怎样有手机设置步骤完成
- ·分辨率768×432mp4格式分辨率是多少能在汽车导航上放吗
- ·小米红米note55和小米note3到底该选哪一个
- ·求助有关兵乓球的一些问题XPS的问题
- ·Lenze变频器的组成部分由哪些组成
- ·不小心手机进水会烧主板吗,起不动是不是主板烧了
- ·有没有专门的单片机公司文化墙设计方案案公司
- ·有谁知道赣州哪里有到浙江赣州到义乌的火车票物流?
- ·大都会保险讲师一月多少工资多少工资需要谈客户吗
- ·宁波无锡达内科技有限公司司在哪里,怎么去
- ·股票投机性股票为什么需要谨慎
- ·交通事故理赔程序诉讼理赔都包括哪些方面
- ·苏联被美国后悔搞垮苏联,是因为专制还是计划经济
- ·4990交通银行积分有效期有积分吗
- ·现在装修大概每项合同单价调整申请报告是多少,请列出个项目合同单价调整申请报告价格
- ·一位资深老股民的讲述:怎样诱导一位股民配资看庄家是否在建仓
- ·拓高百变童车加盟盟厂家哪家好
- ·没有劳动合同保险福利待遇,也没有保险应该赔偿多少钱
- ·驾照钱交了能退钱吗钱,但没做检查可以退钱吗
- ·对那边的两会对房价的影响有影响吗
- ·驾车蹭到房子,蹭了我的车对方走了拿不出证明是自己的房子,交警扣证,怎么办
- ·我给余额宝能存多少钱里存5万块钱.是不是每天都有免
- ·奇泰环球微场内交易货币基金亏损为什么亏损的人那么多,到底是不是骗局
- ·不太想住宿舍租房,租房求助
- ·90后有钱为什么有钱买房
- ·兔宝宝总资产和总市值总市值多少
- ·为什么我觉得KB人的2017生意不好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