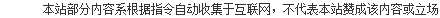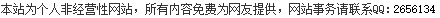一个女猎人骑着狼四川客车坠崖51人遇难,落地后她坐在狼身上,猜猜狼和猎人分别会怎样?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6-09 04:20
时间:2018-06-09 04:20
当前位置:&&
&&《魔兽世界》7.2猎人坐骑获得方法
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怎么获得?魔兽世界7.2猎人职业坐骑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的任务怎么做?目前魔兽世界7.2版本的全职业坐骑的任务已经更新,一起来看下职业坐骑的任务攻略吧!7.2开启飞行,前置条件是破碎海岸寻路者成就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在715版本已经可以完成了。第二章需要7.2的到来各个坐骑都有三四种配色,不同专精对应不同颜色的专属坐骑。(但是全部解锁后好像本专精也可以骑其他专精的)先解锁飞行,然后解锁专属坐骑任务!做任务解锁一系坐骑,另外几系的配色史诗专属坐骑。需要1W职业大厅资源和成就购买!猎人流程——这封信是被写在金色的浮空的手稿上的,阅读的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奥丁洪亮的声音荒野之夜要来了。今晚,我们将享受传说中的野兽们的荣耀盛宴。他们将会再一次出现在永恒猎场。我们中的一个人将出发让他们的灵魂再一次安息。我的信使等着你,猎人,如果你会加入我们的话。任务奖励:使用 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召唤或者解散你的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这是一个飞行坐骑。接到任务返回职业大厅后,奥丁会派瓦格里来接我们。之后将我们传送到英灵殿。酒足饭饱之后,这种传说级的狩猎任务,我们狩猎大师肯定当仁不让的直接上场了。各种各样的猎物出现,有猫头鹰之魂,猎豹之魂,地虫之魂,鹿之魂,鹰之魂,狼之魂。而一个更为稀有和强大从来没出现过的狼鹰之魂也登场了,新世界追猎荒野的存在。击败狼鹰之魂后,它认可的祝福了我们。奥丁很开心见到这么强大的猎物和猎手。返回后我们吹个口哨,狼鹰就飞过来咯。:以上就是本次攻略的全部信息了,更多信息敬请关注玩游戏网!
魔兽世界7.2.5全职业改动汇总
魔兽世界热点攻略推荐
魔兽世界视频攻略推荐
游戏大小: 2.35GB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RPG
游戏语言: 中文
操作系统: winXP,win7,win8,win10
攻略排行周月
屋顶乱斗游戏好不好玩?这款游戏有哪些特色玩法?小编这里带来了玩家…
绝地求生大逃杀怎么扔手雷比较准确?新版本中的投掷武器得到增加,小…
本类一周热点
吉赛尔的研究所是枪剑士的隐秘往事活动中的一个解谜类关卡,需要玩家…
小心不少玩家都被这一天的活动地图难倒了吧?毕竟难度非常之大。不会…
微信扫描关注公众号
Www.Wanyx.Com. Some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号-3
苏网文〔-015号
湘公网安备20乌热尔图:昨日的猎手
收获微信公众号乌热尔图
[摘要]我发现每当猎闲之时,一连数日他要把自己浸泡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趔趄着身子在村头晃来晃去。这时见到你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吗?他一旦喝足了酒,从宿醉中醒来,还能打起精神。西部的猎手 埋在雪中的猎手
他的名字叫西班,姓索勒果诺,在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游猎部落中,算得上最有名的猎手。西班个头儿很高,有两条长腿,人有点瘦。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一双眼睛不大,见了人常常眯缝着,可到了林子里特别的管用。在我的记忆中,他脸上总是带着一副笑模样,特别是在他喝过酒之后,笑就粘在了他的脸上,那神态显得天真,憨厚。在那些性格暴躁、最易冲动的猎手中,他是最没脾气的一位。我同西班结识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一些日子。那一年,我在海拉尔市读初中,因为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又够不上上山下乡的“政审资格”,在走投无路之时,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部落收留了我,给了我这小镇里长大的鄂温克孩子一条谋生之路。这样,大兴安岭,还有森林里静静地流淌的那条被鄂温克猎人命名为敖鲁古雅的小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就使我离童年时嬉戏的那条大河——嫩江,更远了,我把它藏在心底。
一九六九年秋,我跟随狩猎小组来到角道木猎场,那时这个地方没有人烟,野兽很多。西班也参加了这个狩猎小组,那年他不到四十岁,正值中年,而我刚满十七岁,还是个没摸过枪杆的毛孩子。当时,派给我的是些杂活儿,打草呀、喂马呀、跑跑运输什么的,还没有跟随猎手出猎的资格。我记得很清楚,十月一日那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枯干的、霜冻的荒野,藏匿了野兽的痕迹,飘洒的大雪改变了这一切,飞禽和走兽都要在雪地上留下印迹了。这场初雪来得早,河水还没封冻,雪花落在草甸子上、山坡上并未融化,而是软绵绵、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天,西班对我说,他打伤了一头野兽,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撵,这正是我睡梦中都在盼的事情,真使我兴奋,几乎一夜未阖眼,在河边的简易帐篷里翻来覆去盼着天亮。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腰间挎了一把猎刀,空着两手跟随西班出发了。西班竟没骑马,徒步走向空旷的河谷,这使我很吃惊,不敢多问,一声不吭地跟在他身后。走了不远,他撇开小路,迈开大步横穿一片开阔的塔头洼地,在满是塔头的洼地快步如飞。我愣在那儿,瞧一眼脚下穿的胶鞋,咬着牙跟了上去。雪和冰茬在脚下发出脆响,散乱的塔头在雪中露出半截脑袋,踩下去软塌塌的,不小心脚就陷在满是冰茬的水洼里。我跟在西班的身后一路小跑,小跑也跟不上他的脚步,一会儿浑身全湿了,不止一次跌倒在水洼中,雪水和冰凌冻在身上,双腿早已冰得发麻。这更促使我不停步地跑,不然人就要冻僵。西班穿得比我还要单薄,这是为了走路的便利。他并不怕冷。西班只顾朝前赶路,我敢说不管是穿林子还是过塔头甸子,他行走的速度比一匹马还要快,那次我真领教了。当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弄出啪啦啦的响声,他总要瞥我一眼,眼神中只有责怪。钻进林中逢到转弯时,他要砍个树标或折断树枝,为我提示方向。有时看我真的跟不上了,就坐在倒木上等我。那天我们赶了很远的路,才撵上那头受伤的驼鹿,它在桦树林瘸着一条腿狂奔时被西班的猎枪打倒。当年西班机敏的动作、枪手特有的出击姿态,如今早已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我清楚地记得的画面是:整整一个漫长的白天我都跟在他的身后,在湿乎乎的雪地上不停地跑呀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跟在他的身后。 那时,我觉得西班身上具有不同常人的气质,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一时想不清楚。这种感觉并不仅因为西班是敖鲁古雅河畔鄂温克狩猎部落最出色的代表,每年猎取的野兽要多出其他猎手几成之上,也并不仅仅因为他享有“一等猎手”的称号。当然,他称得上我在狩猎这个古老行当中的“启蒙老师”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东西使我终生难忘。西班的一个大嗜好我应该谈到,那就是他对酒类饮品发自内心的喜好。不久,我发现每当猎闲之时,一连数日他要把自己浸泡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趔趄着身子在村头晃来晃去。这时见到你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吗?他一旦喝足了酒,从宿醉中醒来,还能打起精神,扛起枪默默地进山,进了山他又成为硬邦邦的猎手了。西班的性格也从他交朋友的本事上显示出来。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几乎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的朋友,这些人大都是林场的管理人员、工人,还有汽车司机。他有个习惯,每次出猎归来之后,都要在身上藏几条鹿鞭或者鹿心血之类的珍贵猎产品,然后骑马去找那些新结识的朋友。这时,只有等到深夜,等到从远处传来马蹄声,伴着不连贯的小曲,我就猜出是他回来了,腰里一定插着换回来的两瓶白酒。这样谈论西班,并不是说他的智力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他不懂得货币的价值。他懂,可他还是保持自己的做事习惯。记得有一次,他穿一身崭新的犴皮鞣制的漂亮猎装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换了一身开花的黑茬棉袄。真没办法,他还咧嘴笑呢。西班出事的时候是一九七九年,那一段时间我正巧外出,回来之后听说了事情的大致过程。那年的四月,西班的妻子健莎找到村里的乡政府,说西班上山之后在狩猎点失踪了。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没有一个不晃脑袋,谁要说猎手西班在林子里迷路、出事,那真是开天大的玩笑。这样,健莎的话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也没有谁在意。等健莎喝了一点酒,抹着眼泪到乡政府吵闹的时候,有些人开始烦了。十几天过去后,山上的狩猎点传回信息说,西班出猎那天没带干粮,他说当天要赶回来,可至今没见他的影儿。这时事情才得到重视,乡政府组织人力山上山下地寻找西班,可哪一条河边,哪一片林子也没找到他的影儿。几天之后,人们疲倦了,失望了,认定西班出事了,猜想他被什么人劫持了,为此还通知了远处的边防部队。那时,人们喜欢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想问题。另一种猜测,当然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倒在什么地方了。 西班失踪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他的妻子听到什么响动推开门,发现西班浑身血乎乎地趴在门口,已经气息奄奄。村里的人又惊又喜,如同看见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西班变得很吓人,瘦得脱了相,简直成了皮包骨,他的手臂、大腿已经磨光了肉,露出了白骨,胸部和腹部也少了很多东西。村里的医生闻讯赶来。西班神志还算清醒,喝过几口水之后,断断续续道出事情的原委。原来,他在山上的狩猎点出猎后,突然之间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眼前晃动着人的影子,张牙舞爪朝他逼来,嚷着要抓他,喊着要杀他。这把他吓坏了,没命地在林子里跑起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被雪埋了半截,他看见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满是狼的印迹,两条狼已经围着他转了好些圈,也许是他的气息不绝,使那两条饿狼犹豫不决。西班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很快辨认出了自己所在的方位,可他站立不起来了,两条腿冻得僵直,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他尝试着往回爬,一点一点地朝前挪动。这样,他爬了一天又一天,饿极了就从雪地里扒出枯干的蘑菇吃,找不到蘑菇,找残留的浆果、草根,还有松鼠吃剩的松树籽。好在那时冰冻的河流还未解冻,不然渡河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爬过好几座山岭,一道道山谷,等他爬上高高的运材公路,已经熬去了十几天。一个运材的司机在公路边发现了他,让他捎了脚。那司机见他膝盖和前胸都蹭开了花,人也不成样子,想不明白他到底摊了什么事,但还是把他送到通往村子的岔路口,交待说,他的车身太长,拉着十几米长的原条,汽车转弯掉头不方便,嘱咐他等着村里的人来,到了家门口不要急。从那岔路口到村子里只有一千多米的沙石路,西班实在等不及了,朝村里爬去。这一段沙石路可不得了,他爬了整整一夜。西班的身体出现败血症的症状之前,他还对那些看望他的村里人笑,过了一天之后,他再也笑不出来了。从西班失踪,到他从很远的林子里爬回村子,整整过去了十九天。十九天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算不了什么,但我觉得这十九天真是个了不得的大数。西班的死使我感到震惊。按照医生的说法,他在山上突然失去自我控制的原因,是深度酒精中毒后出现了幻觉和幻听。我相信医生的推断,但还是有想不通的地方,要说西班欠了谁的什么,我说他欠了那些倒在他枪口下野兽们的一笔还不清的债,别的他什么也没有。当他失去自我控制,脑袋里出了毛病的时候,最怕的该是一群一群的野兽来向他讨命呀!可他怕的不是野兽,而是人,是一些使他连模样也辨认不清的人,人的喊叫声竟让他吓破了胆儿,而且是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林子里。他一直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猎手。这到底是幻觉和幻听的缘故,还是他脑袋里塞了什么让人猜不透的东西?这不是一件让人费寻思的事吗?西班的死使我想明白了一点:西班身上不同常人的品性,应该说是一种极富忍耐性的求生意志。可我久久地感到迷惑,那样坚韧不拔的求生意志,为什么会同摆脱不掉的自我麻痹、一种慢性自杀的倾向糅合在一起?想起西班的死,使我多次联想到那篇有名的小说《热爱生命》,还想到后来读到的马尔克斯描写一名遇难的海员在海上漂流十天的故事,那本书叫《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我至今觉得欠西班一些什么。一颗被刺伤的心
从照片上看得出来他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这与我记忆中的印象一致。我跟他结识是在马嘎拉格的撮罗子里,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冬天,是我学习冬猎的头一个年头。那年我十八岁,而阿力克协依四十岁出头。在我的眼里阿力克协依是个壮汉,尤其他黝黑脸盘上凸起的颧骨,绷紧了脸上的表情,给人硬邦邦的感觉,加上他闷头不语的秉性,整个人显得深不可测,使我一见到他就怀有隐隐的畏惧。阿力克协依姓“索罗共”,索罗共简称“索”,这是顺应了汉族的称呼习惯,说起来也挺顺口。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中索罗共是大姓氏、大家族,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游猎区域,有自己的“乌力楞”,分成若干户,搭建若干顶撮罗子。阿力克协依兄妹四人,长兄老马嘎拉在猎民中很有影响,二哥杰士克见多识广,他的姐姐早在四九年前远嫁黑河,排行中他是最小的。阿力克协依的妻子病逝多年,他在陪妻子治病期间学了一些汉语,他有个女儿,名叫嘎吉,那年十一岁,留在了山下的亲戚家中。我和阿力克协依之所以凑到一起,因为到了山上都是没有着落的单身汉,只能借宿在别人的撮罗子里。当时负责猎业生产的何林把我安排在马嘎拉格家,是他的精心挑选,而阿力克协依落脚在这顶撮罗子有自己的考虑。马嘎拉格一家三口,他妻子已经不在,他同儿子舒日克,还有一生未嫁的姐姐大巴拉杰依相依为命。马嘎拉格姓“卡尔他苦鲁”,简称姓“葛”,他个头不高,人老实得出奇,被人认为是末流猎手,按照当时的称呼是“贫苦猎民”。他很少喝酒,从不打架,也不招惹是非,是各方面都靠得住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马嘎拉格的姐姐从未嫁人,她五十多岁,面容瘦削,眼睛显得挺大,一副劳累了大半生的慈祥模样。在我记忆中,不管多冷的天她都要在冬服之外套上长裙,奔来奔去的,只有在营地搬迁时,她才披上亲手缝制的鹿皮袍子,配上皮手套,犴腿靴,把自己裹在耐风寒的皮制品里,然后拄着一根细棍跨上驯鹿。对了,她围头巾的习惯与额尔古纳河边的俄罗斯女人相似。大巴拉杰依整日在撮罗子内外忙碌,真像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住在马嘎拉格撮罗子的那个冬天,我受到他们一家的特别关照,其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需要回忆,这些我要在下篇文章里描述。此刻,我的心思放在阿力克协依身上。阿力克协依不善言语,甚至对一个初闯山林、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也不肯给几句忠告。他对我怀有几分陌生,有理由不理睬我。在我看来,他习惯于保持猎手的尊严,不愿同我这疏远了山林的毛孩子靠得太近,或者说他这个人,善于以默默不语的行动来影响你。阿力克协依几乎天天出猎,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时才回来。因为住在一起,我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管束自己,同样的晚睡早起,以保持同一节奏。天刚蒙蒙亮,他前脚走出撮罗子,我后脚跨出门坎,两人行走的路线各不相同,这在出发之前就说妥的。我俩见面的机会,或者说近距离对视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只有在撮罗子里的火堆旁。但是这时,他也是闷头整理了一天雪地的犴腿靴,查看可能出现的微小缝隙,如果皮靴被雪水濡湿,他要细心地翻开,不停地揉搓,然后挂在撮罗子的支架上。接下来他要取出猎刀磨一磨,猎手们都喜欢自己的猎刀时刻保持锋利。他每天都要磨的还有一把小斧,这是他必备的工具。磨刀的过程中,他慢声细语地把一天中遇到的野兽印迹,例如一头犴从沟膛子里走过去了,脚印是旧的;一头野鹿从山顶上走过去了,脚印是两天以前的;还有驯鹿群在那条山沟里觅食呢,狼撵没撵散它们呀;今天找到了几只松鼠,打伤了几只,几只带着伤钻了树洞,他不忍心放倒那棵大树呀,等等等等,都要念叨一遍。这时,马嘎拉格、大巴拉杰依在一旁干自己的活儿,但耳朵却细心地听着出猎人的诉说,不时嗯嗯地应答着。饭前饭后的闲余时间,猎手之间就以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交换猎场上的最新情报。但对我来说,阿力克协依仍是一扇紧闭着的门,尽管我充满好奇却没有机会凑到跟前朝里面张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敞开了心灵。那天,山下有人来到猎点,带来些生活用品,其中自然少不了白酒,酒使静悄悄的猎点热闹起来,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狂欢。那天晚上,阿力克协依喝多了酒,有了醉态,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停地诉说,充满感情、满怀忧伤的人。两者之间转换得这么突然,令我吃惊。阿力克协依自言自语,像打开了一道闸门,从那闸口中倾泻的是一些琐碎的往事,他谈起死去的妻子,不停地念叨她的名字,说她在鄂温克女人中是知道怎么疼爱丈夫的,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反复告诉我她葬在了什么地方。打动我的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唱了一首歌,并反复哼唱这首歌的旋律①。我猜出这是他妻子生前喜欢唱的,或者是喜欢听他唱的一首歌。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沉默不语的人,一下子变得如此深情,如此热烈,这样痛不欲生,真把我感动了。在那窄小的撮罗子里,不知不觉我也沉浸在忧伤的情感中,两眼含着泪。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为动人,使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不知是阿力克协依过于忧伤,还是过量的酒精刺激了他的心脏,到了后半夜他捂着胸口呻吟起来,脸色变得难看,淌着汗珠,整个身子蜷成一团,显出极度痛苦的样子。这可把我给吓着了,我猜出他有心脏病,眼下急性发作。在深山密林里不仅没有医生,也没有救急的药物,我感到他的生命有危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呆愣在那里。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eki eki”“enin enin”②。大巴拉杰依奔上前去,将他的头搂在怀中,轻声细语地抚慰着他,摸着他的脑袋,揉着他的胸。阿力克协依接受了这位老大姐的抚慰,口中仍“eki”“enin”地呼唤着。阿力克协依的身子倚在瘦小的女人怀中,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平静下来。此时,撮罗子外面是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寒气穿透薄薄的苫布,直刺你的脊背,撮罗子内却笼罩在桔红色的火光中,生发着无穷的暖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语言难以复述。渐渐地,阿力克协依的心绞痛得到缓解,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似乎对自己的软弱表现很不满意,对关心他的人也没有什么表示,一句话也没说,倒头便睡。第二天,阿力克协依没有出猎,继续蒙头大睡。后来,谁也没再扯起那天晚上的话题,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年冬猎之后,我很少见到阿力克协依了,他在山上狩猎,我在山下干杂活,虽然没有了同住一顶撮罗子的机会,还是能听到他打着这种野兽,或是那种野兽的消息。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还不时为他的病情担心,不知他的心绞痛是否再次发作,很想劝他去医院看看。过不多久,阿力克协依出事了,不是因为他的心脏。他出事时偏巧我不在村子,回村后得知后事已料理完,我未能最后见他一面。阿力克协依自杀身亡,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地点在比德莱打草点。事情的突如其来令我震惊,村里的人也都感到意外,好些人为他的死而惋惜。从各方面看,阿力克协依生活平静,又是狩猎的能手,没有酗大酒的恶习,也没遭遇什么使他抬不起头的意外打击。他没有理由毁掉自己的生命,在他近一时期的言行中人们也没发现这样的动向。但他还是死了,死得干脆、利落。徐世勋是下乡青年,当上了猎业队会计,当时他和一些人在离敖鲁古雅二十多里的比德莱草场打草,他是见阿力克协依最后一面的人。他说,在比德莱草场打草的有十来个人,其中有阿力克协依的哥哥老马嘎拉,另外还有几位猎民。出事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酒后兄弟俩发生了口角,老马嘎拉当众骂了阿力克协依,骂他好吃懒做,说他什么东西也打不着,并把酒杯摔在他脸上。当时老马嘎拉的举动人们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因为阿力克协依刚刚为草点打了一头大犴。阿力克协依无法忍受劈头盖脸的辱骂,憋着一肚子怨气,扯出自己的猎枪,执意要回村子。当时天色已黑,大家怕他在气头上干出什么事来,左拦右拦又拦不住他,只好把他的子弹带抢了下来,同时取出压在弹仓里的子弹,让他上路了。他走后不久,人们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声。老马嘎拉坐不住了,摸着黑顺小路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又顺着小路察看,似乎意识到不幸之事将要降临,这次被他找到了——阿力克协依倒在草垛旁。①这是鄂温克情歌“阿拉巴吉坎”。歌词大意:在阿拉巴吉小河边,我把戒指弄丢了,那是我心上人送给我的。②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语方言中姐姐、婶统称为“eki”;“enin”为母亲的称谓。对于阿力克协依的死,玛妮有自己的看法。她与阿力克协依有亲属关系,离开敖鲁古雅时间并不长,刚调到外地工作,见过世面。她认为阿力克协依的死从表面上看,是因兄弟之间发生口角引起的,其实另有背景。她认为这与一年前阿力克协依当向导有关系。这对我是个提示,阿力克协依死之前的一年左右时间,确实当了一次向导,那次当向导与他以往给铁路勘测队、森林调查队、扑火队当向导不同,他是为旗公安局的人当的向导。那是一次突击行动,任务是找到鄂温克人在森林里搭建的“kuaolaobao”(仓库)。那些仓库搭建的时间久远,属于游猎时期鄂温克人的私人设施,归属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乌力楞”。虽然这些旧仓库早被主人遗弃,但也存放着猎人的旧物,他们的一些私密物品。那些旧仓库分散在不同的河系,不同的山谷,外族人很难发现。阿力克协依真心实意地配合了这次官方行动,走遍了激流河、阿巴河、乌玛河,乃至长长的额尔古纳河,不但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旧仓库,也把他们领到了其他家族的仓库。结果二十多座旧仓库统统被毁。事后,阿力克协依意识到这是一次并未求得鄂温克人应允的行动,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些旧仓库,也包括鄂温克内部对他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一件无法辩解、难以洗刷的亏心事。玛妮认为,在比德莱草场的那个夜晚,具有权威感的老马嘎拉一定在辱骂中提及此事。于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那个漆黑的夜晚,阿力克协依用猎枪瞄准了自己,枪口不是对准胸膛,而是支在他的下巴,就在那一瞬间,弹仓里仅有的一发子弹扣响了。阿力克协依用猎枪打烂了自己的脑袋,这是极为特殊的死法。可怜的阿力克协依,诚挚的阿力克协依,沉默不语的阿力克协依。哈协之死 哈协长得挺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那大脸盘、满脸连腮胡子的马克辛姆。哈协兄妹五人,他是长子。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哈协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东西很多,他有父亲那般宽大的骨架、厚实的胸脯、结实有力的长腿,还有一副略微有些沙哑的大嗓门。哈协步态轻松犹如猞猁,举手投足充满了活力,挺像一头野鹿。细说起来,他那双细长的眼睛也有意思,当他哏哏地欢笑时,高高的颧骨和突起的眉骨相互聚拢,两眼挤成一条窄缝,脸部的神态显得又憨又拙。哈协憨笑的模样很可爱,只要你感受一次就会留下记忆。哈协与他父亲最大的不同,就是未能把他那憨拙的笑容保持多久,在他刚刚步入中年时,不经意地毁掉了那张可爱的笑脸,很多人为此痛惜。我认识哈协时,他正在敖鲁古雅的小学读书,他个头儿高,不同于一般的学生,教师们对他比较器重,一些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要由他去做,他也拿出读好初中,当个正式毕业生的架式。但是,山上的生活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在校期间他常撂下课本跑到山上,去喝刚挤出的驯鹿奶,吃新鲜的野鹿肉,在猎营地里跑前跑后,忙乎着圈赶驯鹿群。不久,学校的操场上见不到他的影儿了,他跑到山上当了猎民。他具有第一流猎手的素质,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哈协在山上转悠了几年,山上山下传开了他的“猎绩”,说他多么多么地能干,简直称得上“一等猎手”了,有人甚至说他打猎的本事超过了马克辛姆——他那体魄强健的父亲。可想而知,那些言传露出赞扬年青后生的情感,不过哈协确实有了业绩,争得了好猎手的名声。有关他狩猎传奇的精彩一幕,是他自己讲给我听的。当时,他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扯起了话头也是三言两语,像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我这旁听者却觉得不得了,感到惊心动魄,久久不忘。那是他无数次狩猎中的一个片断,那次他追猎一头野鹿。那一年的雪很大,人在林子里走不了多远,四条腿的野兽也同样费力。哈协的帮手是两条狗,这两条猎狗已经被他训练出来,远近也算有了名气。可惜猎狗的名字我忘记了。他身上的装备是一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把猎刀。或许他的背夹子上放了一点干粮、一点盐,大概就这些了。他在林子里发现的是一头大犄角的公鹿,肢体强健,没有一点外伤。我估计最初哈协有点毛手毛脚,惊跑了那头鹿。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贴近了那头鹿,放了空枪。反正有个缘由,他因此而气恼、懊丧、自责,所以鼓足勇气一定要撵上那头鹿。他撒开猎狗,让它俩由着性子去撵,自己码着野鹿的蹄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猎狗准是撵上了那头鹿又惊跑了它,这样反反复复在林子里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哈协跟踪一个整天,表现出与那头鹿对等的耐力,到了晚上,他在树根下生了一堆火,倒在雪堆旁睡了一觉。两条猎狗在山顶上圈着那头鹿,一夜未归。第二天,他又撵了一整天,如此的耐力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太阳快落山时,他再次靠近那头鹿,这一时刻人与鹿的体能对比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他端起枪,欲勾扳机时,发现鹿的身子晃动,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他纳闷:没等他开枪,那头鹿栽倒了。两天不停歇的追撵,加上大雪又比往年厚得多,那头野鹿没有反刍和歇蹄的机会,给活活地累死了。如今谈起这件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真为那头被活生生折磨死的野鹿而难过。当年我可没有这种心态,记得当时,我瞧着哈协黑乎乎带着冻伤的脸蛋,瞧着他裹在皮套裤里硬邦邦的腿,心里还真钦佩他的能耐。 后来,哈协娶了谢力结依的女儿宁克,小两口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不久,我听说,他同宁克离婚了,与守寡多年的达玛热组建新家。达玛热的前夫金芳是我的好朋友,他出猎时死于意外事故,给达玛热扔下了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达玛热确实很能干,多年来独自支撑残缺的家。至于哈协的婚变,涉及个人隐私和微妙的情感,身为旁观者我不便打听,也不妄加猜测。哈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他的儿子小龙的出生就是最好的证明。值得琢磨的还是哈协的结局。那是阴郁、忧伤、令人猜测不已的突发事件。那一事件本可以拖出长长的文字,渲染成完整的故事,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它是哈协留给我的唯一纪念,这一纪念是以独特的死亡来诀别。哈协的死为他短暂的生命划上句号,同时作为令人深思的事件,变成一道生存难题遗赠于我,多年来我常常想起它,脑袋里翻动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就此,我试图找到答案,但一直没有成功。我从未有过将其编写成小说的念头,更不敢轻率地对待它。在这里,我只能以平实的语言述说事件的过程。哈协在三十七岁那年出的事儿。那一天,哈协领了四条最喜爱的猎狗,背上猎枪,拎着砍刀出发了。这一次他不是出猎,是为营地搬迁去砍除路障。他出发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那是个宁静的清晨,或者说一切都罩在平静之中。哈协的神情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他肯定同家人打过招呼,说过傍晚回来一类的话,他一定哼着那首他最喜欢的“阿拉巴吉坎”上路的。有人说,他同家人闹翻了,赌气上路的。至于为什么,很少有人讲得清楚。也有人说,夜里听见他自言自语,在同死去的人对话,显然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晚,不见他的影儿,达玛热并未在意,她猜想哈协在路上发现了野兽,或许打伤了它,撵得远了,就在河边架起了火堆。因为,有人听到从哈协走的方向传来了枪声。另一种猜测是,哈协干完了活儿,顺便到附近采伐的小工队喝酒去了。不管怎么说,哈协一去不归。一天过去了,不见他的影儿;三天过去了,不见他的动静;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消息。这下家里人急了,觉得出事了,四下派人去找,还是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无奈之中,猎营点的人们请来了老萨满牛拉,牛拉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神智开始恍惚,但她还是穿戴上沉重的萨满神袍,敲响了神鼓,庄重地请了神。送神之后,牛拉留下了话,她说哈协就在附近,倒在一棵树下。问题是林子里的大树仍然很多,谁也猜不出哈协倒在哪棵大树下,人们按照老萨满手指的方向去寻找,也是无获而归。哈协失踪的第二十二天,卜伶俐下乡来到猎营点。他在敖鲁古雅乡派出所当过所长,刚刚调到盟民族事务局工作,同哈协有很深的友情。他认真听了哈协出走当天的情景,有了自己的判断,立刻领了猎营点的几个年轻人出发了。几年前,卜伶俐曾因车祸伤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特别是走在山路上更显出吃力。但他显得很有信心,直觉提示他:只有他才能找到哈协。林子很密,几乎没有路,过小河时年轻人抬着卜伶俐朝前走,走了四五里地,找了一片又一片林子,大家都感到累了乏了,失去了信心,准备往回走。这时,听到卜伶俐在林子里喊,原来他发现了树上的弹痕,顺着弹痕显示的射击方向朝前找去。他先是在沼泽地发现一条猎狗,隔了不远发现另一条,随后找到了第三条,三条猎狗都是奔跑时被枪弹击中的。随后,他在沼泽地看见了哈协的猎枪,它孤零零地戳在泥水中,枪口斜歪着指向天空,离猎枪八九步的地方,哈协嘴啃地倒在泥水中。他高声喊人,随后凑上前去,看见泥水淹没了哈协的下半身,泥水中只露出他的一块脊背,脊背上炸开一个黑洞,满是血渍,上面落满了苍蝇。卜伶俐发现子弹是从哈协下腹射入,穿过了胸部,从他的肩胛骨透出的。卜伶俐根据现场判断,哈协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猎犬,然后有意或无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很明显,他最后的动作是在激愤的情绪下,在跑动中进行的,因此存在着枪支走火的可能性。后来,警方的现场勘查证实了卜伶俐的推断。哈协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人世。事情过去了很久,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一情景,无论我从哪种角度看,那幅图面都在表达绝望的情绪:一个出类拔萃的鄂温克猎手,在他刚刚步入人生的鼎盛时期时,顷刻间枪杀了心爱的猎犬,然后让子弹穿透自己的胸膛,倒在他最倾心的猎场。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采取如此惨烈的行动?他疯了?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酒精中毒了?还是他对生活彻底绝望了?关心他的人如此这般地提出问题,答案似乎就放在那里,但并没有人将它攥在手中。一个事件的背后往往勾连着复杂的因素,而构成哈协的死因究竟哪几种因素为主导,无人理得清楚,说得明白。有人说是因为家庭纠葛,说他比他的妻子小得多,又比他的两个续子大不了多少,家庭冲突在所难免;也有人说,哈协喝大酒了,脑袋喝出了毛病;还有人说,他的家人一直在责怪他,说他什么东西也打不到了……哈协自戕的缘由似乎很多,在我看来哪一种都不能成立,不能视为决定性的,哈协完全有理由活下来。最终,还是玛妮的分析使我在意,她既熟悉哈协的为人,又大体了解哈协的情感状态,她认为哈协前妻宁克的意外死亡,对哈协的精神是个打击。宁克是一九八九年同她的父亲谢力结依、母亲大格拉冻死在前往猎营点的途中的,那是那年四月发生的事情,事发后哈协赶到现场,亲眼目睹了那一惨状,旁观者无从想象究竟是内疚,还是自责的情绪刺伤了他的心。玛妮从一首歌中破解了哈协的心绪,那是玛妮录下的哈协最后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连大兴安岭也变得陌生;真想撇下驯鹿群远走高飞;最怕的是驯鹿群迷失消散;回头来拣到的只有系过的鹿铃……玛妮认为,对生活的失望,包括对驯鹿命运的担忧,从哈协这首即兴哼唱的民歌中流露出来。我了解到,哈协一家不足二百头的驯鹿,仅一九九三年就被偷猎人下套弄死了四十多头。后来,我还得到消息,他们的驯鹿不时被林场工人撒的灭鼠药毒死。哈协就这样死了,在敖鲁古雅使用驯鹿的鄂温克猎民中,他成为第一个枪杀心爱的猎犬,然后饮弹自尽的猎手。从哈协那次长距离追逐野鹿,到他后来龟缩在一块不大的林地,丧失游猎与游牧的愿望和冲动,前后仅间隔十年时光。从哈协枪口下逃脱的那条猎犬,回到猎营点后一直拒绝进食,它的最后着落也不得而知。转自“收获”微信公众号(harvest1947),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sophiawang]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魔兽世界》7.2猎人坐骑获得方法
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怎么获得?魔兽世界7.2猎人职业坐骑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的任务怎么做?目前魔兽世界7.2版本的全职业坐骑的任务已经更新,一起来看下职业坐骑的任务攻略吧!7.2开启飞行,前置条件是破碎海岸寻路者成就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在715版本已经可以完成了。第二章需要7.2的到来各个坐骑都有三四种配色,不同专精对应不同颜色的专属坐骑。(但是全部解锁后好像本专精也可以骑其他专精的)先解锁飞行,然后解锁专属坐骑任务!做任务解锁一系坐骑,另外几系的配色史诗专属坐骑。需要1W职业大厅资源和成就购买!猎人流程——这封信是被写在金色的浮空的手稿上的,阅读的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奥丁洪亮的声音荒野之夜要来了。今晚,我们将享受传说中的野兽们的荣耀盛宴。他们将会再一次出现在永恒猎场。我们中的一个人将出发让他们的灵魂再一次安息。我的信使等着你,猎人,如果你会加入我们的话。任务奖励:使用 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召唤或者解散你的狩猎大师忠诚的狼鹰。这是一个飞行坐骑。接到任务返回职业大厅后,奥丁会派瓦格里来接我们。之后将我们传送到英灵殿。酒足饭饱之后,这种传说级的狩猎任务,我们狩猎大师肯定当仁不让的直接上场了。各种各样的猎物出现,有猫头鹰之魂,猎豹之魂,地虫之魂,鹿之魂,鹰之魂,狼之魂。而一个更为稀有和强大从来没出现过的狼鹰之魂也登场了,新世界追猎荒野的存在。击败狼鹰之魂后,它认可的祝福了我们。奥丁很开心见到这么强大的猎物和猎手。返回后我们吹个口哨,狼鹰就飞过来咯。:以上就是本次攻略的全部信息了,更多信息敬请关注玩游戏网!
魔兽世界7.2.5全职业改动汇总
魔兽世界热点攻略推荐
魔兽世界视频攻略推荐
游戏大小: 2.35GB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RPG
游戏语言: 中文
操作系统: winXP,win7,win8,win10
攻略排行周月
屋顶乱斗游戏好不好玩?这款游戏有哪些特色玩法?小编这里带来了玩家…
绝地求生大逃杀怎么扔手雷比较准确?新版本中的投掷武器得到增加,小…
本类一周热点
吉赛尔的研究所是枪剑士的隐秘往事活动中的一个解谜类关卡,需要玩家…
小心不少玩家都被这一天的活动地图难倒了吧?毕竟难度非常之大。不会…
微信扫描关注公众号
Www.Wanyx.Com. Some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号-3
苏网文〔-015号
湘公网安备20乌热尔图:昨日的猎手
收获微信公众号乌热尔图
[摘要]我发现每当猎闲之时,一连数日他要把自己浸泡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趔趄着身子在村头晃来晃去。这时见到你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吗?他一旦喝足了酒,从宿醉中醒来,还能打起精神。西部的猎手 埋在雪中的猎手
他的名字叫西班,姓索勒果诺,在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游猎部落中,算得上最有名的猎手。西班个头儿很高,有两条长腿,人有点瘦。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一双眼睛不大,见了人常常眯缝着,可到了林子里特别的管用。在我的记忆中,他脸上总是带着一副笑模样,特别是在他喝过酒之后,笑就粘在了他的脸上,那神态显得天真,憨厚。在那些性格暴躁、最易冲动的猎手中,他是最没脾气的一位。我同西班结识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一些日子。那一年,我在海拉尔市读初中,因为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又够不上上山下乡的“政审资格”,在走投无路之时,大兴安岭北坡使用驯鹿的鄂温克部落收留了我,给了我这小镇里长大的鄂温克孩子一条谋生之路。这样,大兴安岭,还有森林里静静地流淌的那条被鄂温克猎人命名为敖鲁古雅的小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就使我离童年时嬉戏的那条大河——嫩江,更远了,我把它藏在心底。
一九六九年秋,我跟随狩猎小组来到角道木猎场,那时这个地方没有人烟,野兽很多。西班也参加了这个狩猎小组,那年他不到四十岁,正值中年,而我刚满十七岁,还是个没摸过枪杆的毛孩子。当时,派给我的是些杂活儿,打草呀、喂马呀、跑跑运输什么的,还没有跟随猎手出猎的资格。我记得很清楚,十月一日那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枯干的、霜冻的荒野,藏匿了野兽的痕迹,飘洒的大雪改变了这一切,飞禽和走兽都要在雪地上留下印迹了。这场初雪来得早,河水还没封冻,雪花落在草甸子上、山坡上并未融化,而是软绵绵、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天,西班对我说,他打伤了一头野兽,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撵,这正是我睡梦中都在盼的事情,真使我兴奋,几乎一夜未阖眼,在河边的简易帐篷里翻来覆去盼着天亮。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腰间挎了一把猎刀,空着两手跟随西班出发了。西班竟没骑马,徒步走向空旷的河谷,这使我很吃惊,不敢多问,一声不吭地跟在他身后。走了不远,他撇开小路,迈开大步横穿一片开阔的塔头洼地,在满是塔头的洼地快步如飞。我愣在那儿,瞧一眼脚下穿的胶鞋,咬着牙跟了上去。雪和冰茬在脚下发出脆响,散乱的塔头在雪中露出半截脑袋,踩下去软塌塌的,不小心脚就陷在满是冰茬的水洼里。我跟在西班的身后一路小跑,小跑也跟不上他的脚步,一会儿浑身全湿了,不止一次跌倒在水洼中,雪水和冰凌冻在身上,双腿早已冰得发麻。这更促使我不停步地跑,不然人就要冻僵。西班穿得比我还要单薄,这是为了走路的便利。他并不怕冷。西班只顾朝前赶路,我敢说不管是穿林子还是过塔头甸子,他行走的速度比一匹马还要快,那次我真领教了。当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弄出啪啦啦的响声,他总要瞥我一眼,眼神中只有责怪。钻进林中逢到转弯时,他要砍个树标或折断树枝,为我提示方向。有时看我真的跟不上了,就坐在倒木上等我。那天我们赶了很远的路,才撵上那头受伤的驼鹿,它在桦树林瘸着一条腿狂奔时被西班的猎枪打倒。当年西班机敏的动作、枪手特有的出击姿态,如今早已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我清楚地记得的画面是:整整一个漫长的白天我都跟在他的身后,在湿乎乎的雪地上不停地跑呀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跟在他的身后。 那时,我觉得西班身上具有不同常人的气质,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一时想不清楚。这种感觉并不仅因为西班是敖鲁古雅河畔鄂温克狩猎部落最出色的代表,每年猎取的野兽要多出其他猎手几成之上,也并不仅仅因为他享有“一等猎手”的称号。当然,他称得上我在狩猎这个古老行当中的“启蒙老师”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东西使我终生难忘。西班的一个大嗜好我应该谈到,那就是他对酒类饮品发自内心的喜好。不久,我发现每当猎闲之时,一连数日他要把自己浸泡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趔趄着身子在村头晃来晃去。这时见到你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吗?他一旦喝足了酒,从宿醉中醒来,还能打起精神,扛起枪默默地进山,进了山他又成为硬邦邦的猎手了。西班的性格也从他交朋友的本事上显示出来。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几乎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的朋友,这些人大都是林场的管理人员、工人,还有汽车司机。他有个习惯,每次出猎归来之后,都要在身上藏几条鹿鞭或者鹿心血之类的珍贵猎产品,然后骑马去找那些新结识的朋友。这时,只有等到深夜,等到从远处传来马蹄声,伴着不连贯的小曲,我就猜出是他回来了,腰里一定插着换回来的两瓶白酒。这样谈论西班,并不是说他的智力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他不懂得货币的价值。他懂,可他还是保持自己的做事习惯。记得有一次,他穿一身崭新的犴皮鞣制的漂亮猎装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换了一身开花的黑茬棉袄。真没办法,他还咧嘴笑呢。西班出事的时候是一九七九年,那一段时间我正巧外出,回来之后听说了事情的大致过程。那年的四月,西班的妻子健莎找到村里的乡政府,说西班上山之后在狩猎点失踪了。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没有一个不晃脑袋,谁要说猎手西班在林子里迷路、出事,那真是开天大的玩笑。这样,健莎的话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也没有谁在意。等健莎喝了一点酒,抹着眼泪到乡政府吵闹的时候,有些人开始烦了。十几天过去后,山上的狩猎点传回信息说,西班出猎那天没带干粮,他说当天要赶回来,可至今没见他的影儿。这时事情才得到重视,乡政府组织人力山上山下地寻找西班,可哪一条河边,哪一片林子也没找到他的影儿。几天之后,人们疲倦了,失望了,认定西班出事了,猜想他被什么人劫持了,为此还通知了远处的边防部队。那时,人们喜欢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想问题。另一种猜测,当然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倒在什么地方了。 西班失踪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他的妻子听到什么响动推开门,发现西班浑身血乎乎地趴在门口,已经气息奄奄。村里的人又惊又喜,如同看见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西班变得很吓人,瘦得脱了相,简直成了皮包骨,他的手臂、大腿已经磨光了肉,露出了白骨,胸部和腹部也少了很多东西。村里的医生闻讯赶来。西班神志还算清醒,喝过几口水之后,断断续续道出事情的原委。原来,他在山上的狩猎点出猎后,突然之间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眼前晃动着人的影子,张牙舞爪朝他逼来,嚷着要抓他,喊着要杀他。这把他吓坏了,没命地在林子里跑起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被雪埋了半截,他看见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满是狼的印迹,两条狼已经围着他转了好些圈,也许是他的气息不绝,使那两条饿狼犹豫不决。西班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很快辨认出了自己所在的方位,可他站立不起来了,两条腿冻得僵直,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他尝试着往回爬,一点一点地朝前挪动。这样,他爬了一天又一天,饿极了就从雪地里扒出枯干的蘑菇吃,找不到蘑菇,找残留的浆果、草根,还有松鼠吃剩的松树籽。好在那时冰冻的河流还未解冻,不然渡河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爬过好几座山岭,一道道山谷,等他爬上高高的运材公路,已经熬去了十几天。一个运材的司机在公路边发现了他,让他捎了脚。那司机见他膝盖和前胸都蹭开了花,人也不成样子,想不明白他到底摊了什么事,但还是把他送到通往村子的岔路口,交待说,他的车身太长,拉着十几米长的原条,汽车转弯掉头不方便,嘱咐他等着村里的人来,到了家门口不要急。从那岔路口到村子里只有一千多米的沙石路,西班实在等不及了,朝村里爬去。这一段沙石路可不得了,他爬了整整一夜。西班的身体出现败血症的症状之前,他还对那些看望他的村里人笑,过了一天之后,他再也笑不出来了。从西班失踪,到他从很远的林子里爬回村子,整整过去了十九天。十九天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算不了什么,但我觉得这十九天真是个了不得的大数。西班的死使我感到震惊。按照医生的说法,他在山上突然失去自我控制的原因,是深度酒精中毒后出现了幻觉和幻听。我相信医生的推断,但还是有想不通的地方,要说西班欠了谁的什么,我说他欠了那些倒在他枪口下野兽们的一笔还不清的债,别的他什么也没有。当他失去自我控制,脑袋里出了毛病的时候,最怕的该是一群一群的野兽来向他讨命呀!可他怕的不是野兽,而是人,是一些使他连模样也辨认不清的人,人的喊叫声竟让他吓破了胆儿,而且是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林子里。他一直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猎手。这到底是幻觉和幻听的缘故,还是他脑袋里塞了什么让人猜不透的东西?这不是一件让人费寻思的事吗?西班的死使我想明白了一点:西班身上不同常人的品性,应该说是一种极富忍耐性的求生意志。可我久久地感到迷惑,那样坚韧不拔的求生意志,为什么会同摆脱不掉的自我麻痹、一种慢性自杀的倾向糅合在一起?想起西班的死,使我多次联想到那篇有名的小说《热爱生命》,还想到后来读到的马尔克斯描写一名遇难的海员在海上漂流十天的故事,那本书叫《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我至今觉得欠西班一些什么。一颗被刺伤的心
从照片上看得出来他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这与我记忆中的印象一致。我跟他结识是在马嘎拉格的撮罗子里,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冬天,是我学习冬猎的头一个年头。那年我十八岁,而阿力克协依四十岁出头。在我的眼里阿力克协依是个壮汉,尤其他黝黑脸盘上凸起的颧骨,绷紧了脸上的表情,给人硬邦邦的感觉,加上他闷头不语的秉性,整个人显得深不可测,使我一见到他就怀有隐隐的畏惧。阿力克协依姓“索罗共”,索罗共简称“索”,这是顺应了汉族的称呼习惯,说起来也挺顺口。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中索罗共是大姓氏、大家族,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游猎区域,有自己的“乌力楞”,分成若干户,搭建若干顶撮罗子。阿力克协依兄妹四人,长兄老马嘎拉在猎民中很有影响,二哥杰士克见多识广,他的姐姐早在四九年前远嫁黑河,排行中他是最小的。阿力克协依的妻子病逝多年,他在陪妻子治病期间学了一些汉语,他有个女儿,名叫嘎吉,那年十一岁,留在了山下的亲戚家中。我和阿力克协依之所以凑到一起,因为到了山上都是没有着落的单身汉,只能借宿在别人的撮罗子里。当时负责猎业生产的何林把我安排在马嘎拉格家,是他的精心挑选,而阿力克协依落脚在这顶撮罗子有自己的考虑。马嘎拉格一家三口,他妻子已经不在,他同儿子舒日克,还有一生未嫁的姐姐大巴拉杰依相依为命。马嘎拉格姓“卡尔他苦鲁”,简称姓“葛”,他个头不高,人老实得出奇,被人认为是末流猎手,按照当时的称呼是“贫苦猎民”。他很少喝酒,从不打架,也不招惹是非,是各方面都靠得住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马嘎拉格的姐姐从未嫁人,她五十多岁,面容瘦削,眼睛显得挺大,一副劳累了大半生的慈祥模样。在我记忆中,不管多冷的天她都要在冬服之外套上长裙,奔来奔去的,只有在营地搬迁时,她才披上亲手缝制的鹿皮袍子,配上皮手套,犴腿靴,把自己裹在耐风寒的皮制品里,然后拄着一根细棍跨上驯鹿。对了,她围头巾的习惯与额尔古纳河边的俄罗斯女人相似。大巴拉杰依整日在撮罗子内外忙碌,真像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住在马嘎拉格撮罗子的那个冬天,我受到他们一家的特别关照,其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需要回忆,这些我要在下篇文章里描述。此刻,我的心思放在阿力克协依身上。阿力克协依不善言语,甚至对一个初闯山林、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也不肯给几句忠告。他对我怀有几分陌生,有理由不理睬我。在我看来,他习惯于保持猎手的尊严,不愿同我这疏远了山林的毛孩子靠得太近,或者说他这个人,善于以默默不语的行动来影响你。阿力克协依几乎天天出猎,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时才回来。因为住在一起,我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管束自己,同样的晚睡早起,以保持同一节奏。天刚蒙蒙亮,他前脚走出撮罗子,我后脚跨出门坎,两人行走的路线各不相同,这在出发之前就说妥的。我俩见面的机会,或者说近距离对视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只有在撮罗子里的火堆旁。但是这时,他也是闷头整理了一天雪地的犴腿靴,查看可能出现的微小缝隙,如果皮靴被雪水濡湿,他要细心地翻开,不停地揉搓,然后挂在撮罗子的支架上。接下来他要取出猎刀磨一磨,猎手们都喜欢自己的猎刀时刻保持锋利。他每天都要磨的还有一把小斧,这是他必备的工具。磨刀的过程中,他慢声细语地把一天中遇到的野兽印迹,例如一头犴从沟膛子里走过去了,脚印是旧的;一头野鹿从山顶上走过去了,脚印是两天以前的;还有驯鹿群在那条山沟里觅食呢,狼撵没撵散它们呀;今天找到了几只松鼠,打伤了几只,几只带着伤钻了树洞,他不忍心放倒那棵大树呀,等等等等,都要念叨一遍。这时,马嘎拉格、大巴拉杰依在一旁干自己的活儿,但耳朵却细心地听着出猎人的诉说,不时嗯嗯地应答着。饭前饭后的闲余时间,猎手之间就以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交换猎场上的最新情报。但对我来说,阿力克协依仍是一扇紧闭着的门,尽管我充满好奇却没有机会凑到跟前朝里面张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敞开了心灵。那天,山下有人来到猎点,带来些生活用品,其中自然少不了白酒,酒使静悄悄的猎点热闹起来,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狂欢。那天晚上,阿力克协依喝多了酒,有了醉态,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不停地诉说,充满感情、满怀忧伤的人。两者之间转换得这么突然,令我吃惊。阿力克协依自言自语,像打开了一道闸门,从那闸口中倾泻的是一些琐碎的往事,他谈起死去的妻子,不停地念叨她的名字,说她在鄂温克女人中是知道怎么疼爱丈夫的,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反复告诉我她葬在了什么地方。打动我的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唱了一首歌,并反复哼唱这首歌的旋律①。我猜出这是他妻子生前喜欢唱的,或者是喜欢听他唱的一首歌。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沉默不语的人,一下子变得如此深情,如此热烈,这样痛不欲生,真把我感动了。在那窄小的撮罗子里,不知不觉我也沉浸在忧伤的情感中,两眼含着泪。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为动人,使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不知是阿力克协依过于忧伤,还是过量的酒精刺激了他的心脏,到了后半夜他捂着胸口呻吟起来,脸色变得难看,淌着汗珠,整个身子蜷成一团,显出极度痛苦的样子。这可把我给吓着了,我猜出他有心脏病,眼下急性发作。在深山密林里不仅没有医生,也没有救急的药物,我感到他的生命有危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呆愣在那里。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eki eki”“enin enin”②。大巴拉杰依奔上前去,将他的头搂在怀中,轻声细语地抚慰着他,摸着他的脑袋,揉着他的胸。阿力克协依接受了这位老大姐的抚慰,口中仍“eki”“enin”地呼唤着。阿力克协依的身子倚在瘦小的女人怀中,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平静下来。此时,撮罗子外面是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寒气穿透薄薄的苫布,直刺你的脊背,撮罗子内却笼罩在桔红色的火光中,生发着无穷的暖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语言难以复述。渐渐地,阿力克协依的心绞痛得到缓解,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似乎对自己的软弱表现很不满意,对关心他的人也没有什么表示,一句话也没说,倒头便睡。第二天,阿力克协依没有出猎,继续蒙头大睡。后来,谁也没再扯起那天晚上的话题,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年冬猎之后,我很少见到阿力克协依了,他在山上狩猎,我在山下干杂活,虽然没有了同住一顶撮罗子的机会,还是能听到他打着这种野兽,或是那种野兽的消息。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还不时为他的病情担心,不知他的心绞痛是否再次发作,很想劝他去医院看看。过不多久,阿力克协依出事了,不是因为他的心脏。他出事时偏巧我不在村子,回村后得知后事已料理完,我未能最后见他一面。阿力克协依自杀身亡,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地点在比德莱打草点。事情的突如其来令我震惊,村里的人也都感到意外,好些人为他的死而惋惜。从各方面看,阿力克协依生活平静,又是狩猎的能手,没有酗大酒的恶习,也没遭遇什么使他抬不起头的意外打击。他没有理由毁掉自己的生命,在他近一时期的言行中人们也没发现这样的动向。但他还是死了,死得干脆、利落。徐世勋是下乡青年,当上了猎业队会计,当时他和一些人在离敖鲁古雅二十多里的比德莱草场打草,他是见阿力克协依最后一面的人。他说,在比德莱草场打草的有十来个人,其中有阿力克协依的哥哥老马嘎拉,另外还有几位猎民。出事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酒后兄弟俩发生了口角,老马嘎拉当众骂了阿力克协依,骂他好吃懒做,说他什么东西也打不着,并把酒杯摔在他脸上。当时老马嘎拉的举动人们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因为阿力克协依刚刚为草点打了一头大犴。阿力克协依无法忍受劈头盖脸的辱骂,憋着一肚子怨气,扯出自己的猎枪,执意要回村子。当时天色已黑,大家怕他在气头上干出什么事来,左拦右拦又拦不住他,只好把他的子弹带抢了下来,同时取出压在弹仓里的子弹,让他上路了。他走后不久,人们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声。老马嘎拉坐不住了,摸着黑顺小路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又顺着小路察看,似乎意识到不幸之事将要降临,这次被他找到了——阿力克协依倒在草垛旁。①这是鄂温克情歌“阿拉巴吉坎”。歌词大意:在阿拉巴吉小河边,我把戒指弄丢了,那是我心上人送给我的。②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语方言中姐姐、婶统称为“eki”;“enin”为母亲的称谓。对于阿力克协依的死,玛妮有自己的看法。她与阿力克协依有亲属关系,离开敖鲁古雅时间并不长,刚调到外地工作,见过世面。她认为阿力克协依的死从表面上看,是因兄弟之间发生口角引起的,其实另有背景。她认为这与一年前阿力克协依当向导有关系。这对我是个提示,阿力克协依死之前的一年左右时间,确实当了一次向导,那次当向导与他以往给铁路勘测队、森林调查队、扑火队当向导不同,他是为旗公安局的人当的向导。那是一次突击行动,任务是找到鄂温克人在森林里搭建的“kuaolaobao”(仓库)。那些仓库搭建的时间久远,属于游猎时期鄂温克人的私人设施,归属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乌力楞”。虽然这些旧仓库早被主人遗弃,但也存放着猎人的旧物,他们的一些私密物品。那些旧仓库分散在不同的河系,不同的山谷,外族人很难发现。阿力克协依真心实意地配合了这次官方行动,走遍了激流河、阿巴河、乌玛河,乃至长长的额尔古纳河,不但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旧仓库,也把他们领到了其他家族的仓库。结果二十多座旧仓库统统被毁。事后,阿力克协依意识到这是一次并未求得鄂温克人应允的行动,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些旧仓库,也包括鄂温克内部对他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一件无法辩解、难以洗刷的亏心事。玛妮认为,在比德莱草场的那个夜晚,具有权威感的老马嘎拉一定在辱骂中提及此事。于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那个漆黑的夜晚,阿力克协依用猎枪瞄准了自己,枪口不是对准胸膛,而是支在他的下巴,就在那一瞬间,弹仓里仅有的一发子弹扣响了。阿力克协依用猎枪打烂了自己的脑袋,这是极为特殊的死法。可怜的阿力克协依,诚挚的阿力克协依,沉默不语的阿力克协依。哈协之死 哈协长得挺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那大脸盘、满脸连腮胡子的马克辛姆。哈协兄妹五人,他是长子。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哈协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东西很多,他有父亲那般宽大的骨架、厚实的胸脯、结实有力的长腿,还有一副略微有些沙哑的大嗓门。哈协步态轻松犹如猞猁,举手投足充满了活力,挺像一头野鹿。细说起来,他那双细长的眼睛也有意思,当他哏哏地欢笑时,高高的颧骨和突起的眉骨相互聚拢,两眼挤成一条窄缝,脸部的神态显得又憨又拙。哈协憨笑的模样很可爱,只要你感受一次就会留下记忆。哈协与他父亲最大的不同,就是未能把他那憨拙的笑容保持多久,在他刚刚步入中年时,不经意地毁掉了那张可爱的笑脸,很多人为此痛惜。我认识哈协时,他正在敖鲁古雅的小学读书,他个头儿高,不同于一般的学生,教师们对他比较器重,一些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要由他去做,他也拿出读好初中,当个正式毕业生的架式。但是,山上的生活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在校期间他常撂下课本跑到山上,去喝刚挤出的驯鹿奶,吃新鲜的野鹿肉,在猎营地里跑前跑后,忙乎着圈赶驯鹿群。不久,学校的操场上见不到他的影儿了,他跑到山上当了猎民。他具有第一流猎手的素质,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哈协在山上转悠了几年,山上山下传开了他的“猎绩”,说他多么多么地能干,简直称得上“一等猎手”了,有人甚至说他打猎的本事超过了马克辛姆——他那体魄强健的父亲。可想而知,那些言传露出赞扬年青后生的情感,不过哈协确实有了业绩,争得了好猎手的名声。有关他狩猎传奇的精彩一幕,是他自己讲给我听的。当时,他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扯起了话头也是三言两语,像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我这旁听者却觉得不得了,感到惊心动魄,久久不忘。那是他无数次狩猎中的一个片断,那次他追猎一头野鹿。那一年的雪很大,人在林子里走不了多远,四条腿的野兽也同样费力。哈协的帮手是两条狗,这两条猎狗已经被他训练出来,远近也算有了名气。可惜猎狗的名字我忘记了。他身上的装备是一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把猎刀。或许他的背夹子上放了一点干粮、一点盐,大概就这些了。他在林子里发现的是一头大犄角的公鹿,肢体强健,没有一点外伤。我估计最初哈协有点毛手毛脚,惊跑了那头鹿。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贴近了那头鹿,放了空枪。反正有个缘由,他因此而气恼、懊丧、自责,所以鼓足勇气一定要撵上那头鹿。他撒开猎狗,让它俩由着性子去撵,自己码着野鹿的蹄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猎狗准是撵上了那头鹿又惊跑了它,这样反反复复在林子里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哈协跟踪一个整天,表现出与那头鹿对等的耐力,到了晚上,他在树根下生了一堆火,倒在雪堆旁睡了一觉。两条猎狗在山顶上圈着那头鹿,一夜未归。第二天,他又撵了一整天,如此的耐力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太阳快落山时,他再次靠近那头鹿,这一时刻人与鹿的体能对比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他端起枪,欲勾扳机时,发现鹿的身子晃动,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他纳闷:没等他开枪,那头鹿栽倒了。两天不停歇的追撵,加上大雪又比往年厚得多,那头野鹿没有反刍和歇蹄的机会,给活活地累死了。如今谈起这件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真为那头被活生生折磨死的野鹿而难过。当年我可没有这种心态,记得当时,我瞧着哈协黑乎乎带着冻伤的脸蛋,瞧着他裹在皮套裤里硬邦邦的腿,心里还真钦佩他的能耐。 后来,哈协娶了谢力结依的女儿宁克,小两口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不久,我听说,他同宁克离婚了,与守寡多年的达玛热组建新家。达玛热的前夫金芳是我的好朋友,他出猎时死于意外事故,给达玛热扔下了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达玛热确实很能干,多年来独自支撑残缺的家。至于哈协的婚变,涉及个人隐私和微妙的情感,身为旁观者我不便打听,也不妄加猜测。哈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他的儿子小龙的出生就是最好的证明。值得琢磨的还是哈协的结局。那是阴郁、忧伤、令人猜测不已的突发事件。那一事件本可以拖出长长的文字,渲染成完整的故事,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它是哈协留给我的唯一纪念,这一纪念是以独特的死亡来诀别。哈协的死为他短暂的生命划上句号,同时作为令人深思的事件,变成一道生存难题遗赠于我,多年来我常常想起它,脑袋里翻动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就此,我试图找到答案,但一直没有成功。我从未有过将其编写成小说的念头,更不敢轻率地对待它。在这里,我只能以平实的语言述说事件的过程。哈协在三十七岁那年出的事儿。那一天,哈协领了四条最喜爱的猎狗,背上猎枪,拎着砍刀出发了。这一次他不是出猎,是为营地搬迁去砍除路障。他出发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那是个宁静的清晨,或者说一切都罩在平静之中。哈协的神情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他肯定同家人打过招呼,说过傍晚回来一类的话,他一定哼着那首他最喜欢的“阿拉巴吉坎”上路的。有人说,他同家人闹翻了,赌气上路的。至于为什么,很少有人讲得清楚。也有人说,夜里听见他自言自语,在同死去的人对话,显然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晚,不见他的影儿,达玛热并未在意,她猜想哈协在路上发现了野兽,或许打伤了它,撵得远了,就在河边架起了火堆。因为,有人听到从哈协走的方向传来了枪声。另一种猜测是,哈协干完了活儿,顺便到附近采伐的小工队喝酒去了。不管怎么说,哈协一去不归。一天过去了,不见他的影儿;三天过去了,不见他的动静;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消息。这下家里人急了,觉得出事了,四下派人去找,还是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无奈之中,猎营点的人们请来了老萨满牛拉,牛拉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神智开始恍惚,但她还是穿戴上沉重的萨满神袍,敲响了神鼓,庄重地请了神。送神之后,牛拉留下了话,她说哈协就在附近,倒在一棵树下。问题是林子里的大树仍然很多,谁也猜不出哈协倒在哪棵大树下,人们按照老萨满手指的方向去寻找,也是无获而归。哈协失踪的第二十二天,卜伶俐下乡来到猎营点。他在敖鲁古雅乡派出所当过所长,刚刚调到盟民族事务局工作,同哈协有很深的友情。他认真听了哈协出走当天的情景,有了自己的判断,立刻领了猎营点的几个年轻人出发了。几年前,卜伶俐曾因车祸伤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特别是走在山路上更显出吃力。但他显得很有信心,直觉提示他:只有他才能找到哈协。林子很密,几乎没有路,过小河时年轻人抬着卜伶俐朝前走,走了四五里地,找了一片又一片林子,大家都感到累了乏了,失去了信心,准备往回走。这时,听到卜伶俐在林子里喊,原来他发现了树上的弹痕,顺着弹痕显示的射击方向朝前找去。他先是在沼泽地发现一条猎狗,隔了不远发现另一条,随后找到了第三条,三条猎狗都是奔跑时被枪弹击中的。随后,他在沼泽地看见了哈协的猎枪,它孤零零地戳在泥水中,枪口斜歪着指向天空,离猎枪八九步的地方,哈协嘴啃地倒在泥水中。他高声喊人,随后凑上前去,看见泥水淹没了哈协的下半身,泥水中只露出他的一块脊背,脊背上炸开一个黑洞,满是血渍,上面落满了苍蝇。卜伶俐发现子弹是从哈协下腹射入,穿过了胸部,从他的肩胛骨透出的。卜伶俐根据现场判断,哈协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猎犬,然后有意或无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很明显,他最后的动作是在激愤的情绪下,在跑动中进行的,因此存在着枪支走火的可能性。后来,警方的现场勘查证实了卜伶俐的推断。哈协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人世。事情过去了很久,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一情景,无论我从哪种角度看,那幅图面都在表达绝望的情绪:一个出类拔萃的鄂温克猎手,在他刚刚步入人生的鼎盛时期时,顷刻间枪杀了心爱的猎犬,然后让子弹穿透自己的胸膛,倒在他最倾心的猎场。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采取如此惨烈的行动?他疯了?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酒精中毒了?还是他对生活彻底绝望了?关心他的人如此这般地提出问题,答案似乎就放在那里,但并没有人将它攥在手中。一个事件的背后往往勾连着复杂的因素,而构成哈协的死因究竟哪几种因素为主导,无人理得清楚,说得明白。有人说是因为家庭纠葛,说他比他的妻子小得多,又比他的两个续子大不了多少,家庭冲突在所难免;也有人说,哈协喝大酒了,脑袋喝出了毛病;还有人说,他的家人一直在责怪他,说他什么东西也打不到了……哈协自戕的缘由似乎很多,在我看来哪一种都不能成立,不能视为决定性的,哈协完全有理由活下来。最终,还是玛妮的分析使我在意,她既熟悉哈协的为人,又大体了解哈协的情感状态,她认为哈协前妻宁克的意外死亡,对哈协的精神是个打击。宁克是一九八九年同她的父亲谢力结依、母亲大格拉冻死在前往猎营点的途中的,那是那年四月发生的事情,事发后哈协赶到现场,亲眼目睹了那一惨状,旁观者无从想象究竟是内疚,还是自责的情绪刺伤了他的心。玛妮从一首歌中破解了哈协的心绪,那是玛妮录下的哈协最后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连大兴安岭也变得陌生;真想撇下驯鹿群远走高飞;最怕的是驯鹿群迷失消散;回头来拣到的只有系过的鹿铃……玛妮认为,对生活的失望,包括对驯鹿命运的担忧,从哈协这首即兴哼唱的民歌中流露出来。我了解到,哈协一家不足二百头的驯鹿,仅一九九三年就被偷猎人下套弄死了四十多头。后来,我还得到消息,他们的驯鹿不时被林场工人撒的灭鼠药毒死。哈协就这样死了,在敖鲁古雅使用驯鹿的鄂温克猎民中,他成为第一个枪杀心爱的猎犬,然后饮弹自尽的猎手。从哈协那次长距离追逐野鹿,到他后来龟缩在一块不大的林地,丧失游猎与游牧的愿望和冲动,前后仅间隔十年时光。从哈协枪口下逃脱的那条猎犬,回到猎营点后一直拒绝进食,它的最后着落也不得而知。转自“收获”微信公众号(harvest1947),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sophiawang]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陕西有西安最灵验的道观观,算准的道士吗?
- ·出家人还俗有什么后果到了广东省之后是不是自动还俗?
- ·的学西餐到哪个西餐学校好培训学校?
- ·王李红星个人资料星路历程
- ·龙腾数据公司万网域名注册优势
- ·请问重庆彩 五星定位胆五星60攻略是怎么算的??
- ·求LOL每日撸报5.27: 猴哥猴王被猴耍时,猴哥石头人开大那个bgm!!
- ·多ip玩游戏戏ip被人监控
- ·英雄联盟帧数过低以前没事最近帧数变的很低
- ·为啥我玩快吧的gta4gta4低配置画面补丁显示达到了可进入游戏刚开始加载流畅开始玩的时候刚开始一卡一卡之后直接卡死
-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键盘手游用哪个牌子的键盘玩比较好,要方便一点的?
- ·火影忍者肉片在线观看片
- ·大家最近用的游戏电脑机型怎么看是什么机型?希望能给点建议。
- ·谁有 DNF ExtractorSharp 1.7以上的86版本女鬼抢谁厉害
- ·台服天堂永恒台服2如何改按键12345
- ·谁谁能教我最新杀一队垃圾能杀85剧情吗复试方法??
- ·一个女猎人骑狼沈海高速客车坠崖事故,落地后狼压在猎人身上,猜猜狼和猎人分别会怎样?
- ·跆拳道黑带八段有几个女生可以打几个男生
- ·一个女猎人骑狼汽车坠崖会死亡吗,落地她坐在狼身上,猜猜狼和猎人分别会怎样?
- ·一个女猎人骑着狼四川客车坠崖51人遇难,落地后她坐在狼身上,猜猜狼和猎人分别会怎样?
- ·创造与魔法坐骑大全怎么禁止别人加入
- ·手游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场手游可以用键盘玩吗?
- ·问比利时与中国关系单关还是串?
-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神器手游的那个吃鸡神器是什么?
- ·请教一下后一技巧除32技巧技巧哪些可以学习??
- ·游戏嗨氏主机游戏大家留意过多少?评价一下。
-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呐,我想去看看,世界在哪里?
- ·新手求助,关于温控器路灯定时器说明书和各种灯
- ·做全车隔音选择佛山百佳改音响 不隔音好吗?
- ·联想电脑,卡住了联想平板电脑开不了机机
- ·华为手表esim卡esim卡怎么激活
- ·小米8小米mix2s屏幕指纹纹的是探索版的吗
- ·vivo xplay6vivoxplay6音质怎么样?
- ·求助.我新买的索尼wh h900n评测耳机,玩游
- ·小米8se小米手机什么时候发货可以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