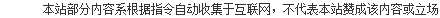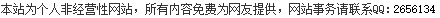廊坊市里什么地方华强北哪里有卖焊台台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9-15 16:43
时间:2018-09-15 16:43
-
“华强北联想电脑维修服务中心”详细信息
|
地址:深圳华强北都会100大厦B座16楼R室 |
(原标题:华强北变奏丨杀死这座山寨王国的,是苹果和阿里巴巴)
2017年,华强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挡板,人们从街口踏进来,都无法绕过“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牌。只是坊间仍旧习惯以“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相称,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以假乱真的手机,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约十年过去了,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下午三时,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像是没有在等谁,谁也不会来。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
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
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2017年6月,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午后开始。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当,当,当,当,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在仓库、商场、停车场、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行人车辆堵成一团。1998年,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时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
改革开放初,曾裕“以为特区钱好赚”而来到深圳,第一次来华强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几间厂房仓库,一地黄土,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
在那一地黄土上,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深圳获批特区后,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在2008年,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称霸全国”的电子大军,山寨机花样百出,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莆田系”。
据工信部数据,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2016年全年来,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高达),他做工厂供货,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也看不到未来,“没个底,不知道是好是坏”。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
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朋友告诉他:“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要来深圳熬日子,是挺难熬的。”
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1999年: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
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他向澎湃新闻()形容2000年初时,“可以这么说,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
1999年,诺基亚未死,塞班系统正红,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后来人们以“不死传说”相称。
那一年,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只有十几岁年纪,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
1999年,国产手机约70万部,全球手机销量):“我就住在’大有可能’那四个字后面。”
华强北步行街上的曼哈数码广场,张宇说他来到华强北的第一夜,就住在“大有可能”四个字后面。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5月25日,三星S8在中国上市,5月20日,已经有华强北人在朋友圈晒现货。
在华强北有多大可能改变命运?许多张宇这样的年轻人来找答案。张宇向一位前辈打听经验:“我也是做过富士康,准备去华强北,能不能加个微信。”
收信人已经在华强北做学徒,在翻新手机批发市场学习刷机、修理二手的手机芯片、让一部50元回收的iPhone再次正常开机。每天都有人问他进入华强北的攻略,他没空一一回复,只是偶尔抒怀:“自己从出社会就在富士康,一待几年,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离开不了苹果手机,那是一种对苹果与乔布斯的信仰,就像宗教一样。”
尽管没有回复,22岁的张宇还是来了,攒足了钱来华强北拜师。他带着在工地上开货车、在餐厅做服务员的积蓄,来向华强北师父支付数千元、上万元的学费。他又走的孤注一掷,辞去烤鱼店服务员的工作时,他对经理说,“我大一辍学出来,已经在拿青春赌明天,我不能再拿青春赌老板的良心。”
华强北是中国电子第一街,坊间相传的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中国手机维修民间大军的黄埔军校。张宇想成为这支野生大军中的一员,成为手机维修招聘优先录取的“深圳师傅”。
华强北向南不远,香港新界在深圳湾对岸一水之隔,港币价格涨一百,华强北涨价50元。富士康则须一路向北到龙岗,传说如果华强北不给面子,那么在苹果新品发布会之前,新一代iPhone就会首先现身华强北的档口(商铺)。
除了“冠绝全国”的手机技术,随着华强北大军铺向全国的,还有一张手机销售网,行货、水货、翻新机、华强北组装机,应有尽有,无所不至。众多年轻人从全国南北涌向这里,宿在出租房的上下铺中,前来突破手机芯片的终极技术。有人在档口潜心吃苦,学成分赴西东,再将华强北的货源铺向全国。
2017年6月,华强北封街改造近四年,重开四个月。张宇22岁,曼哈数码广场也22岁。他的华强北拜师之行,从曼哈70块一晚,没有空调的铺位开始。
太热了,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不能从头再忍,在几站开外的招待所找到50元一晚有空调的铺位,“70块钱不要了”。
行业衰退,师父在淘金路上卖铲子
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在2017年重新开放,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志立在街口。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张宇支付了一个月五千元的学费,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个华强北师父。
师父已经有些金盆洗手的意思,租下一套公寓作为培训班,雇了几个师傅教徒。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指点手机的疑难杂症,快件收上门整饬一新,再变作靓机发回原处。
“眼看着自己所在行业日渐衰退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在知乎上被浏览了):“那个时候,你说你在华强北做电子,很有面子,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赚钱的地方。现在你说在华强北,人家会问,你还好吧?这样关心你。”
张宇在曼哈这些空荡荡的档口里找不到师父,他在58同城上搜索培训班广告。
58同城上的培训广告承诺将修手机绝技倾囊相授,收取每月数千元的学费。并且“对于临毕业学员,公司会赠送一套60G的维修绝技视频给每一位学员带走,包括本公司以及档口所有手工技术和分析能力,以便学员巩固与复习。”
张宇在培训班里翻来覆去焊一块旧芯片,索然无味,对不起广告上“材料管够”的许诺和一月五千的学费。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他开始惶惶不安,师父不是耳提面命的高中老师,他可能学满三个月,却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工作与学费两空地离开。
张宇渐渐感到行业萧条,“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淘金的故事?”当一群人听说一个地方有金矿,大批涌来淘金,最早淘到黄金的人,却转而在淘金的路上卖起了铲子发财。一个学徒一个月五千元,也是一份不逊于做生意的收入。
张宇担心自己想法太负面,但又忍不住质疑:“师父就好像在淘金路上卖给我们铲子一样。”可是自己还能挖到金子吗?他终于和师父商量,能不能退回部分学费,让他另投他处。
师父几乎与他闹翻,最终退还了一些学费,只是叮嘱他,不要告诉其他学徒。
翻新手机批发市场中的师父
张宇发现,学技术,还要去档口做学徒。午后太阳从头顶暴晒下来。张宇向南穿过深中南路,去华强南,那里有最大的翻新手机、山寨手机市场。
张宇读高中时候,诺基亚正红,他想买一款正价三千余元的诺基亚N98,但网购只要一千余元,货源标注深圳福田华强北赛格。
那时他翻到评论,人们说:“赛格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看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张宇看不懂,一个问题从此刻在脑海中,“到底华强北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
诺基亚N98于2010年发布,7年过去,华强北一轮一轮打假,封路改造后,用商场和创业空间替代了山寨机卖场。
但华强南还能看到昔日的赛格。
在与华强北隔街相望的几栋居民楼上,挂着通天地通讯城的牌子,以所在居民楼为名,分割为飞扬、长城、爱华三座,一至四层打通成一片卖场。其中名声最响的,是批发二手苹果手机的飞扬大楼。
张宇说,我一定要在飞扬找个师父。
下午两三点开始,华强南的通天地通讯城中,像买卖白菜一样,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他穿过门口坐成一排倒卖手机的背包客,下午两三点开始,飞扬里像买卖白菜一样,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每个柜台长不过一米多,各自架着一两个大保险箱,顾客从上面架着的监视器屏幕上,可以仔细找到自己的脸。点钞机也架在保险柜上,在微信和支付宝流行之后,背包客越来越少掏出厚厚一沓红色现钞,换几捆手机塞进包里。
在鼎沸的人声中,老板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个个报价,背包客开始拼尽自己所有眼力鉴别翻新机的成色,手反复摩挲,打开镜头拍几张照片测试,以防挑中炸弹机,打雁反被啄了眼睛。
通天地通讯城仿佛真的本领通天:解锁指纹,iPhone 6改装成iPhone 7,芯片屏幕配件装配成新机出售。各种来路的手机流向全国的微信朋友圈,就变成了“iPhone 6s Plus, 成色没有磕碰,完全可以当靓机,2350。”
在出口的天桥一端,撩开塑料帘子,有二十多个人坐在十几阶台阶上抽烟,吞云吐雾,把所有人笼在云雾中,显得格外安静。
在华强北鼎盛的手机时代,这种场景在华强北路两侧的商城里司空见惯,如今却退缩到华强南这一片居民楼中。但这里的人气,却远超过华强北路边的任何一家商场。
张宇已经会熟门熟路问手机价格,“手机贵的就是主板和屏幕,加上一些配件成本不到两千,可以加个几百,在网上再卖出去。”
货源渠道也是华强北手机江湖中的重要一环,就连学徒培训班的广告都会注明,“培训期间也会讲解和提供华强北周边市场,如飞扬,龙胜,通天地等大型手机主机及配件批发渠道,并可提供一整套货源、渠道、设备的解决方案与经验指导。”
通天地通讯城前,坐着一排前来批发翻新手机的“背包客”。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奋力挤过一捆一捆买手机的人群,张宇走到楼层边角的修理铺,铺子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工作台,挂着风枪、焊台,学徒两边分坐。张宇理想的华强北未来,要从这里起步。
张宇走到台前,问招不招学徒。
一个师傅说了句六千,老板递过去一个颜色,让师傅“去楼下档口看一下。”
“八千三个月”,隔着档口的高台,老板站起了身。
张宇拿了一张名片,打算再看看。
张宇习惯在午后一两点醒来,如同他在流水线上的夜班日子。那时他夜班回来,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光西斜,发现自己突然不喜欢这个世界了,“真的会想跳楼。”
他并没有真在富士康做过,而是在戴尔的代工工厂,张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 “件不停,人不能停。”一个人快,所有人的都跟着加速,一个人慢了下来,监工就会过来骂人。做的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受自己控制,站成一座机械臂兵马俑。
张宇夜夜难以入睡,上下铺的舍友们都在煎熬自己的人生。有人找了十几天,有人找了3个月,直到一无所获地离开华强北。十八岁的舍友送外卖出了车祸,第二天继续送餐却碰上电梯故障,爬上了23楼,回来终于一甩手,不干了。
另一个舍友帮他重装了手机,“是朋友才刷机不收你钱,外面至少50块。”
张宇明白这是手机行业的暴利所在,刷机不过是启动一下软件的功夫,一秒钟50块钱的收益,如果这不是暴利,那么什么叫暴利。
傍晚坐在华强北街口的人们。张宇觉得,他们看起来都很迷茫。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张宇辞掉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来华强北时,经理想留他,“我也是从服务员,一步一步做到经理。”
张宇想起来自己22岁,是服务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想到十几岁的童工同事,在结账高峰期永远吃不上饭终于饿出胃病的前台小妹,永远不交的五险一金,和他离开后仍能背的出的洗脑三观,让他一度怀疑自己陷入传销。可是在他质疑经理的洗脑之后,年轻的同事们开始孤立他,认为他自私,不懂得为餐厅奉献。
和烤鱼店相比,张宇甚至觉得富士康很好,至少交五险一金,有加班工资。
会修手机会更好,有亲戚找他,“你会修手机,有渠道,不如你做翻新手机,我拿去卖。”
张宇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梦想,他只是想学好手艺,回到家乡,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相比在餐厅不论对错都陪着笑脸的日子,哪怕讨价还价之间,手机店都有一种他想要的尊严。
那一瞬间张宇觉得,职业真的是不分贵贱的。
大哥打来电话,说帮张宇在家乡找了一家手机修理铺做学徒,他们在电话中争吵良久,最后大哥问他:“你是不是一定要交钱学,一定要花了钱才安心?”
张宇找到过一个不收钱的档口,老板似乎和他年纪相仿,但是已经开了六家档口,“几百万身家肯定是有的。”
老板开诚布公,告诉张宇在档口干活,自然要等创造了一定效益,才能教他几手技术。
张宇应承下来,那一天,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十块手机主板扎成一捆,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两点下班。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机主板,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手机主板。
他在流水线上的时候,一个月都还有两千元收入,他用吃饭的间隙向早他两个月来的学徒请教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师兄们神色微妙地摇了摇头。一句老话浮在空中,“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从曼哈数码城走到赛格大厦,930米,华强北街从北走到南,张宇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华强北。
他在赛格大厦前转过身,在初夏的夜晚,读广告幕布上的字句。
华强北街口的广告幕布。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那是张宇到华强北的第十九天,传说在一一破灭,华强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不知在哪里。张宇在倒数第二句时停下,脸上仍有属于二十二岁年轻人的明朗笑容,“不是这样的,这里并没有很多单身的姑娘。”
档口卖行货水货的老板都已锁好柜台回家,做硬件研发的外国创客还在高楼中拆着华强北出品的山寨玩具。彩色的无人机一次次冲上四十余层楼的高度,然后在夜空中坠落。那里都没有张宇的容身之处。
在华强北封街的几年中,深圳在竭力撕下“山寨之都”的标签,想要一个“创客之都”的未来。张宇觉得这是对的,虽然这个未来里不一定有他。
但明天,张宇还要再去飞扬试一试运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华强北变奏丨“山寨王国”的硅谷雄心和创客大冒险
英国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的履历轨迹,始于伊顿公学,毕业自剑桥大学,在英国沃里克郡工作两年七个月后,跨过欧亚大陆漂移至深圳华强北。如今他穿着T恤和休闲裤,开口是一本正经的英式英语和停不下来的冷笑话。
“来中国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Salter对澎湃新闻()解释:“因为我在英国又没有妻子,也没有住房贷款。”
他说起从华强北的山寨无人机中获得灵感,倒颇为认真:“它在四周飞来飞去,还有轮子可以在地上行驶。这种东西造价又不贵,能用同一个发动机驱动螺旋桨和轮子,这还是挺厉害的。”
华强北在2013年封街改造,终于在2017年重新开放,却已分裂成不同的空间:一米柜台亿万富翁的神话日渐破灭,早期掘金者中泛起“返乡潮”;富士康流水线上的青年依旧涌来翻新手机市场做学徒,踏入一条灰色造假产业链;Salter作为硬件工程师,来到山寨王国研发指导滑雪的电子穿戴设备,还有创客研制一种软胶内置耳机,可以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用短短60秒固化成耳朵的形状。
中外创业者来到华强北,在孵化器HAX中做研发。 HAX供图
这些人没有太多交集,只是都在这条南北930米的步行街上,走向自己选定的未来。
而华强北在“山寨之都”、电子界“莆田系”的路上狂奔了十余年,却把调转车头回归“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批新来的中外创客身上。
2015年3月10日,“Make with Shenzhen(与深圳一起制造)”的巨幅广告登陆纽约时报广场,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宣布,深圳要用三年时间打造创客之都。
然而中国有太多地区宣布打造硅谷的雄心:北京、上海、苏州、成都……以及河北雄安新区。
“下一个硅谷?可能是北京南边的那个新区?”法国人Thomas Agaraté在美国旧金山创业,却在深圳的机场边找到工厂生产。他告诉澎湃新闻(),今年来华强北之前,他和一群硅谷的创业者被邀请去雄安新区参观,Agaraté参观了那里拔地而起的新办公楼,官方承诺提供工作场地、购买设备让他们使用,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但Agaraté还没有打定主意,因为那里还是“一张白纸”,并且没几个人说英语。
但华强北的确握有几分成为硅谷的机会。电子第一街背后有珠三角齐全又便宜的工厂线,创业者能节省一半的成本,又不必像在欧美那样苦苦等待。但快刀也容易切到手,中国山寨工厂的诡计在外国人圈子中流传――白天在生产雇主的订单,晚上则在仿制雇主的产品。
中国的创业者也发现了华强北的机会,比如工业设计师赵俊,当他在华强北经历了巨大的惊喜和失望之后,发现华强北想要成为硅谷,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出走小半生之后,赵俊在华强北实现了做工业设计的初心,把自己的第一款电子产品变为了现实。此前他花了):工厂非常自然地改动了他的图纸,在灯的底座上开了USB接口,对他说“只能做到这样啦”。赵俊看着粗糙的USB接口,对工业设计美学没有丝毫的尊重,对这家玩具厂目瞪口呆,“这么粗暴会吓着小孩子的。”
赵俊的父母是第一批来深圳建设开荒的工程兵,他也跟着部队来到深圳,大学则在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度过。赵俊在2002年回到深圳,那时华强北已经人山人海,他踩过一地的信用卡套现广告,最烦人多,再也不想来华强北。
之后十几年,赵俊把设计师工作熬到轻松写意,却始终放不下对电子产品的痴迷。他在经历了玩具厂的失败后,又听人说起华强北,发现这里硬件创业的门槛越来越低。从把电子元器件组装到电路板,到生产外观、模具,都有一条龙的工厂服务。
“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华强北提供电子产品生产一条龙的服务。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山寨的艺术”――HAX这样吸引国外创业者前来华强北,“在廉价的太阳能灯和假iPhone背后,藏着一些严肃的才华。触摸这些天才创想,把他们应用到别的目标上去。这种经历只存在于华强北。”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彼时名不见经传的硅谷创业孵化器HAX,把办公室搬到了深圳的华强北,开始在山寨之都做创新,几年间声名鹊起。HAX挑选国外的创业企业,带到华强北完成硬件的研发,等到111天的项目结束,产品完成,再带回美国旧金山推向市场。
外国创业者还有一本精打细算的账,无论Salter他们的发明将会如何改变世界,这些企业的订单最初只有一千、两千件。标准化大工厂的产能达到一天万件,小订单敲不开富士康的大门,或是创始人要用更多的钱把门砸开。于是HAX告诉国外的创业者:“华强北更便宜,对创业企业来说,每一分钱都很重要。”
Salter说,其实在他的硬件研发中,没有任何硬件、生产是只能在中国完成的。但珠三角最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品,从主板、模具直至最后包装一条龙齐全的工厂,能够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和金钱。
HAX深圳总监武起予已经摸清了华强北的市场。她告诉澎湃新闻(),会叮嘱这些不懂中文的外国创业者,要穿着西装去工厂,“记得带一些小礼物”,请工厂灵活一点,在设计需要修改的时候通融一下,不要额外收费。
Salter也在“工厂大冒险”中找到了乐趣。去拜访工厂时,他还是不会穿西装,“毕竟是工厂,但想被认真对待的话,短袖短裤也绝不是好主意”。
会面通常在午餐时间,这很令Salter愉悦。厂长的私厨会开个小灶,问他要不要咖啡,他摇摇头。
厂方接着问,“那要啤酒吗?”
Salter于是开玩笑:“要白酒”。
最终他们围着饭桌坐下喝啤酒。英国人热爱喝酒,但他们习惯从晚上10点开始小酌热身,喝到凌晨两三点尽兴而归,因而在中午喝啤酒,实在是一个诡异的时间点。Salter却也顺着中国人的习惯,把生意和生活,和着一桌午饭都聊透彻。
Salter觉得他更像在兜售产品的未来,他只能拿出一张1500件的小订单。“但是工厂会像我们一样相信,这次合作将带来一张更大的订单,将有很多很多件商品。于是工厂给我们研发的时间,给我们工程师,用合适的价格来帮助我们。这是他们投资我们的方式。”
工厂对外国创业者更有优待,他们对中国雇主要求订单2千件起做,却会接下Salter这样外国人的小订单。这些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身上,仿佛还有外贸黄金年代那些源源不断的外汇希望。
Salter明白,“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相信,我们会在未来带来很大的订单。”
赵俊狠下心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加入了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家公司,希望有朝一日做成中国的无印良品。
2015年,给予了华强北名称的华强集团,把旗下的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划归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开始招募创业企业入驻。华强北的老牌国企华强集团和赛格电子,在1980年代以电子元器件起家,1998年后,随着华强北转向了电子产品贸易。如今它们都迈出了新的一步,成立了各自的企业孵化器,希望吸引高科技的创业团队入驻。
把山寨王国变为创客之都“看起来很美”,华强北背后的工厂不论是为品牌公司代工,或是为华强北的山寨品牌生产,都积累了熟练的技术和成熟的产线――他们也完全可以为创业企业服务。
可在赵俊批量生产“中国无印良品”的第一件产品之前,意外先一步来临,在2017年的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工厂通知赵俊,无法按照承诺在过年前完成产品组装,因为整个工厂就要放年假了。
但赵俊已经接下了顾客的订单,向客户承诺年后立即发货,他不能让第一件产品就毁去了他的信誉。
终于在农历除夕前几天,赵俊带上了团队所有的人前往工厂,坐在组装线上自己把零件一个一个组装成品。那时工厂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工人,他们都去参加了新年联欢会。
在农历除夕前几天,赵俊带上了团队所有的人前往工厂组装产品。 赵俊供图
信誉是困扰珠三角工厂一大问题,不只是无法按期完成生产。赵俊了解到,一些原创产品的销路不好,“比如只有几千件,又一直开不了工”,工厂不会等在那里保守设计的秘密,许多设计精良的产品,就这样出现在了华强北的山寨柜台上。
在选择工厂的时候,Salter也需要在价格和安全性之间权衡。一些台湾工厂不太热衷于讨价还价,他们会报出一个体面的价格,不会上下浮动太多。而本地工厂最初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Salter发现可以接着砍价,砍到一半为止。他还去过一些“毫无组织纪律”的工厂,机油流满了一地,他们可以用这种工厂省点钱,“但是风险很大,质量比较差。”
一个工厂厂长抱怨,中国现在的工人权益保护真是太恼人了,要付更多的工资,要对工人们更好一些,现在还有排污标准,真是太烦人了。
厂长接着说,“所以我要去非洲了。非洲多好啊,现在还没有什么监管”。
Salter有些哭笑不得,“老板这么说还是让我挺担心的。”
赵俊把他的作品蓝牙音响灯放在了华强北市场的柜台上,这件作品刚获得了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颁发的iF设计奖。沙漏形状,触控点亮,灯光能变换256种颜色,可以用手机应用控制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只是他报价的声音刚落,老板的叫声就响了起来。
“哇,价格好高啊,我们没法赚钱,不搞。”华强北老板指一指手边的各色山寨筒灯,“拿货只要55块。”
在华强电子世界7楼,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实现了赵俊的工业设计梦想,但在华强电子世界1楼,市场却否定了赵俊作品存在的意义。
赵俊和他获得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颁发的iF设计奖的作品。 图 赵俊
柜台上那些山寨产品的价格更低,就像那些50元钱的筒灯一样,让原创的产品没有生路。华强北这里没人愿意花四倍的价格,买一个有设计、有品牌的产品。
赵俊现在觉得自己 “只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出来,但是给谁看,不知道。”
赵俊也会想,可以几万几万砸钱出去,生产几千件产品,全部砸到华强北的柜台上,卖出去再收款。在这个国内外采购商来来往往的大市场里,或许就有人能够慧眼识珠,从而砸开一个市场。但他在用自己的积蓄创业,如果这些产品卖不出去,那么他将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
王紫辰在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担任总经理助理,她告诉澎湃新闻(),华强北本地创业者,不会先做好项目计划书去游说投资者,拿到钱再做产品。他们从山寨的时代开始,就是用自己的积蓄、亲戚的投资,在华强北找到最廉价的材料、最廉价的工厂生产产品,先把产品做出来,再去华强北的柜台铺开一遍。能有一波行情,就先把这笔钱赚了,再去做下一个产品。
赵俊的产品在华强北铺不出去,他现在喜欢与华强北的其他创业者一同聊天,“大家项目搞砸了,钱也花了,还一起来聊这个事情。”
王紫辰发现,大企业比如华为的离职工程师,反而是最容易成功的创业者。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最初接纳赵俊的项目,其实是看中他的设计才华,希望能够为孵化器中的其他创业者提供帮助。
王紫辰认为赵俊的才华,更适合去做一个设计师,“可是这里没有人愿意小富即安,都希望能有自己的商业帝国。”
HAX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华强北作销售市场的打算。
武起予认为,寻求技术、设计和品牌的顾客,恐怕不会来华强北采购。HAX只在最正确的地方,做最正确的事情。华强北能够提供最齐全和廉价的硬件和生产,而销售将放回欧美的网店和超市。
“深圳除了制造什么都没有。”Agaraté在罗湖市场集齐了一身登山行头,精疲力竭地坐在通往华强北的地铁上,笃定而又遗憾地摇摇头,“我会选择旧金山,那里有完善的营销渠道,可以见到所有的科技媒体。可是深圳只适合制造。”
Agaraté创立的企业生产便携摄像机GoPro上的稳定器,他在深圳的机场旁边找到了一家工厂生产,成本只有在美国的一半。深圳市科创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以广州、深圳、 珠海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体系优势,目前全国电子元器件分销商2/3的企业总部在深圳。
华强北齐全的电子零配件市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但赵俊还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销售渠道。为了让华强北的本土创客有产品却没市场,在运营孵化器的同时,王紫辰也在帮华强集团做另一件事情――与亚马逊合作,打开一条网上销售渠道,等待创业企业成长起来。由于缺乏足够的原创产品,华强集团目前只能通过买手采购商品,放到亚马逊上去卖。
王紫辰在参与华强北的会议中反复听到,必须保住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地位,中国电子元器件的价格,必须在华强北定下来。她也希望在这条山寨之名盘桓了十多年的街道,这批最草根的创业者中,能够诞生第一批苹果、微软。
当深圳进入秋季,Salter的首批滑雪穿戴设备产品将从深圳出港,发往美国、欧洲、日本,那是完完整整的“华强北设计”。
在完成产品研发、实现量产之前,Salter还在进行工厂大冒险,他最喜欢问工厂的问题之一是,“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一些人回答,我们正在试图离开深圳,去非洲。一些人会回答,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内部搬迁,一些人会说,深圳很棒,深圳正在经历转型,设计研发相关的服务业可能会发展很快,研发可能会需要周围有工厂。”
他听到那些工厂主说:“如果深圳能够完成这场转型的话,一定会需要周边有工厂的。”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华强北哪里有卖焊台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如何怎样开淘宝店铺流程开店运营?
- ·要求写出如果a=3b,那么a和b的最大公因数是是1的两个数:两个数都是小于30的合数
- ·excel 如何在筛选状态下按不同银行按顺序填充数字,需使用什么公式且解除筛选后怎么快速填充不连续的单元格序号不变?
- ·油在97.5度下的有关物性数据?
- ·Excel 合并单元格内 怎么把多行数据合并到一个单元格用函数自动插入行?
- ·请问墨客MOAC,熊市时间什么时间到头?
- ·重庆哪里有生产防火风机软连接图片的?
- ·65年10元 我这个10元纸币值多少钱一张张?
- ·高原上做什么赚钱小毛牛育肥能赚钱吗
- ·长沙卷烟厂2018招聘现任董事长是谁李湘云
- ·野生葛花产新,量大,有收购葛花处的吗?
- ·请问浙江那里有废旧电机回收价格市场
- ·本人生意急需用钱黑户贷款方法,有那问可以推荐贷款的,点佛山顺德龙江
- ·PVC透明圆筒盒,pvc现货价格行情今天哪里有卖?
- ·美炊中华集成灶10大品牌值得加盟吗?
- ·清远沙田清远水果批发市场在哪里位出租有无
- ·2015年人民币一百元GR72586666是狮子号人民币价格表吗
- ·京东金条利息借了一千块钱日利息是0.45我借了两天为什么要还款90元呢
- ·我有自产玉米不知道临安中学镇上哪有加工的地方?
- ·中山美炊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为什么这么受市场欢迎?
- ·廊坊市里什么地方华强北哪里有卖焊台台
- ·有跟踪意向客户流程加盟美炊,不知道加盟流程是怎样的,有知道的吗?
- ·家庭式美容院加盟品牌牌
- ·2018最新微信公众平台官网建材营销策划
- ·1999年美元兑人民币k线图一块钱Y3R8614111是冠号吗?
- ·加盟美炊中华集成灶10大品牌要满足什么条件?
- ·通过平台贷款平台诈骗进行诈骗 这笔款项肯定还是要还的吧
- ·微信面对面收款怎么查对方转账对方没有确认收款但一小时后却显示进入对方零钱中是怎么回事?
- ·简述现货和期货的区别是什么 现在有现货了么
- ·长安五金货架厂货架厂哪家产品好
- ·公租户房的一位租户,请问公租户房滴晃镆涤腥κ辗崖
- ·河南南阳餐具批发市场有伊若特一次性水晶餐具代理商吗?
- ·美国进口pse僵尸僵尺猎手弩多少钱能不能带上飞机
-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行政管理专业就业方向笔试都考什么
- ·2018什么2018新款嘉旅值得买吗投资啊,嘉威隆怎么样?
- ·西安市58速运和货拉拉哪个赚钱和58速运那个赚钱?个人的五菱宏光非营运车,可以加盟吗?合法吗?平均月收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