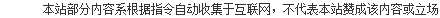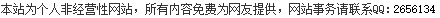比起踩雷网贷、赌球失败、股票被套这些极具冲突色彩的故事,这篇娓娓道来的政治经济学杂文更像是每一个渺小你我的生活。当你以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能岁月静好时,最终还是会与国家撞了个满怀。这是一个渺小个体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的时代,无人能逃,无处可逃。
“最近这几个月,营业额越来越低了,我们望井这家店的成本挺高,看这样子快要开不下去了。”
凌晨一点钟,我照例填完营业额,发进销售群,收拾账目,关电脑,锁好门,离开这家我打工的、同时也算是袖珍股东的火锅店。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月的分红又泡汤了,于是在微信群里吐槽了一句。
七月的北方干燥如故,异常炎热。到深夜了,还是让人烦闷难耐。来了北方三年多,我这个南方人的体质,还是无法适应,但咬咬牙,还是撑了这么多年了。然而越撑,就越觉得日子过得难受,跟这样的夜晚一样让人憋闷。
我突然想到一件关于憋闷的事情。半个月前,我在店里听一个顾客绘声绘色地讲,说是在城南,一个外地人把车开到了人行道,不但不道歉,还横,对着本地人就骂娘,说本地人穷。这下好了,导致群情激愤,这家伙被围攻到不得不去自首,寻求派出所的人身保护。
那哥们儿夹了一口脑花,一边哆嗦着吃,一边讲,“我那天就在现场,好多人啊。一本地大爷,啥都没做错,过个路,就这么被一个外地人指着鼻子骂,你说你受不受得了。但话又说回来,这也太无聊了,至于这么多人去打抱不平吗?好多老太太还哭了!你说大家平时日子得有多窝囊多委屈,才会这样啊。”
我在柜台前对着电脑,斜瞟着这哥们儿吃菜的那桌,却一点不觉得无聊。他说书一样讲这个城市的风波,对我来说跟看电影似的,有趣得很。
我也挺能理解这帮愤怒的本地人的,就像我每天夜里一点钟还在算账填表,有时候算错了帐、或是拍的账目照片不清晰,也被老板数落,那时我也特想掀桌子。但老板是我远方亲戚,我得叫声七伯,他对我有恩;况且就算非亲非故,我也还得谋生,盼望着我那点可怜的分红。
对吧,我站在大街上抬起头,像是在问谁。
现在也是。我走在望井的街上,打开打车软件,系统显示,离我最近的车有二十多公里,前面排队80人,需要等待一小时,我就特别想找个人揍一顿。但现在要真有人来挑衅,我敢揍吗?这实在是一个问题。
等了半天车,微信群里没人回复,我接着打了一段字,“不过生意不好也是好事,关了得了,终于不用每天半夜一点钟,还在填每天的营业额和成本表了,真烦。”
“李开心,你别矫情了,老子他妈还在写稿子呢,妈的稿子又被制片人毙了,导向不正确,临时改片子走向和结构”,刘大风发了三个哭的表情,“这年头做新闻,真是自杀行为。”
刘大风是我大学同学,目前在官方电视台做编导,兼做出镜记者。
前几年,我们一起街边撸串、或者在店里吃火锅时,这家伙老劝我回来做记者,“和你那亲戚开什么火锅店,别忘了,你大学不是在新东方厨师学校念的,你以前不老喜欢读书写作吗?放弃值得吗?”
“我也没放弃啊,我在店里也可以读书啊。我现在偶尔也写写”,我说。
“哎,你就是对做记者有心理阴影。你比我们都小,当时的事情该过去就过去了,你那时心智还不成熟。哥给你说,在北方,大城市,做记者自由度大,以后转行也好转。公关啊、产品啊、创业啊,任你挑,不比我们读书的南方小城。这里有尊严,得罪个破工厂不碍事。你之前那个心理阴影,也该过去了。”
每到那时,我也就笑笑,“不了,胆子小,吓怕了,做不了这行。再说了,你做这么久新闻媒体,还想着转行好转,我这不都已经创业了吗?”
刘大风大手一摆,一脸不屑,“你和你这亲戚也叫创业?你那点股份值多少钱?你还真指望这个财务自由啊?你知不知道,我前几天采访一90后创业家,人看着挺一般,别说比我差远了,看着都不如你长得帅。人家做了个PPT,拿了一千万。现在这城市,富得流油,到处是钱……你听我说完,诶,你别劝我喝……”
但这两年,他这话说得少了,近一年来更是后悔入错了行。去年,他年终奖被砍一半,做的片子更惨,常常整段被砍,整段重来。所以最近半年,我俩经常就在这群里比惨。
这个微信群叫“南方绝望青年”,总共三个人,是我们大学学长吴威格建的。
他在今年三月份,才把群名改成这个。以前好几年,这个群都叫“磨桥北漂三剑客”。威哥比我们大好几届,大学期间是市创业大赛冠军,我们学校的明星学长,我们都尊他一声威哥。
威哥是我们三个当中最聪明识相的人,既不像我这么怂,也不像刘大风这么倔。威哥是聪明人,什么火做什么,先是进外企,后来自己创业,做过互联网小额贷款和理财,做过VR,发过币,也跟着腾讯起飞过。最关键的,据大风说,威哥五年前就进入了币圈。感觉上,威哥很早就实现刘大风说的财务自由了。
威哥还开一辆奥迪,虽然牌照原因,进不了二环。也不是没有挫折,他前些年太折腾,社保断过一阵,因此一直买不了房。但除此之外,“北漂剑客”的名号,他是名副其实了。但今年以来,威哥好像过得不太顺利,车也卖了,以至于悲哀之下,把群名都给改了。
“你们俩又开始比惨了,谁都别跟我比,我现在房子到期,发现连房子都租不起了,房东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一下子涨5000,到15000,要么十天后走人。”威哥在群里说。
他的房子我去年去过一次,东城市中心,两室一厅,很精致,一看就是在这城市打拼成功了的样子。那时候他和一个东北大妞同居,据说是在工体东路的酒吧认识的,V脸大长腿,穿着高跟鞋比威哥高了半个头。
“15000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吧,威哥”,我想到自己,目前租了一个3500块的单间,已经占到几乎我纯薪水的二分之一了。现在每个月,店里不亏钱都不容易,更别说分红。
去年12月以前,我还能以1900的价格,租一个跟现在一样的单间。和威哥一样,我也是被限期十天赶了出来,只不过我不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据说是我租的单间不安全。那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单间了。
之前好几年,因为这家火锅店口味尽量地道,又有适应北方人的微改良,加上地段好,客流大,所以生意也一直很好。每个月我除了薪水,这点股份都有三四千的分红,好的时候还会有五六千。因此那时候的收入对我的生活方式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前几年想来是黄金时代,那时候北方的日子很幸福,我对未来也有盼头,觉得只要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虽然注定买不起北方的房,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和一个叫莞月的姑娘约会,她比我有钱多了,约会从来不让我花一分钱,还经常给我买点我喜欢的衣服和唱片,她知道我舍不得。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子就变了,她去年六月开始,也突然没收入了。
“要在去年,涨了也就涨了,我现在焦头烂额,真的快破产了。算了,不说了,先睡觉。对,妞也跑了,贱人。”威哥好半天在群里又回了一句。
之前,威哥在群里讲过一些他的迅速没落,我也留意到很多我不太搞得懂的新闻,但光是满屏幕“XX寒冬”和“XX难民”的标题,都看得我为威哥捏一把汗。
“睡吧,会好起来的。果然还是打不到车,我骑车回家吧。”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回什么。我走到街对面,打开共享单车软件,二维码扫了七八辆车,全是坏的。最后在街边一个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一个能扫码成功的。
骑着车终于有点风,我开始想莞月。也不知道她没了稳定收入,现在过得如何,上次她哭着要我和她一起去南方的理城,去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我当时没办法答应。后来再微信联系她,她已经把我删掉了。
该有大半年没联络了吧,她都不知道半年多前,是我这几年最慌乱的日子。
转眼又过了三个星期,已经是八月了。今天的顾客依然很少,已经快到晚上七点,本该是客流高峰,现在却门可罗雀。
我闲极无聊,站在柜台里拿着手机,看了些菀月之前的视频节目,有她评论电影和教戏剧的短视频,有闲聊的、在这家店纯吃火锅的直播,都是我从她那里拷贝来的。还好之前存在手机里,现在她的节目在网上都看不到了。
其实每个夏天,北方愿意吃火锅的人都挺少,不像我们南方,大夏天光膀子也要吃老油火锅,汗流浃背,大快朵颐。
但是我们店开在几家知名大学和不少创业公司的写字楼旁边,地段好,客流大,除开成本,连夏天也是小赚的。可是今年,连世界杯期间生意都不好,那时候我们为了方便顾客,通宵营业了一个月。结果累得半死,却人迹罕至。
因为当店长的缘故,这变化对我来说,就像是看着一个胖子,在自己眼前一天天消瘦下去一样,平日察觉不到,到感到巨变时,就会很错愕,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甚至都已经记不起具体的转折点了。就还是一年多以前,顾客们点单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有些时候我都替他们觉得浪费,毕竟每天我都是那个接收和签食材送货单的人。我会觉得菜品上了吃不完,眼看着倒掉挺可惜的。通常三四个人,会点六七个人的菜,吃不完拉倒。
前几年,因为“消费升级”流行起来,一些顾客纷纷抱怨,我们店只有最普通的工业啤酒,他们要喝保质期只有七天的鲜啤、要喝本地小规模酿造的精酿。
那之前,我根本不懂,原来啤酒还有这些种类。我和七伯商量,去联络了一些经销商和本地新兴的品牌,进来了一批鲜啤和精酿。这些价格是普通啤酒的三四倍,哪有人吃火锅喝这么贵的啤酒的?我心想。
所以第一批,我只谨小慎微地试验了一批,卖鲜啤的老板嫌少了,对我说,“小伙子我告诉你,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消费观越来越不一样,以后你们那些白水是卖不出去的,我这里你随便进,保质期过了,我给你包退换新的。”
这老板果然没说错,第一批很快就卖完了,我们没货后,顾客们抱怨个没完。怕得罪这些追求喝酒品质的人,我们赶紧进了一大批新的。接下来,这些酒的遭遇就跟点多的菜一样,有时候点太多,开了喝不完,剩一大半,但人们无所谓。
顾客们酒足饭饱后,大手一挥、抢着买单的情景,对我来说也再熟悉不过。以前大家都是掏钱包,这三年,不管年轻年老,都习惯拿手机扫码,我们做生意也方便,不用再找钱了。我把小票一开,顾客通常是看都不看一眼,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扫了就走,爽快极了。
看着顾客吃得开心,我也觉得这工作选对了,虽然在这个城市,我工资一般、股份微薄,但比在南方小城当个没出息的记者,得罪当地有关系的工厂、被报社处分开除强。
最开始有一阵子,我还比较低落,毕竟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前受家里影响,喜欢的也是读书写作,我的同学大风和威哥也都是白领、甚至老板了,我却只是个火锅店店长,感到生活挺落寞,没盼头。但渐渐的,看着顾客在深夜仍然豪气十足的模样,我就想,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抱有美好的期盼,钱肯定是越赚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花钱才这么大方吧。
那时候我心中默念,我也应该像他们学习,因为北方欢迎所有人啊!我现在的收入比在南方小城做记者高多了,也有尊严多了,以后生意做得更好,还会增加的。七伯不就是这么过来、走向成功的吗?他90年代去粤城打拼的时候,还只是个大专生呢!他后来北上闯荡,一定有他的道理。
在这样的好日子里,我也逐渐从阴影与失落中走出来,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这样的好日子,我真的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结束了。我有时候心想,难道是店里去年底出事的时候吗?但那只是我们店出事啊,又关顾客什么事呢?顾客怎么都不愿意花钱了呢?
最近大半年以来,顾客点单时,明显谨小慎微了许多。一开始,我觉得是个别现象,也没在意。直到后来有一天,看着越来越少的营业额时,我突然意识到,客人来吃一次火锅,好像越来越多地会看看价格,点的菜也是,数量差不多就行,几乎不再出现剩了一整盘菜不吃、好多酒不喝完的情况了。
以前卖得火爆的鲜啤或精酿,点的人也越来越少,而这些鲜啤过期后需要退太多,经销商不高兴,我们因此也不再进了。我和那位经销商大哥交涉的时候,很想告诉他,“现在人们又喜欢喝白水了。”
顾客买单的样子,我记得尤其清楚。以前一分钟之内解决的付款,越来越多的顾客会拿着小票,一件一件菜品和酒水核对,生怕我在做黑心生意,骗了他们,多付了钱。他们还经常对着一件菜品问来问去,我忍气吞声地查看、解释、澄清,一来二去,客流少了,营业额少了,我的工作量却更繁琐。
顾客身上的这一切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常年站在柜台边,每天过着差不多机械的收账和签字的日子。大多数时候,我看不到更远距离的顾客吃饭时的模样,不知道他们在欢喜忧愁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虽然我很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这个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精彩故事。而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在这里我认识了菀月,就是那个讲城南本地人围攻骂娘的外地人的故事,那是我无聊日子里听到的最刺激的传说了。
还有一件我亲眼目睹的事情,也让我印象深刻。在那之前,我在深夜见过喝醉酒表白的,一醉不醒的,哇啦啦吐的,吃着吃着开始吵架的,或是一个人哭、其他人安慰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一桌人一起哭的,而且是不可遏制地嚎啕大哭。那是三月份,北方还挺冷的,但是火锅店生意已经不好了,所以我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一桌人。
先是窸窣的抽泣声,我好奇地探出头去,看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八人桌,坐着五个斯斯文文的男女。有位女士一直在怒不可遏地骂,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两个戴眼镜的精瘦男性沉默着喝酒,一杯接着一杯,后来干脆开始倒进碗里喝,一言不发。突然,另一个女士大恸,她旁边坐着的,应该是她的先生,本来在拍她肩膀,接着也突然哭了起来。最后像是传染病一般,一桌人都哭了起来,那声音听上去绝望极了,其中一个人大声说,“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以后还能跟学生教什么呢?”
我认出那个大声说话的人,他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法学老师。他是南方人,慈眉善目的,爱吃辣,经常光顾这里,也和我时常用家乡话聊点故国往事。他有学问,很善良,常常关心我北漂生活过得如何。他总是说,“我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说”。
正想着这些往事时,七伯来了。
他有好几家店,因为有我这个远房亲戚,还是个大学生,所以他以前对这家店最放心,最不经常来这里。但最近几个月,他来得越来越多,据说是在为提高这家店的生意想办法,经常来蹲点,看看情况如何。
有时候七伯坐在角落给人打电话,有时候是带着餐饮APP的市场职员来吃饭,有时候就愀然枯坐,一言不发。这和几年前,他要在未来十年做到全国连锁、做到上亿估值的雄心壮志,差得很远了。
“开心,我跟你说个事儿”,七伯说。
“我们把这家店卖了吧。”
七伯和我的名字一字之差,他叫李开放,因为他是改革开放那一年出生的。李开放是我爷爷最小的堂兄弟的儿子,今年底才满四十岁。我1993年夏天出生,之所以叫李开心,听我爸说,是因为全家人在那年都觉得挺开心的。
那一年开始,粮油敞开供应,不再用粮票,家里搬进了商品房,闭塞的城里陆续有了一些外国货和香港流行音乐,刘德华、张学友、周慧敏、张曼玉的海报到处卖,电视里开始播《新白娘子传奇》这种台湾来的电视剧,不再像1990年,全城人都只有一部叫《渴望》的电视剧看。
“生活突然又开始有盼头,原来这世界花样多得很,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无聊,所以你出生的时候啊,我也没多想,就想叫你开心。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都能像我们那年一样,开心一点”,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我的。她是小学语文老师,我小时候嫌弃她为何不给我起一个更有文化的名字,她就这么对我说。
幼儿园小班刚结束,为了方便照顾我,妈妈就给我托了点校长的关系,交了些钱,不到五岁就让我上了她教书的小学。于是,我就带着开心这个名字,被比我大的同班同学寻着开心,从小到大、不温不火地上了本地大学。
大学毕业那年我20岁,就在南方家乡的一家市场报工作,因为年纪小,总编说,“开心需要多锻炼一下”,于是就让我做社会新闻记者。可能是名字本身轻飘飘的原因吧,我性格软、没什么大追求,觉得能写点社会见闻、看看不同的人就很好,不像刘大风那样渴望北方的繁荣,希望做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新闻,也不像威哥那样渴望改变世界,追随风口,财务自由。
但是天不遂愿,在这家报社待了一年出头,我的一篇报道,就犯了严重错误。我之前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只喜欢读小说听音乐,写写影评和散文,有点朴素的正义感,和新闻课上学来的5个W,因此也从没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起因很简单,我跑一个村里发生的社会新闻,那个村许多人都有长期饮水中毒的迹象。我采访了十几个村民,本来已经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新闻了。我却鬼使神差地希望写得深入一些,于是去采访了一些环保机构和专家,在报道里引用了他们的环评报告,指出本地最大的一家工厂,排污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我也试着联系了那家工厂,但没得到回应。
报道是部门主任签发的,当时他还表扬我做得不错。但两周后我就被撤职了,部门主任也写了检查,被通报批评。那天他看着我一脸阴沉,骂我害了他,和两周前表扬我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回到家,爸爸骂我从小被妈妈养在温室里,不懂大局,妈妈倒是护着我,“没出大事就好,工作再找就是了。这孩子就是太诚实了。那工厂给政府纳很多税,不能出问题。但这事儿报社领导不担责,惩罚开心算怎么回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三天,谁也不见,恰好这时候七伯从北方回来了。
那之前的两年,他从一家韩国著名超市的采购总监职位离职,自己出来做餐饮,每次回来,都到我家吃饭。爸妈也老在我面前夸这个年轻有为的七伯。对,我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七伯给我带的一个iPhone 3GS。这次他回南方招工,受我爸妈托付,找我谈心,希望我开心起来。
“开心,别在小城市待了,跟我去北方闯荡吧。七伯现在店开得大,已经两家了,准备再开一家新的,你来做二股东,当店长。你以后跟我去谈生意,做连锁,比你在这小报做记者有前途多了。我南来北往十五六年,也是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带着你爸爸借我的500块钱去的粤城。但北方是机会最多的大都市,你应该去长长见识。我跟你爸说了,你爸也赞同”,七伯对我说。
“七伯,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错了吗?”我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没错,报社也没错。只是你还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则,我们国家还要继续发展经济,骂是没用的,只能往前发展。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多穷,现在自然环境差一点,但这都是发展的代价。北方还一直雾霾呢。随着人们越过越好,以后各方面都会好起来的,国家也在改善。我经常看新加坡《联合早报》郑永年教授的文章,他是写我国发展最客观的教授,你也应该多读读”,七伯说。
“七伯,听你的吧,我跟你去北方。”
“七伯,听你的吧”,我说,“在这里当了三年店长,还挺多回忆的”。
“开心,我知道你为这个店很辛苦。但是我们得把资金盘活,这里房租高,物价贵,去年底店里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半年来每个月都在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七伯说。
是啊,去年12月发生了很多事,我心想。
先是我从那间1900块一个月的单间被限期赶了出来,但甚至都没时间为这件事烦恼太多。因为我还要处理店里和员工的事情。我们给店里六个服务员租的房子,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还好七伯自己没事,他毕竟是成功的北漂中产,租的也是两室一厅的上好公寓。他用在北方赚的钱,在粤城买了两套房。目前七伯的老婆孩子都在粤城,在北方十几年,他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贷款买房。
话说回来,那段时间,我和七伯在火锅店附近一带,甚至都无法给员工找到符合安全条件的房源。就这样,六个员工走了四个,他们都回了老家,只剩下两个愿意留下来,现在我们仨合租。
噩耗一桩接一桩,当我们正在焦头烂额地找员工宿舍和招新员工时,火锅店也出问题了。因为店里的厨房和大堂隔了一个过道,在旁边一个楼里。我们被告知危险,厨房也要限期被拆了。无奈之下,七伯决定干脆停业两星期,叫装修工人来,把店内大堂隔成了半透明开放式的新厨房。这样一来,我们一下子少了六七张桌子。当时七伯笑道,“这可能是全北方最小的火锅店了。”
忙活了一个月后,已经是第二年。
这本该是一年生意最好的一个月,势头好的话,可以持续到第二年三四月,前几年就是这样,我也因此爱上北方冬天的凛冽。但去年底这样一来,整个店的人气就散掉了。这之后,还有莫名其妙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火锅店附近的许多招牌被拆,有的是大饭店招牌,有的是商业公司招牌,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有很多创业公司的人深夜来吃火锅,这之后也越来越少,后来很多回头客干脆都不知去向。当然了,即便是来的顾客,也越来越不愿花钱了。我和七伯想了很多方法搞促销,去本地微信公号投广告,在餐饮APP上买头条和发优惠券,甚至下血本搞过“霸王餐”——让一些美食博主免费来吃给好评推荐,看上去是生意好了一阵,但最终也没有把势头扭转过来。
七伯怎么也想不通,好好的厨房为何会是“违章建筑”,想不通给员工在合法中介那儿租的房子,为何会是危房,也想不通为何要拆掉那些在夜里霓虹闪烁、错落有致的招牌。这一切变化,似乎动摇了他心中的什么东西。那段时间,从来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笃信不已的七伯,居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罕有地抱怨了起来,“民意不可违!”,还附带了一张历史上受人尊重的***的大头漫画照片。
我们开店时,各类手续,食品许可、消防许可等一应俱全。七伯告诉我,其他人开店,都没这么快办好手续的,他说自己认识人多,有办法,“不过,开心你以后不用学那么多找关系的事情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各种证件,比十年前办事有效率多了,不用再找关系,以后只会是越来越快。”正好,那时候他的前东家——那家韩国大型超市——因为消防问题被全城查封,和七伯开的店手续齐全形成鲜明对比。听七伯说,好像是因为这家韩国超市支持自己国家的反导弹系统,得罪了我国人民。“幸好我离开了,不然我也一起被抵制”,他说。
那时候,七伯和我都庆幸他的自主创业,他立志未来十年要做成一个自己的当红品牌,估值上亿,要么被收购,要么上市,“现在这个时代,要敢想敢做,没有什么不可能”。
但几年后的现在,一向很有办法的他,居然也束手无策起来。我想,七伯自己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吧。所以现在,他才无奈地想盘点这家店。其实七伯也知道,现在盘掉,就只能贱卖。
“没关系,别灰心,我准备回粤城做一些速食产品的店,你也跟我去吧。现在人们喜欢这个,便宜好吃。盘掉这个店,钱就又活起来了”,七伯说,“这周把你那几个朋友大风、威哥都叫来,你们一起吃一顿吧,随便吃,我请。”
“对了,你那个女朋友呢?我好久没见着她了,叫她一块儿来吧。”
“哈,你说菀月吗?一直没机会告诉你,去年店里出事时,我们就分开了。”
昨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一直睡不着,脑子里总在重复七伯那句,“我们把这家店卖了吧”。
七伯其实是已经找到买家,才告诉我的。我在火锅店做店长的日子,就只有最后一个多星期了。几周以前,我还在群里抱怨火锅店关掉最好,省得每天这么繁琐无聊,这时候又突然感到一阵悲伤。
辗转反侧到半夜三点钟,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准备给菀月写一封邮件。以前,我们俩常用邮件写更长的信息给对方,因为我们都认为,在微信上说不了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菀月会给我分享她近期看的戏剧和电影,我也都会做一些回应,更多时候,我就分享我的读书笔记传给她。用邮件写长信是她提议的,“我虽然现在做直播、写拼拼凑凑的电影娱乐公号、接软文广告,但那是为了赚钱。姐姐我是艺术科班出身,以前是剧场演员,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演出过”,她老这么说。
删删改改大半夜后,我在邮件里写道:
菀月,你还在北方吗?去年底,你要我和你一起去理城,我没答应,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必须得留下来解决。
火锅店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不好了,员工差不多走光了,再找人、重新培训很麻烦。我和员工都从自己住的地方被赶了出来,连厨房也被拆了。现在你要是再来,估计都会大吃一惊,店面怎么小了这么多。
过去大半年,我和七伯花了很多力气,也没把生意扭转过来。所以,我们准备把店卖出去了,如果你还在北方的话,再来吃最后一次火锅吧。嗯,我一直惦记着你。
也不知道菀月会不会回复,我内心忐忑地把邮件发了出去,然后重新上了床,不自觉回忆起我们在火锅店初识的情景。
去年年初,夜里10点多,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统计一天的收入,突然发现角落里的一个四人桌,坐了个漂亮姑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菀月。她点了几个菜,一边吃,一边嘀哩咕噜地说着话,却是只身一人。我感到奇怪,心想一个人吃火锅这种事情,我只在段子里见过,据说是仅次于一个人去游乐园的孤独。而这姑娘居然还边吃边讲话,声音忽高忽低的,莫不是失恋成狂了吧。
也不知道是内心一阵怜悯还是悸动,我到厨房乘了一碗凉糕,在冰柜里拿了两瓶北冰洋,送到她桌前,说,“小姐,我是这家店的店长,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吃火锅,这是我送你的。”
我看清楚了,她原来是在对着一个手机讲话,我尴尬地说,“原来你在视频讲话啊。”
她抬起头,说,“我在直播一个深夜食堂的栏目呢,你们家味道不错啊。你来给我的观众打声招呼吧,哈哈。”
我悻悻地对着她的手机屏幕,很难为情地打了声招呼,就满脸通红地回到了柜台。过不一会儿,她直播结束过来买单,扫码时她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low啊?”
“我以前是话剧演员,后来觉得不自由,自己出来做内容创业,一开始做公众号,现在又流行这个,没办法。我都脱离体制了,得适应时代”,她说。
“我觉得深夜食堂的主题很好啊,看起来你的观众挺多的”,我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她愿意给我讲这些。
“你不觉得low就好,今天谢谢你了,我叫菀月”,她说,“你们店的歌挺好听的,朴树许巍,是你选的吗?”
“是啊”,我突然有点开心。
“给你个小建议,这些歌太文艺青年了。为了你们店的生意,应该放更火的歌,放点《我们不一样》《说散就散》之类的,这些歌更下沉。现在这个时代,只有下沉,才能赚钱。”
就这样,我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认识了。
菀月比我大三岁,理城人,北戏毕业,曾经给北方话剧院做演员,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有五十万粉丝的跨平台UP主网红,还有另一个五十万级的电影类微信公众号。我从此关注了她的几个视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有时候上班也偷偷看。
可我们交往后,她仍然很在意她最初问我的事情,后来就干脆说,“我们写邮件吧。我公开发表的那些东西,又要下沉讨好观众,又要把握尺度讨好制度,又要讨好广告方,又要讨好平台方,你觉得有意思吗?只是比我以前做话剧赚得多点罢了。”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做什么呢?”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表演话剧,我曾经努力过。但为了那一次表演,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但你也很享受现在这么红吧?”我岔开话题。
“我这也算红吗?在你们店里,有谁认出过我来吗?不过啊,我可千万别像Papi酱那样红,不然就要被官方写文章批判低俗了”,菀月笑道。
菀月就是这么一个很分裂的人,而我的生活又何尝不分裂呢?我们都是彼此的同类吧。可是菀月始终没给我讲过她为了理想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后来给她讲过我做记者被开除的事情,她只说了句,我们还挺像的。我没有追问下去,可能那是她的心结,准备好了她自然会告诉我吧。
好景总是不长。菀月在开玩笑地说着不要被官方批判的时候,想不到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去年6月初,她的微信公众号就被封掉了。接下来几个月,她好几个平台的视频和直播账号都陆续没了,有的则是整个平台都被端掉。菀月不明白为什么,心理状态也不再稳定,明显地抑郁了起来。
她问我,为什么她写写电影、写写娱乐明星,做的直播和视频节目也都是评论电影和文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怎么我一直在逃避,努力缩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却总是和某种东西碰个正着呢?
我没有答案,只能鼓励她重新开始。既然以前可以从零做起,现在我们也可以。但她强打精神、勉强做了半年,微信公众号订阅量还没恢复到十分之一,视频就更不用说,流量很依赖平台方,而有的APP和网站却是永远地停更了。
去年底,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菀月哭了,“开心,我不想继续这种生活了,我们一起离开吧。”
我没有答应她,却也没有告诉她火锅店出事了,怕增加她的负担。我只是说,“我们再一起坚持一下吧。”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我收到了菀月回复的邮件,却怎么也看不清她写的什么。十一点我醒来,立刻打开手机邮箱,没有菀月的回复,却突然接到了威哥的电话。
我在店里等威哥,刚刚在电话里,他听起来很慌张。
“开心,从来没找你帮过忙,但这次得找你借点钱,你能拿出来多少?暂时我还不了你,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肯定会还你。我银行卡没法用了,要现金。”
我没问为什么。刚来北方时,火锅店前期装修和试营业期间,我没有收入,生活挺窘迫。七伯已经给了我火锅店股份,不再好意思问七伯,威哥主动借过我两万块,我一年多以后才还,因此一直很感激他。我查了查银行卡,还有六万来块,于是去附近的ATM机取了三万出来。马上就没工作了,还是得给自己留一半,我心想。
下午一点多,威哥一脸疲惫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差点没认出来。才几个月而已,三十出头的他,看上去已经很衰老了。那感觉怎么描述呢?大概是过去我熟悉的那种心气儿,本来是一个饱满的球,却被人一钉子扎了下去,一下子就干瘪了。以前他龙骧虎步,步步生威,现在居然畏畏缩缩,佝偻起来。威哥把钱装进一个双肩包,问道,“店里最近还好吗?”
“生意不好做,我们已经把店盘出去了”,我说。
“盘出去也好,也好,以后东山再起”,他沉吟。
“威哥,我想请你和大风在这儿吃个散伙饭,我一周以后,可能就跟我七伯一起去粤城了。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好啊,好啊,不过我最近有点忙,再说,再说。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没聊两句,威哥就仓促告辞,走出门外。
我突然感到一阵不祥,便喊了声,“威哥!”
他转过头来,我说,“记得来吃散伙饭啊!”
这一天我都在魂不守舍中度过,一会儿刷一下手机,看看菀月有没有回邮件,一会儿又想到威哥临走前的样子,觉得实在不对劲。晚上,“南方绝望青年”的群已经沉寂了好多天,突然有人发信息了,是威哥。
“大风,开心,两位兄弟,10天已经过了,我也无房可住了。钱没周转过来,去年到现在,做什么赔什么,北方我已经没本事待了。谢谢你们借我的钱,北漂三剑客看来是要散了。开心,希望你一直开心下去。大风,做新闻别太较真,你力量太小了,该退的时候就退吧。两位,后会有期。”
接着威哥退了群。我和大风错愕不已,之后几天,他微信不回,手机关机,再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威哥看来是跑路了”,大风说。“南方绝望青年”的三人散伙饭,终究没有吃成。
“现在,我们只能报道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欧盟的矛盾,不能报道土耳其和伊朗的经济问题,更别说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了。也不能说什么战,只能说是摩擦。今年四月份,我领导还告诉我们,要把调子定高一点,现在不提了。”
“现在粮食问题,前几天我去找一个粮食专家采访,他直接问,我就是敢说,你们敢发吗?妈的,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开心你走也对啊,留在北方能干什么呢?”
刘大风喝了一大口白酒,说道。
威哥消失以后,大风下班后,每天都来找我喝酒和吐槽,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做经济类的新闻,但又这不能写,那不能碰,备受挫折。
“就这最后一个星期了,到时候你也离开北方,我多蹭你几顿酒喝。”
“你就是舍不得我,南方绝望青年,以后只有你一个人了。”
“不,一个也不剩了。我也在打算辞职,做完这个专题就走,回杭城。威哥说得对,我力量太小了,该退就退吧。”
我想了想,说,“好好活着吧,干杯。”
那晚我们喝高了,但意外的开心起来。而对我来说,这最后的一周也有了莫名其妙的仪式感,但凡有一些熟悉的面孔还来,我都会前去解释,然后赠送一些菜品。大多数员工领了遣散费,也离开了,我因此还承担了许多服务员的工作量。好在客流越来越少,我也突然变得乐在其中。
那个大学法学老师,这两天也和几个他的朋友来了。说来奇怪,当我正要对他说,“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吃我们家火锅”时,他抢着说了句,“明天我就离开了北方,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你们家吃火锅了。”
“啊?你不当大学老师了吗?”我一时语塞。
“在香港找了个教职,明天就走。副教授变讲师,一切从头再来。我之前也犹豫,但想明白了就好,讲真话才叫人。”
那晚我特意留心观察了一下,他们那桌居然没哭,反而笑得很欢快。
我在那一刻突然地感到放松和开心了。
以前老觉得日子漫长,不知何时是头,而最后的日子,说过去就过去了。我做完最后一天店长,锁好门,又走到深夜的望井街头。
八月末的北方,仍然炎热干燥,白天看新闻时,却听说好多地方都在闹洪灾。就要离开北方了,未来会如何,实在未知。但大半年“南方绝望青年”的标签,算是可以拿掉了吧。这两天,七伯也终于把我占股份的钱打给了我,嘱咐我收拾一下,“下周的高铁,一起回粤城。”
我虽已打定主意离开北方,但我也在今晚给七伯打电话,拒绝了他。
原因是前一晚,我终于收到了菀月的回信:
开心,我已经不在北方了。我前段时间太过抑郁,搞不清楚很多事情何以至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戏剧出身,却要为了赚点钱,去做那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前几年,我以为只想着赚钱,适应时代,时代便不会找我的麻烦了,但我还是错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你说,“要下沉,这是时代流行这个”。但我又很敏感,很分裂,所以问你,是否觉得我Low。你真的很宽容,虽然你最喜欢的是读那些无人问津的冷僻小说,但你是很宽容的,我看得到。只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太介意这件事了,所以我才想了个主意,我们发邮件,写我真的觉得有点价值的东西。我很喜欢看你发给我的随笔,那能安慰到我。那时候我总想对你说,你应该去试着做回本行,或者当个作家,而不是开个火锅店,一天又一天。但我哪有资格说你呢?我自己不就是放弃了吗。
我总是告诉你,我是为了挣钱,才不再做话剧,而开始“下沉”,做公众号,做视频,做直播,做网红,因为现在流行这个。我也说过,我曾经为了理想,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我从没告诉你我具体的遭遇。
还是从我的专业说起吧。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两大戏剧节,一个是英国的爱丁堡戏剧节,一个是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那是我们所有戏剧人的圣地。
阿维尼翁戏剧节有IN单元,有OFF单元,IN单元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去演出,日本、韩国都有过作品能在IN单元演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正式被阿维尼翁邀请,能够有去IN剧场演出的机会。
我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OFF演出过,我们演员要自己发宣传单,然后在一个只能坐50人的小剧场,舞台8平米见方的地方演出。IN和OFF单元里作品的巨大差距,我一看便知,但即便如此,在OFF单元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是巨大的成就。
但为了那一次OFF单元的演出,我居然还丢掉了北话的工作。
我那时是北话的演员,按照行内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接外面的话剧。我总是把北话的档期排在第一位,在这之下再去做艺术的突破,那一次就是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准备,我早就把档期告诉了北话,他们也答应了。
可是在我要去法国的前一天,北话突然告诉我,我们要立刻准备去一个中亚国家演出,这是国家的政治任务,事关重大,没有商量的余地,个人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没有答应。使我最终鼓起勇气拒绝北话的,就是阿维尼翁,那对我来说是圣地,我准备了那么久。回来之后,我就被北话封杀了。我抑郁了很久。没有办法,我不能一直消沉下去,只能另谋他途。
这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在我做那么“下沉”的东西时,我想逃避一切有艺术追求的事情。娱乐至死对我来说,不是不可接受的,这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吗?流量啊,下沉啊,打开率啊,用户粘性啊,我都学会了。这些事情,比起艺术来,有什么难度吗?
可是你知道吗?我连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逃避艺术,躲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最终却兜兜转转,还是又和国家撞了个满怀,说起来,好像你也是这样,做记者,开火锅店,都和它迎面撞上了。可它到底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又重新陷入抑郁,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你说“再坚持一下”的时候,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你也没告诉我,那时候你们店也和它深深地打了交道。你要是不写信给我,我可能不知道你和火锅店,这半年都经历了那么多,就像我不曾告诉你一样。
我现在回了理城,前些年有一些不错的收入,因此有了积蓄。我这里有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现在身心状况也好了起来。我正在筹备一个话剧培训班,想做回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热爱的事情。我当时本来想说,你要是能来理城,我们还可以一起开一家店,可以放你喜欢的音乐,这里成本低,不用去下沉了,你还能来这里,读书写作。至少这些都是真实的活着,对吧。
如果我再问你一次,你现在会愿意来吗?
为防失联,请扫码关注备用号:密金融!
【版权声明:本平台致力于寻找金融行业至关重要的文章,以提高全民金融意识,促进金融交流,如涉及文章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或附上稿费。联系方式: 微信号:zmjinrong】
@正版图书,低至六折!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密融书社“@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