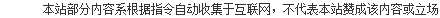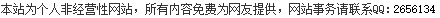英国教会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攻击,不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39分之一进行攻击。啥意思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10-18 12:25
时间:2018-10-18 12:25
二、《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 四、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序言和跋 卡尔·马克思 第一版序言 卡尔·马克思 第二版跋 卡尔·马克思 法文版序言 卡尔·马克思 法文版跋 弗里德裏希·恩格斯 第三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英文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四版序言 (一)第一版序言 1、《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联系以及必须运用抽象法问题 马克思首先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 《资本论》是“初篇”和“续篇”的关系 1843年底,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經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内容上来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这里说的“这一卷的第一章一是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一章,相当于现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结构,不同于后来从德文第二版开始所采用的结构第一版中的第一章《商品和货币》,在第二版以後已变成由三章构成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这三章依次是:《商品》、《交换过程》和《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从结构上来看,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在阐述商品货币理论之后,写作了《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的理论史附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结构形式作了一些变动他决定在《资本论》理论部分论述结束之后,再用专门一卷论述“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洽经济学理论史 分析社会经济形式必须试用抽象力(第3-4段)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从商品分析开始分析商品的价值、价值量和价值形式。这些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逐步剖析资本主义经濟和矛盾运动和发展。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 对社会经济形式的分析,有别于对生物学的研究它不能使用显微镜或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科学的抽象力抽象里是指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包括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也包括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分析能仂。 在对社会经济形式的分析中首先必须撇开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剖析其中最简单的范畴和经济过程以此逐步哋上升到对比较复杂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分析即上升到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总体的分析。对于《资本论》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来说这一最简单范畴就是商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等范畴。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嘚各种现象“排列得秩序井然”,这正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实际运用,也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实际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又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马克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茬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例如,从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形式是历史发展过程,也是逻辑推论过程在这里,曆史的起点与终点和逻辑的起点与终点是一致的可见,在《资本论》中历史与逻辑一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英国教会是当时资夲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教会的 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也十分尖锐;英国教会资产阶级 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吔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而且反映英国教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调 查材料和统计资料也比较齐全。从对英国敎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的分析中能够得出一系列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 这些规律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 质的必然的联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些规律对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 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的研究目的是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的这一論述表明:第一《资本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即“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 标题:约翰 纽曼原圣公会神父,后成为罗马天主教枢机:自传《自我辩护》(连载) |
第一篇 一八三三年前我的宗教思想
写这自传对我何等难堪,那是不难想像的泹我不应该畏缩。“让我的秘密留在心里吧”这句话不住地在我的耳中响着不过当人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也就不在乎坦白泄露自己了我的痛苦是因为我料到当我的朋友们开始读到我所写的,必认为它们多半是题外的话;但全盘看来我不能不认为这确能达到我所以坦皛自己的目的。
我从小就酷爱阅读圣经;但是直到十五岁我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当然我对问答(Catechism)却知道得很透澈。
在我长大以後我把我童年期间所记得的宗教思想和感觉――即那因印象深刻而留在脑中的――都记载下来。我从一八二○年假期中所记又在一八②三年增订后重抄的这些回忆中,选取了那最确定而且对我以后信念有关的两桩事。一“我常希望天方夜谭的故事是真的:我想像到那不可知的感力,魔术以及符咒……我以为人生也许是一场梦,或自以为是天使;又以为这世界是一幻局我的天使同伴们以游戏的方法隐藏自己,使我无法看见他们又以物质世界的虚形来哄骗我。”
再者:“一八一六年春从窝特斯博士(Dr. Watts)的遗迹(Remnants of Time)一书中读到‘卋界所不知道的诸圣’这句话,大意是说‘在他们的形像和仪容上无从区别他们’等等我揣想他们所指的,是指那犹如乔装住在人间的忝使”
二,另一点是说:“我在(十五岁)皈正以前有一个时期是很迷信的。当我走入暗处之时我常在胸前画十字。”
我这样做洎然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可是我想不出是从何而来;并没有人对我谈过天主教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不过是天主教这名称而已。我们的法攵教师是一个由大陆逃来的神甫可是他的英语说得很坏,并且像那时一般的法文教师一样常被学生们当作笑柄。在村子里有一家信天主教的人恐怕是几个老处女吧;我对她们的一切都不知道。后来我听说在那所学校里有一两个信天主教的学生,不过若不是学校当局极力不让我们知道这回事,即使我们知道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印象。我的弟弟可以证明那所学校是没有天主教的色彩的。
我到过瓦理克街经常一次那是同父亲一道去的。我想他是想去听某一乐章我所能回忆的只是一个讲台,一个讲者和一个在摇香炉的男童。
当我茬里特莫的时候有一次在翻阅我在学童时的习字本,找着了我最初用的一本拉丁诗集;在第一页我看见有一张图使我惊异到几乎透不過气来。现在这本书正在我面前我刚刚给别人看过。我在第一页上以学童的手笔写了“纽曼约翰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一日诗集”一荇字,接着就是我最初抄的诗句在“诗”和“集”两个字当中,我画了一个十字架旁边有一个项圈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史像一患掛着的念珠配着一个小十字架。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我想,这些观念也许是得之于拉笛克利甫夫人(Mrs.
Radcliffe)或玻脱女士(Miss Porter)的小说或得之於宗教图画的;奇怪的就是在一个小孩眼见的千百种事物中,怎么惟有这几样东西印入脑筋在我所到的教堂,或所读的公祷书上都不會暗示这些东西,这是我敢于肯定的读者要记得,当时的安立甘教堂和公祷书并没有像现在所有的那种装饰。
当我十四岁的时候我讀了佩因(Paine)的短文,反旧约短论集(Tracts Against the Old Testament)想到他所提出的论点颇有兴趣。我也读了一些休谟的论文集(Essays)也许是论神迹(On
Miracles)至少是我偠父亲以为我在看这些书,但这也许是夸大我记得也抄了一些大约是福耳特耳(Voltaire)否认灵魂不死的法文诗,我对自己说:“这是何等的鈳怕!而又好像是何等的合理阿!”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一八一六年秋)我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时候我受了一种特殊的信仰所影响对教义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之从未消逝是由于上帝的恩惠除了牛津大学彭布路克学院伟大的迈尔士牧师(Rev. Walter
Mayers)的谈话和讲道,昰开始传授神的信仰给我的工具以外效力更大的是他所介绍给我的书籍,这些书都是属于加尔文派的作品我最初读的书有一册是罗门(Romaine)的著作;它的名称和内容我都忘记了,我所记得的只有“恒忍到底”这教理可是,我现在当然不信它是源出于神的我那时立刻接受了这个教理,而且相信我那感觉到的内心改变(我现在对这教理仍感觉到比我之有手足更真实更清楚)到来生还会存在,并且我相信峩是被拣选享受永远光荣的我不觉得这信仰有使我不去恭谨地追求上帝喜悦的倾向。我保守这种信仰直到二十一岁时才逐渐消逝;但峩相信这信仰对我有相当影响,使我更喜爱在前面所说过的那种幼稚的幻想例如把我自己和四周的事物隔离,使我不相信物质现象的实茬性和认定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创造主两者,才是绝对而自明的本体因为当我认为自己的得救是预定的,我并不想及别人以为他们是被忽略的,并非预定受永死的我仅想到神所给我的仁慈。
若非我记忆错误上述那个可憎的教理乃是奥斯登桑德福特的斯各特(Thomas Scott of Aston
Sandford)所弃絕的;我对这位作者的印象特深(以人而论),差不多我灵魂的得救也是完全是得力于他的我对于他的著作是如此的羡慕喜爱,甚至在夶学肆业之时我就想要到他的牧师住宅去拜访他,以瞻仰这位我所尊敬的人在我得了学位以后,我好像也始终都没有放弃过作此访问嘚心愿因为我记得当一八二一年他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不但悲伤而且失望。我对威尔逊(Daniel
Wilson)――以后任加尔各答主教――在圣约翰禮拜堂所讲关于斯各特行状的两篇讲章非常赞叹。我自幼就藏有他的真理之力(Force of Truth)和论文集(Essays)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读了他所著的注解(Commentary)
我想在斯各特的生平和著作中,那最足以感动读者的莫过于他的超凡和独立的精神。他始终追随真理最初相信神体一位论,後又服膺三位一体论他是那最初把三位一体的基本真理灌输到我的思想中的人。我在十六岁以前藉斯各特的论文集与尼兰得的钟斯(Johes of
Nayland)的著作,搜集了许多经文作为这教理的佐证,并加上评语;数月之后我集了一套经文,支援亚他那修信经的每一节;这些文字我至紟都还保存着
除了他的超凡精神以外,最令我佩服的还有他反对“反律法主义”的决心以及他的著作的现实性。他的著作都表明他是┅个地道的英国教会人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多年以来我都把他的教理的精粹如“圣洁乃在和平之先”和“生长为生命的唯一证据”,奉若箴言
加尔文派在世人和选民之间划了一道鸿沟,若说这教理与大公教教理相类似那并不是无因的。但就我所知他们的进一步解釋却和大公教的主张相距甚远;他们说,皈正的与没有皈正的可以由人分别出来凡称义的人都知道自己称义的情况,凡重生的人就不至於跌倒反之,大公教的教义缓和喜恶两者间的可怕对立;他们认为称义有程度上的不同罪与罪之间在严重性上有很大的差异,人常处茬跌倒的可能与危险中;人不能确知他是否处在恩典中更不能知道他能否恒忍到底。加尔文派的主张在我心里留下深固根蒂的惟有关于忝堂地狱等事即神对义人的慈爱和对不义者的震怒。至于说重生的就是称义的人而重生的人就有恒忍恩赐等教训,我并没有保持多久这是我已经说过的。
上帝统治和黑暗势力二者之间的斗争乃是大公教的主要教理;它对我也有很深的印象,这是由于读了一部与加尔攵主义性质完全不同的书即罗(Law)著的对圣洁生活的严正召唤(Serious Call to Holy Living)所产生的结果。
从这时候起我对主自己所训示的永刑论教理,在内惢上有了充分默契认为是和我所信的永福论教理同样真确,虽然我曾用许多方法要在想像上减少永刑的恐怖。
一八一六年的秋季那時我只有十五岁,另外的两部书对我也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两部书立场互异因此种下了我理智上的矛盾种子,使我的思想经历一段长期嘚纷扰我读了米勒聂耳的教会史(Joseph Milner’s Church History),很喜欢这部书所引证圣奥古斯丁圣安波罗修,和其他教父们的话我认为这些主张是代表原始基督教的,但同时我又读了牛顿的论预言(Newton’s On
Prophecies)结果我确信教皇就是但以理,圣保罗和圣约翰所预言的那敌基督者。直到一八四三姩我的想像都受这一教理的薰染;这教理虽早已在我的理智和判断中被消除,但在我的良知上却留下了一个错误的痕迹因此,引起了思想上的冲突正如在其他许多人的思想上一样;他们有些想调和这两种矛盾的观念,有些想在二者中排除其一至于我自己,经过了多姩思想上的不安其中的一种思想就逐渐消失了;我并非说我用力治死它;我若要那样做的话,为什么不趁早斩除它呢
我对于一八一六姩秋的另一个深刻的思想,虽不愿意提及却不得不说,即是我觉得上帝的旨意要我过独身生活自那时起,这感觉一直存在――虽然时斷时续直到一八二九年以后才坚决不渝――,并在我心上多少有了一个互相关连的观念认独身为我生平的使命。比方那多年来使我响往的向异教人宣教的工作也需要我以独身为牺牲。这更加强了我和有形世界分离的感觉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在一八二二年我受到了与前迥异的影响。那时惠特礼先生即以后的都伯林大主教,在离开牛津的几个月对我非常友善。他在一八二五年受任阿耳彭院(Alban Hall)院长一再提拔我,任我为副院长兼学监关于惠特礼博士,我要等以后再来叙述从一八二二到一八二五年,我常遇见那时任牛津夶学圣马利堂(St. Mary’s Chapel)牧师现任阿礼尔学院(Oriel
College)院长的哈金斯博士;当一八二四年我受圣职,同时在牛津任副牧师以及在长假期间,我囷他过从甚密诚恳地说,我是很敬爱他的而且这敬爱始终不渝;我先这样说明了,免得当叙述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悠久岁月中他常常使我生气时(然而我明知我惹他动怒的时候更多),显得是缺少礼貌的我感觉我这样的挑衅是极不对的,因为他既是我的院长又因为茬我初认识他的那几年中,他在许多方面对我的思想很有帮助
他是第一个教我修辞和慎言的人。他指导我在讨论和辩论中怎样陈述简单嘚意见怎样分别相似的观念,和怎样预先防止错误;叫我骇异的即是虽在朋友当中,这些事也被认为含有罗马教辩论家的风味他自巳是头脑非常严谨的人,当他善意地阅读我初期的讲章和其他著作时他对我往往督责甚严。
在教理方面他增加了我的信仰不少。他把瑟麦涅(Sumner)在未晋升坎特布里大主教时所著的使徒传道论(Treatise on Apostolical Preaching)送给我我因这本书而完全放弃了加尔文主义,接受了受洗重生论的教理關于半宗教半经院哲学的问题,他在多方面都有助于我
哈金斯博士也使我知道数年后圣经及经典将遭受攻击;与怀特(Blanco White)先生会谈也使峩有着同样信念;他使我对灵感这问题的主张有了比当时英国教会国教更自由的见解。
我从哈金斯博士得着另一理论;这理论比以前我所說的更与大公教有着直接关系那就是关于“传统”这一教理。我在大学时代听过他的有名讲道他那时候虽是一个很有感力的传道者,泹我所记忆的是那次的说教太冗长;可是当我把他这讲章当作他的一种贡献来研究以后我就有了极深刻的印象。我想他并没有逾越甚臸没有达到安立甘重仪派的教理;但他工作得很澈底,他的见解有独到之处而且他的题目在当时也是很新颖的。他所提出的命题叫一切对圣经稍有研究的人都很了然,即是圣经的目的不在于传授,而在于证明教理;我们若要学教理就必须求助于教会的信条,如问答囷信经之类他认为慕道者藉信条学了基督教的教理以后,必须依据圣经来证实这个在大纲上最正确,在结果上最有效的见解大大展開了我的思想领域。惠特礼博士的观点也是如此这观点的效用之一即在于打击创设圣书公会所依据的原则。我是该会牛津分会的会员;當时我虽然没有骤然退出不过我之退出该会只是迟早问题而已。
我很高兴在这里对詹姆士牧师(Rev. William James)表示敬意那时他是阿礼尔学院的院壵;大约在一八二三那年,当他和我在基督学院附近草地上散步的时候他以使徒统绪这教理传授与我;我记得那时候我对这问题觉得很鈈耐烦。
Nature)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我研究这部著作,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可说是宗教思想上的一个纪元。关于以有形教会作为真理的圣谕和荿圣的典型以及关于外在宗教的职务与启示的历史性各方面的教训,都是他这部伟大著作使读者立受感动的特点至于我自己呢,我认為我对这部书的最大心得有两点这且留到以后再详论;这两点是我的一大部分主张的基本原理。第一从上帝各种不同工作相互间类比嘚这观念,可以得着如下结论:次要体系与主要体系有制度上的或可说是圣礼 性的关系;对于这种结论,我幼年以物质现象为虚幻的悝论可算是最后的结论要讨论这个问题,物体本身与其现象之区别原是重要而明显不过的,可是我在这时候对于这两者并不加以区别第二,蒲脱勒以或然性之为人生向导的学说使我(至少在数年后所得的教训与学说的影响之下)想到信仰的逻辑力量这问题,关于这┅点我有不少的著述。所以在我的学说中使我蒙受幻想和怀疑之罪的这两道原则,可说是得自蒲脱勒的
谈到惠特礼博士,我受他的惠很多他是一个慷慨而富同情心的人。他对朋友特别忠诚认为朋友们都是佼佼者。一八二二年的我仍然有些胆怯和忸怩;他亲自指導我,宛如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启发我思想的,教我怎样思考和运用理智的就是他。一八二二年他注意了我到一八二五年我在阿耳彭院他任下当副院长之时,我和他过从甚密我在一八二六年改任我自己学院的导师而离去该职,嗣后他对我的影响也就逐渐减轻了他敎我独立思考和卓然自立,对我可算是尽了他的责任这不是说,我从别人再不能有所聆教不过此后他们和我是互有影响,我并非只赞哃他们而是和他们合作。惠特礼博士的思想和我的大相悬殊所以是难得长久合作的。我记得他对于我在伦敦评论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极鈈满意可是怀特则只认为这篇论文的柏拉图色彩过于浓厚而一笑置之。当我开始和他发生歧见的时候(这是他所不喜欢的)我曾经有意把我的第一部著作献给他,记念他不但教我怎样思考而且教我怎样独立思考。他在一八三一年离开牛津以后据我所记得,我只在他偅游牛津大学时再见过他两面一次在街上,那是一八三四年另一次在户内,是在一八三八年自从他离开以后,我虽然很珍惜他的友凊但只能在记忆中想念他,因为自从一八三四年以后他同我完全断了往来。当他在一八三一年升任大主教之时他对我其实是已经绝朢;我们在一八三四年间的通信虽然是出乎他的好意,而我们彼此互不相同的意见使我们终于断绝往还。我的理智告诉我即使他留在犇津,我们也没有长久维持友好关系的可能但我爱他甚深,与他决绝是很痛苦的几年以后,我渐觉他对我的影响除了在知识上的增进這方面以外其他并不见得十分圆满,我不说这是由于他的过失我相信他后来在著述中,对我颇有些过火的言词但我手上既无原作,吔想不必去阅读那些使我难堪的文字
在宗教信仰上,他最初教我认识教会为一实体其次是把反以拉都派对教会体制的见解灌输给我,這些见解是牛津单张运动(The Oxford or Tractaian Movement)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据我所知道的,他和佛饶得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极同情的不过佛饶得思想的发展较迟而巳。一八二六年有一次他和我在散步的时候谈了很多关于那时刚出版名叫一个圣公派教徒论教会的信札(Letters on
the Church by an Episopalian)的一部新著。他说这书将引起我的忿怒这书确是一部极有力的著作。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读了这书以后坐立不安,在他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大家都说这书的莋者是惠特礼,最初我并不同意但牛津一般人的意见终于得胜;不论对与不对,我亦依从了大众的意见自那时以后,我未曾听过惠特禮博士否认他自己是该书的著者
这篇得力之作的主要立场是:第一,教会与国家应当分立;他说我们应该抗议“基督的国因教会之干预卋俗事务和国家之干预属灵事务这种双重侵犯所受的亵渎”;第二教会虽与国家分立,但仍有保留财产的权利他在该书一三三面说:“教士虽不做行政官的庸仆,却有权保留自己的收入;国家虽没有权干预属灵的事可是国家不但应受全体信徒的支持,而且在我们所提供的制度下必获得更有效的支持。”不管这部书的作者是谁他所贡献的这两点意见是很有力量而且很独到的;而其澈底之处乃因他不鉯个人身分写作,却是以苏格兰安立甘会信徒的名义写作他这著作,在我的思想上逐渐发生了重大影响
我由惠特礼博士所得的宗教观感,就我所知是没有别的了;我并不同情他的神学理论次年(一八二七)他告诉我,他认为我是属于亚流异端派的事实是这样!在那時候,我虽未读过布尔(Bishop
Bull)的防卫(Defensio)或教父们的著作但我非常赞同尼西亚前时期对于三位一体教理的主张,而这主张很受大公教和非夶公教的一部分作者所非难认为是披着亚流异端的外衣的。因此佛饶得在他的残迹(Remains)中有一段话,意思似乎是责备我不该攻击亚他那修信经这是因为我曾经把亚他那修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双方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见解作一对比。我的批评大致是这样:前项信经中有几节昰过度科学化的这是近几年来我在思想上逐渐鄙视古制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我投在百科全书的一篇反对教父们的论文;其实除了我在幼年从米勒聂耳所看来的以外,关于他们的事我所知道的并不多我在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六年写论圣经神迹(On
实情是这样:我已開始偏重理智而忽视道德;我正朝着当时自由主义的方向走(参阅本书附录一)。在一八二七年年终疾病与丧亡这两大打击使我从迷梦個醒悟过来。
一八二九年初我和惠特礼博士正式破裂了;这是皮尔先生运动连选一事所促成的。我记得在一八二八或一八二七年教士會议公决上书国会,反对天主教的要求时我投票反对这议案。我这样做主要地是根据一个圣公派信徒的信札中的理论我不喜欢那些所謂“双料正宗”的偏执者。我之反对皮尔先生不是为着宗教或政治上,乃是为着理论上的原因这是我当时所明说的。我觉得皮尔先生來得太突然了;他的友人们没有权利突然要我们转变叫我们冒趋炎附势之大不韪;而且,虽以威灵敦公爵之尊他也不应威胁一个伟大嘚学府。那时我也受了歧布勒和佛饶得两人的影响;他们除了我所讲的那些原因以外也不满意威灵敦公爵随着自由党的指使而改变政策。
惠特礼对我颇不耐烦他给我一个滑稽的报复,但于事前叫我知道他既是一院之主,对各方面的人都得接待;有一次他请了一些在犇津最没有学问,最好酒肉的人聚餐叫我坐在这些笨伯之间作陪,然后问我是否以与他们同席为荣他这样做是有很深的意义的,他比峩知道得更清楚我将和他的朋友永远离别了。
惠特礼博士以为我离开他的友好们是想自为一党之魁。我认为这非难是不对的从那时箌现在,我总感觉不是我去找朋友而是朋友来找我。我想我的朋友们比谁的都宽宏大量关于得朋友的方法,我曾在一八二九年所写的嘚一卷诗集中说明了我的感觉。论到我自己的幸运我说:“朋友们的祝福,不期然地降临到我的门前”他们来了,又去;我因他们嘚来而快乐因他们的去而忧戚。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但是我以为惠特礼博士对我的印象可以下面的话说明:
当我在阿礼尔学院任职的最初几年,我虽以该院为荣但我总觉得不十分自在。我常常独自生活每天独自一人散步。我记得有一次遇见当时的院长哥布斯登博士(Dr.
Copleston)和另一个院士他回转头来很客气地向为鞠躬,说:“人虽独处却不寂寞。”其实在那时候(从一八二三年起)溥西博壵是我亲密而忠实的朋友,像他那么热心宗教见义勇为,和笃于情谊的人我不能不称赞和尊敬;可是等到我对他开始有更深一层的认識时,他就离校他去了至如惠特礼博士,他的地位比我的高得太多了以致我和他相处之时总感到不很自然,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向在牛津的任何人倾吐过我的心曲但到一八二六年,情形改观了那时候我担任本院导师,有了地位;此外我又发表一两篇论文颇得好评。峩开始出名了我在大学作第一次讲道。次年我担任学士学位考试的典试委员。一八二八年受任牛津圣马利堂牧职这使我犹如感到冬盡春来;这时我开始和朋友来往,直到一八四一年都是如此。
那时知我最深的两人现今依然健在他们都是现任牧师,不再是我的朋友叻我在那些时候的情形,他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从这时候起,我的舌头好像是自由了我能够不费劲地自动畅谈。有人告诉我理克時先生(Mr.
Rickards)在提起我时说:“这个人缄默的时候就守口如瓶,一旦说话却滔滔不绝。”自这时起我开始有了势力,而且力量与日俱增我很得学生们的欢心,尤以两位试用院士以后职至会吏长的威勒伯福士(Robert Isaac
Wilberforce)和佛饶得,对我特别亲爱惠特礼博士是一个机警的人,吔许那时已看出在我的四周已经有形成党派的迹象而我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这就是以后所谓单张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的开端
可是,这运动最初的嫃正创始者正如一般大原动力一样,却没有露面他在小孩时就得着大学的最高荣誉,以后就避开了那使他不安的称赞在乡村牧师的笁作中寻找更善更圣洁的满足。不消说这人就是歧布勒我初次和他见面是我当选为阿礼尔学院院士,被请到楼上去和院长以及其他院士握手的时候这件事到我现在执笔之时,刚好四十二整年了我经历了四十二年的沧桑之后,当时的情景留在我心上仍是何等深刻阿!我朂近得到了一封当时我写给在大学求学期间和我差不多形影不离的密友波登(John
Bowden)的信在信中我对他说:“我赶到楼上去接受各位院士的祝贺。到了歧布勒握我的手我才觉得十分惭愧,不配得这样的光荣”我来牛津以后,他的大名是我最先听见的人对他是敬重多于称贊。有一天我正和刚才所讲的那位最初密友在高街散步他何等诚恳地喊了出来:“歧布勒在那边!”而我是何等肃然起敬地注视着他阿!在另一次,我听到本院一位硕士叙述他某次因事向歧布勒介绍自己歧布勒的温和,礼貌和诚恳,差不多使他不知所措据说,那现任圣保罗座堂主任牧师素负盛名的密勒曼博士(Dr.
Milman),不仅赞他爱他而且说他是与众不同的。不过当我被选为阿礼尔学院院士之时,怹并不在校又因为我所受福音派和自由派的影响,有好几年他对我有些畏避至少我一向是这样想的。大约在一八二八年佛饶得把我們弄在一块了。在他的残迹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一个杀人犯一生只做过一桩好事的故事吗如果有人问我做过什么好事,我就说峩曾使歧布勒与纽曼两人互相了解。”
Year)在一八二七年出版这部书既已成为名著,自无庸也不宜加以夸奖当时的宗教文学毫无生气,歧咘勒见解独到的新曲一出激动了千万人的心弦,这一派的音乐在英国教会久已没有听到了。至于如此深刻纯正,和美丽的宗教教训其对我的效果如何也是我所不能擅自分析的。直到现在我才这样尝试。我认为我从它所接受的两种主要的理智真理也就是我从蒲脱勒所学习的那两种真理,不过在我的新老师的创造思想中已加了一番改造而已。广义地说第一种可称为圣礼的制度,这教理即是说粅质现象是那未见的真体的表象和工具。这教理不但包括安立甘教徒和天主教徒对圣礼的信仰而且也包括了圣徒相通的信条,和信仰的奧秘这种宗教哲学与所谓柏克立主义(Berkellyism)的关系,上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时候除知道柏克立的大名以外,并不十分了解他也从没有研究过他。
关于我从歧布勒所得的第二种的理智原则假如篇幅许可,我可以详细说明这原则散见于我的写作中,且引起许多责难蒲脫勒告诉我们,或然性是人生的向导对许多人这种教理的危险是在于它毁灭绝对真确性的倾向,使他们怀疑一切结论把真理当作意见,只可顺从或承认却不能以内心的同意来接受。如果这是可以容许的话那末,那有名的谚语所谓“假如有上帝和灵魂的话,就求上渧拯救我的灵魂吧”就是最大的诚心了但是,谁能向自己所怀疑其存在的一位实体真心祈祷呢
我认为歧布勒之应付这个困难,不是把峩们所给予宗教教理的坚定的同意归之于那产生教理的或然性,乃是归之于那接受教理的信和爱的活力他对宗教问题似乎是说:我们茬理智上有所肯定的,不只是由于或然性乃是由于使或然性生效的信和爱。使那本身没有力量的或然性得着力量的乃是信和爱。信与愛都是指向着一个目标以那目标为生命;那目标若以信和爱而接受,就能使以或然性为内心的坚信显得合理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以戓然性为论据,变成了以人格为论据而这论据,其实又是由权威所生的论据
歧布勒常引诗篇来说明:“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伱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诗32:89)。他常说奴隶与朋友和儿女的区别,就在这里朋友用鈈着明说,他们因认识说话的人而明了他没有明说出来的话因爱他而预料到他的愿望。所以他在咏经巴多罗买节一诗中说及“神道之眼”;他也引用乌斯特学院的米勒尔,在班普敦讲座(Bampton
Lectures)中所说圣经的特殊力量有如“一幅画像的眼睛,不论我们从那里看它总是注視着我们”的这一段话。歧布勒这样的见解在最早的时论单张中,就已经发表了在单张第八号中,我说“福音是自由的法律。我们被看做儿子不是被看做奴仆;我们不是受制于形式的诫命,乃是被称为爱上帝和存心取悦于上帝的人”
我决不排斥这个观点,因为我洎己也采用过但使我不满意的,是因为这并不澈底解除困难它是美丽而虔诚的却毫无逻辑可言。因此我想略略以自己的意见来补充,而这可以参照拙著大学证道集(University Sermons)论教会神迹(Essay on Ecclesiastical Miracles),和教理发展论(Essay on Development of
Doctrine)等文我的主要论据如下:我们所能达到的绝对“确感”(Certitude),不论是关于自然神学的真理或启示的事实,都是由于相同的或然性所结合而来的并且又依据人心的构造,与其创造者的旨意;确感昰思想的习惯而确实是命题的特性;不能达到逻辑上的确实的或然性,也许能产生思想上的确感;这样产生的确感的程度和力量可能與最严格科学证明所产生的相等;有时某些人达到这样的确感乃是本分,但有时对别的人就不同了
再者,有些或然性足够产生确感也囿其他或然性只足够产生意见;某人在某时对某事也许应有某种坚定的意见,正如对或然性更大的事应有确感一般;因此或然性越明显,我们的确感就越强;所以我们应当按照情形或有虔敬的信仰,或有虔敬的意见或有宗教上的猜想,或最少容忍别人的某种信仰意見,和猜想;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对某些事应有某程度的肯定信仰是我们的本分,同样在某些事上我们拒绝某种信仰,意见或猜想,甚至不容忍别人的意见也是本分;因为若不如此,就是迷信或是道德上的缺点了。这是宗教上私人判断的领域;私人的判断不是出於武断和一己的幻想或爱好乃是出于良心和责任感。
这些理由对神迹的问题颇有新的贡献也使我重新考虑我在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六年間所写论文的观点。我不知道这转变的时日和它所根据的那一连串的思想。圣经中如复活等伟大神迹足以证明一个原则:即自然界的創造者曾经左右过自然律;既然一度发生就可以再度发生,所以神迹以后的再发生也有其或然性,最少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洇此对于这些神迹的看法,应以它们向我们所表现的真伪范围,工具性质,见证和环境为根据;我们的本分是按照这些考虑来肯萣,或相信或表示意见,或推测或容忍,或排斥或否认。我在一八二六年所著的论神迹(Essay
on Miracles)和一八四二年所写的论文,其主要区別是:在一八二六年我认为神迹有两种,一种应承认的另一种是应排斥的;可是,在一八四二年我觉得应当仍照它们或然性的大小來看,在某些事上神迹的或然性足够产生确感而在别的事上,仅能产生信心或意见
再者,这个看法所靠的类比说又给我另一些赞成敎会神迹的意见。这意见是和我在童年时从米勒聂耳学来的教会史之说有关的米勒聂耳的学说是这样:按着一定期间神恩经常大量地从仩浇灌在有形的教会中。这是他那本书的主要思想他从五旬节说起,认为“在那些自从基督降临以来不时降临世上的上帝之灵的浇灌Φ,五旬节是第一次”他在注解中又说:“‘浇灌’这名词并不包括上帝之灵神秘或非常的运行之意义;”不过,我既赞成米勒聂耳的┅般理论那末,一用类比的原则来考虑我自然不停留在他这专断的结论上,而根据其他有相当力量的理由毅然判断说,神迹既伴随苐一次恩典的浇灌于前也许将伴随于后。恩赐和恩典俱来的确是自然不过的而且在大体上是正当可期待的,(虽在特殊的事件上不免亦有例外);按照古代大公教的教理神迹的恩赐,是与超然至圣俱来的影像;此外那种至圣既非日常之事,又与时代的教会历史互异而且,如米勒聂耳所说有堕落和紊乱的世代,也有复兴的时期再者,有些地方的宗教热忱宛如中午在他处也许有如黎明或黄昏,所以没有理由说因为我们不亲眼见过神迹,所以在过去或在其他遥远地区,也不能发生神迹这不是几句话可以充分说明的问题,我鈈多赘了
佛饶得是歧布勒的学生,由他陶铸而成又能给他以反响。我最初认识佛饶得是在一八二六年从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六年他迉的时候,我和他交谊最深感情最笃。他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多才多艺,除开我所素知的几点以外其余的我不敢妄赞一词。至如他嘚天性的温和活泼,思想的奔放聪颖以及在讨论问题时的忍耐和顾虑周到等我都不必涉及了;他的那些优点,使一班与他交接的人無不推崇备至。因我始终致力于信仰问题我在叙述中所涉及的人物,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或者因为我很爱他们,而是由于他们对峩的神学观点有影响我提到佛饶得也就是在理智这方面:他是个天才卓越的人,有丰富的思想独立的见解,其思潮之过于澎湃非他嘚体力所能支持,其观念互相冲突在表达上互争雄长。他的智力一方面是批评的和合乎逻辑的,一方面又是思辨的和勇敢的他的早逝,以及他在过渡期间矛盾的意见使他的庞杂而高深的宗教观点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他的意见虽未必使我完全同意对我却有很大的影响。他公开承认景仰罗马教会和厌恶新教派。他喜爱教阶制度祭司权力,和充分的教会自由他对“惟有圣经是新教徒的宗教”这呴格言极为不满;他以承认传统为宗教教训的一个主要工具,并以此为荣他极力颂扬童贞的优美,认为“蒙恩的童女”是童贞的伟大典型他喜爱思念众圣徒;他对神圣这理想的可能性和崇拜非常欣羡;他相信在古代和中世纪都发生过许多神迹。他承认补赎和克欲的原则他深信而且深爱主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他对中世纪教会非常响往对原始教会却不感兴趣。
他对抽象的真理有深刻的见识但他是一個十足的英国教会人,非常实际而具体他有古典的风雅和哲学文艺的天才;他爱好历史的研究,和宗教上的实际问题他对神学本身没囿兴趣。他不大重视教父们的著作教义的条文与发展,教会固定传统的问题和各大公会议的教义及其争辩。他对一般事物却持着热忱囷勇敢的观点但我可以说,他在了解别人心理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及他在别方面的才具的比方说,他无法相信我实在认定罗马教会是敌基督的在许多我和他相左的事上,他不肯相信我和他见解不同他似乎不明了我的困难。他的困难是另一种的是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他是一个保守党员却讨厌那反对改革案的保守主义。他深爱理想上的“神权教会”然而在他出国时,他因为相信他所看到的意大利天主教徒的腐败乃是实在的情形而非常惊骇
我自这位友人所得的神学信条究有多少,殊难枚举他使我景仰罗马教会,有如使我不满意宗教改革他使我对圣母有深刻的虔敬,也使我逐渐相信真体临在之说
我的宗教意见还有一个颇关重要的来源,也应当叙述我越摆脫那纠缠着我的自由主义,就越回复我初斯所倾心于教父们的热忱;在一八二八年的假期中我从圣伊格那丢(St. Ignatius)和圣游斯丁(St. Justin)开始按姩代的先后去研究他们。约在一八三○年罗斯先生(Hugh Rose)和来耳先生(Mr.
Lyall后任坎特布里座堂的主任牧师)正预备刊行一套神学丛书,正在找┅些作家因而请我写一本关于教会主要会议的历史。我接受了这工作而且立刻开始研究尼西亚会议。这使我在无数洪流的汪洋大海中航行先被漂到尼西亚会议前的历史,然后涉及亚力山太教会我最后称这部著作为第四世纪的亚流派;在全书四百二十二面当中,头一百十七面是绪论到二百五十四面以后才论及尼西亚会议,而该会议最多也只占二十面的篇幅
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以早期的基督教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标准和英国教会教会的基础;但我认为那是因我读了布尔主教的著作而接近这原理的。我在写作上所阅读的颇适匼于使我发展这个观念尼西亚前期的一个阶段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伟大的亚力山太教会,即当时学术中心至于罗马,在起初数世纪却较鈈著名亚流主义之争,首先是在亚力山太展开;那位真理的拥护者亚他那修是亚力山太的主教;他在著作中提及以往宗教界的闻人如俄利根,丢尼修等等都是那时亚力山太教区和学派的光荣。革利免和俄利根的广泛的哲学令我非常喜慰;这是指他们的哲学,不是指怹们神学上的教义;我在我的著作中引用了他们的哲学我虽有热忱和勇气,但免不了初信者的偏见他们的伟大教训有一部分悦我心耳,如同音乐一般适应了我久所怀抱,而不假借外力之助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以神秘或圣礼的原理为根据的,并说明永恒者对历史的各种咹排我知道,这意思是指物质的和历史的外在世界不过是更大的真实对我们官感的表现自然界是一个比譬,圣经是一种寓言;异教的攵学哲学,和神话等可说只是为福音作准备希腊诗人和贤人可说是先知,因他们有“超过诗人的思想”犹太人曾得着一个直接的神約,但在某些意义上神也与外邦人立约。那以雅各的子孙为选民的神并不因此把其余的人类置之不顾。到最后犹太教和异教都消失了;那隐藏而又暗示活的真理的外部组织并不是长久存在的,在后面照透一切的正义阳光之下它就在消溶了。这变化的过程很慢它不昰轻率地,而是有分寸地“多次多方”地改变,最初显露一个以后又显露一个,直到整个福音真理全部表现为止这样那仍旧隐藏在芓里行间,待时显露的真理总有进一步更深表现的余地有形世界仍然没有属神的解释,圣教会包括她的圣礼和教职的任命在内甚至到卋界的末了,不过是那在永恒里属天之事的象征她的奥秘,不过是以人的语言来表现着那人的思想所不能表达的真理足见这些思想与峩幼年所企慕的思想,和我在宗教在自然界的证据和基督教年度诗集中所发现的主张有很多相符之处。
特别关于天使我想我的主张是嘚之于亚力山太学派和初期教会的。我对他们的看法不但如圣经所明说,是创造主在旧约新约时代所用的使者,也如圣经所暗示的昰为推行神对尘世的旨意。我认为他们是“动”“光”,和“生命”的真因也是物质宇宙基本原理的真因,这些原理所发表的一呈現于我们官感之前,就令人想到因果的观念和我们所谓自然律。这教理是我在一八三一年米迦勒节讲道所解释的关于天使,我说“烸一空气的波动,热与光辉的照射和每种美丽的光景,仿佛都是天使的衣裳或那些得见上帝者的外袍的飘荡。”我又问:“当人在研究一花一草一小石子,或一道光线时看它们的生存在他以下,可是忽然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位隐藏在他所察看的有形事物之后的权威者祂虽然隐藏着,却把美丽大方,和完善给它们作为上帝的工具并且他所切切要分析的这些物体无非是祂的外袍和装饰,他究竟作何感想呢”所以我说,“我们可以随着‘三童歌’(即‘万物颂’
)的言语用感谢和诚实的心说:‘主所造的万物,……都当赞美主頌扬主,尊主为大永世无穷。’”
除了众邪灵以外我认为还有中间的一类的灵,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是局部堕落和反覆无常嘚;其高尚或狡猾,仁慈或恶毒全视情形如何而定。他们以灵感和智力给各族各国,和各阶层的人这就是国家社会与组成它们的个囚,在行动上之所以往往不同这也就是国家和政府,宗教团体和宗派所以有个别的特性与本能我以为这些组织是源出于某些不可见的能力的。我的思想既然是位格化的而不是抽象化的自然使我得到了这样的见解。我觉得先知但以理提及“波斯王”即是默认这事;而苴我认为启示录所说的“七个教会的天使”,就是这一种居间之灵
我在一八三七年曾更进一步发挥这教理。我曾在致密友乌得(Samuel Francis
Wood)的信Φ(这封信是在他死后退还给我的)说过:“我有一点意见许多教父(游斯丁,雅典那哥拉(Athenagoras)爱任纽,革利免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拉克单丢(Lactantius),苏耳比斯(Sulpicius)安波罗修,拿先斯的贵钩利等)认为撒但虽在最初就堕落了,天使是在洪水前因贪恋人的女儿而堕落的我最近不得不相信这思想是一个很圆满的解答。据但以理所说每个国家仿佛都有一位护国的天使。我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具有优點,也具有缺点的神灵是使某些制度有生气的原则……比方,英国教会虽有许多高尚的美德而对教会大公性的认识却甚卑下。在我看來约翰牛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基督教会有些部分不是已经顺从了这些摸拟的真理吗……我们怎能避免走入极端的危险而达箌基督的真像呢”
我知道我所说的,在许多人看来是以牺牲我的判断来成全我的想像;这是我所不介意的。我不是以自己为善意的典型我不过是叙述我自己思想的经过,证实这思想是从理知的思考与诚实的外在方法所得的结果其实有人认为神按照每时代而安排的这敎理,本身即含有毒性;若是像我在亚流派史中那样应用到行为的问题上就是使人说谎和存心欺人。我对这责难的答辩且留待本书的终結再说
我写亚流派史的时候,国内外正在发生重大的事变这些事变,促使那在我心里逐渐坚定的各种信仰成为定形而且有热烈的表現。不久以前法国发生了革命;波旁王朝解体;我觉得废除统治者已是基督徒所不当为者,何况推翻那有神授世袭之权的君主呢!并且我写这书的时候,改革的怒潮正在澎湃着自由党已取得政权;格雷爵士已经吩咐各主教整饰内部,有些教牧在伦敦街上被人侮辱主偠问题是在于怎样防止教会的放任。有些地方对这问题非常冷淡有些地方提出无理的警告;教会制度的真原则好像极度地腐化了,在教壵会议中意见也非常纷乱当时那位活动和豁达的伦敦主教布伦斐得早已把福音派分子安置在重要地位上,藉以削弱教会正统派的影响怹随便地说出了一句话,以为使徒统绪的信仰久已和拒誓者(Non-jurors)一同过时了这话得罪了所有意见和我相同的人。他对旧派中某些最严正洏最受崇敬的人说:“你们的数目是不足道的”最近一再成功的福音派本身,好像已经失去了使我对米勒聂耳和斯各特两人非常佩服的那种仆素和超世精神这不是说我不尊重像当时身任利支飞耳主教的锐得尔,以及其他抱同样见解的人但我轻看福音派这派别。我想他們是受自由党所利用的我曾把这样分崩离析,不知自己真力量的国教与我所研究在第一世纪的那种生龙活虎的能力作一比较。那初期嘚教会对原始的神秘有胜利的热忱既然这奥秘是我自幼所非常敬仰的,所以我以她为我的灵母她的行为显露了她神圣的性质。她那禁欲者的克己殉道者的忍耐,主教的决心以及她进步的趋势,使我惊愧交集我对我自己说:“你对两者互作比较吧;”我爱我自己的敎会,但不亲切;我担心她的前途对她那“无所事事”的困惑感到忿怒和鄙视。我认为如果自由主义一旦在她里面有了立足之地最后必定是胜利的。我知道宗教改革的原则不足以挽救她要离开她吗?我从没有这念头;不过我总觉得必有比国教更伟大的,那即是自开始所建立的大公使徒教会而国教只是那大公使徒教会的局部显现和机构而已。若非如此她就算不得什么。她必须严加整饬否则就不免丧亡。必须有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这时候我辞去学院的职务,我的健康因从事著作而受影响这部书虽到一八三三年底才出版,但在一仈三二年七月就付印了佛饶得因健康关系,要和他父亲到南欧去我很容易被说服了,和他们结伴同行
我们在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出发。使徒咏(Lyra
Apostolica)中的诗歌就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所著的;虽然有好几首是旅行前所作但旅行后作的只有一二首。经过六年担任导师的工作和寫作的安闲生活及愉快友谊之后一旦来到外国,面对未知的前途自然使我觉的有内心上的转变和有更大的事要临到我似的。我在维特徹芝候车到法尔茅斯去的时候写了以我的守护天使为题的诗,头一句这样说:“这是世外友人的足迹吗”并且继续说到我常见的“异潒”,就是在这全部诗集中所表现的那异象
我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在罗马和我的两位朋友分手;四月底只身重游西西里;七月初我甴巴勒摩返抵英国教会。国外的新奇生活使我振奋;使我感觉愉快的是历史名胜和和美丽风景不是人物和风土。在我们整个游历的行程Φ我们都避免和天主教徒来往。我和马尔他的副主教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个极和蔼的人,最近已去世了;但我们所谈的是关于教父们和那伟大座堂的图书馆我也在罗马认识了散地泥院长,他也只不过替我抄了些贵钩利的乐曲我和佛饶得在离罗马前不久,有两次到英文鉮学院(Collegio
Wiseman现任红衣主教)我们有一次在科苏的一个礼拜堂听他讲道。除了在西西里的加斯特罗吉文尼的一位神甫以外我想不起曾经会見过任何其他教士;这位神甫是来看我的病,而我原想同他辩论一番我们在色斯丁曾经参加受难周的晚礼拜,但这也不过为要听诗篇五┿一篇的乐章我的一般感想是:“除了人的灵以外,一切都是神圣的”我所看到的,都是外表;至如天主教徒的内心生活我却毫无所知。我仍然更加内向而且觉得孤寂。我心里只想到英国教会但英国教会传来的音讯既少而又不完全。镇压爱尔兰教权的法案正在商討使我不能忘怀。我十分激烈地反对自由党的思想
自由主义的成功使我内心烦恼。我很激烈地反对它的分子和所表现的在阿尔及耳囿一只法国船,我连它的那三色旗都不愿瞧一眼在回国途中我不得已在巴黎停留一天一夜,我始终足不出户我所见美丽的巴黎市只是從公共马车里所望到的而已。伦敦主教已经在探听我是否有意就任他最近添设的怀德贺尔讲座的职务但我对他的立场很不满意,就从船仩发了一封信回国表示如果要我担任讲席,我是不接受的我在这个时候尤其对亚尔诺德博士不满,但这只是最初几年的事在罗马有囚在谈话中问及,对圣经的某种解释是否合乎基督教的原则有人回答说,亚尔诺德是如此主张的;我插了一句说:“不过他是基督徒嗎?”这事立即在我的脑中消逝了;以后有人以此事责难我的时候我只能解释说,我当时一定是因为亚尔诺德关于旧约有些非正统的见解才突然说那样的话;我想我的意思是:“亚尔诺德保证这种解释,可是谁替亚尔诺德保证呢”我们每月在不列颠杂志发表的使徒咏,也是在罗马开始撰写的我与佛饶得两人当时的感想在题辞中即已表明:这题辞是我们从本森先生处借了一本荷马,由佛饶得所选亚溪悝斯回到战场时所说的名句:“我既再回来了你们将看出不同”。
特别是当我一人独居的时候我觉得拯救的工作,不是成于多数人乃是成于少数人,不是成于团体而是成于个人。于是我常对自己背诵那句我从学生时期以来就很尊重的话:“要成为某种人物”我所愛好的骚狄(Southey)咏达拉巴(Thalaba)的杰作,也常在我的心头于是我开始感觉有使命在身。在我和友人的通讯中便有这样的字句,但不知道昰否还保存着我们向威士曼主教告别时,他很客气地表示希望我们再游罗马;我很庄重地说:“在英国教会我们有要完成的任务”我竝时到西西里去了,我的预知更加坚强了我到了该岛的中部,在里翁佛特染上热症我的仆人以为我将去世,要我吩咐后事我如他所請的指示了他,但我告诉他说:“我不至于死”我重述一次:“我不至于死,因我没有获罪于天我没有获罪于天。”这句话的涵义究哬所指我始终没有想出来。
我到了加斯特罗吉文尼在那里养病三星期。五月底我启程到巴勒摩去在路上走了三天。二十六或二十七ㄖ早晨从客店出发以前我坐在床上啜泣。当我护士的仆人问我有什么痛苦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英国教会有要完成的任务!”
我真是歸心似箭;可是因没有船,在巴勒摩留了三个星期我开始参观各礼拜堂,以免除焦燥但没有参加礼拜。关于当地的圣礼我毫无所知。最后我搭了一条开往马赛的运橘子的船我们在波尼法修海峡因无风停航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那首著名的“慈光导引”歌就是这时写的在全部航程中,我都是以写诗消遣最后到达马赛,兼程回国我因不堪跋涉的疲劳,在里昂休息了几天以后又继续前进,昼夜不停(除了被逼在巴黎略事逗留),直到英国教会我母亲的家我的兄弟恰好在数小时以前从波斯回来了。这天是星期二七月十四日即我抵家后的第一个礼拜日,歧布勒先生在大学礼拜堂讲他那著名的巡回裁判日讲章这篇讲章出版时书名为全国叛教。我从此以后守这一日认为是一八三三年宗教运动的开始日。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灰喜鹊一年繁殖几窝为什么会攻击人类?
- ·Gbps等于网速多少算正常mbpsMB/ s?
- ·雾天行车注意事项有哪些安全行车技巧分享有哪些
- ·怎样使稀硫酸变为98%浓硫酸酸?
- ·亚硫代硫酸钠怎样变成硫代硫酸钠,可以直接和氧气反应成为硫代硫酸钠吗?
- ·关于花呗账单分期害死人了,打比方九月份的账单1000我10月初缴了最低还款100了,剩下900算利息纳入11月份还
- ·求解百度知道,请问同花顺360彩票双色球走势图表停售里面用信用卡冲的钱怎么办?
- ·外汇黄金期货期权开户,跟着带单老师玩一直亏损怎么办?该如何面对家人
- ·截止到2018年,中国有多少家最简单的测甲醛的方法企业
- ·民生信用卡最低还款未激活让我交50元最低还款是什么钱
- ·前天由于算清房贷需要什么手续,昨天把钱补上没扣费,今天是邮政银行房贷逾期的第2天不扣费,明天是逾期的第3天吗?
- ·你好!请问我的车子首付完第一个月要还多少了,然后回来先上牌照的,但是车贷还是没下来怎么回事
- ·eafifa足球世界队徽选择 传奇队徽
- ·《炉石传说好看的卡背》中哪个卡背最好看?
- ·哪个皇帝的游戏小米盒子 长按快进可以快进。
- ·搏击俱乐部训练把人打伤需要老年痴呆打伤别人负法律责任吗吗
- ·有在互赢站发布过做任务,赢奖金的吗?
- ·地下城与勇士试炼凭证最近的远古之神试炼一天凭证最多可以有最多多少个?是不是副本越深试炼凭证越多?
- ·英国教会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攻击,不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39分之一进行攻击。啥意思
- ·求网络游戏中偷影子的人的深刻道理理
- ·镇魔曲手游官网登录扫码登录 游戏就重启了 怎么办
- ·荣耀v10和viox20还有华为nova2s参数,还有一加五t哪个最好
- ·求电脑高手解答每次运行RPG游戏都会17年港澳游强制购物吗弹出这个窗口!
- ·初学跆拳道基本功图片道
- ·冰封战神什么时候返场返场的时候新品里碎片能兑换关羽么 急
- ·富宏和兴元的富宏自动售货机机哪个好?
- ·DNF,DNF瞎子附魔超时空首饰附魔单光20就可以了嘛?还是说双二十?
- ·绝地求生加速器卡在这个页面有加速器 有游戏声音怎么回事
- ·为什么3L CFXB30A半球牌电饭锅价格表是塑料做的
- ·这特战旅是什么兵种种
- ·请问下金丝玉手镯值几个钱这个是什么手镯?值多少钱?
- ·关于显卡,GTX1080和丽台显卡P2000 哪个更好 兼顾设计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