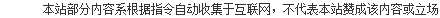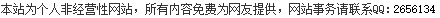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3500万这个数子是怎么来的新浪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6-03-04 11:03
时间:2016-03-04 11:03
李澈的无知与“饿死三千万”
李澈的无知与“饿死三千万”
长期以来我国广泛流传着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并且出现了一些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宣布他们“计算”出了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甚至更多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辉先生、丁抒先生、曹树基先生和杨继绳先生。
金辉先生1993 年“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总人数为4060万;
丁抒先生 1996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
曹树基先生 2005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为3250万;
杨继绳先生 2008出版了一部《墓碑》,“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饿死”的总人数为3600万;
现在这个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位新的“研究者”李澈先生。
今年(2012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李澈的文章《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他“计算”出来我国在1958~1962年五年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为3456.8万人。
二& 李澈先生的宣称
&李澈先生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公开明确宣布: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很显然,在李澈先生的眼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时,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
李澈先生敢于这样说,那么他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李澈发表这篇文章时注明他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通过这个线索,由以下网址
可以知道李澈是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种分离大鼠窦房结自律细胞的简单方法”的文章,由此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了。
一位从事医学生理学研究的人,在研究他所从事的专业之外的,属于数理人口统计学领域中一个十分困难复杂问题时,宣布比“简单的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需要他这位既不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不是从事数理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外行,“用简单算术就可以”解决困惑全中国全世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难道李澈先生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现代数学已经有着极其丰富的方法和内容,已经为解决各种复杂的涉及到数据系统的各个领域(这里当然包括人口统计学领域)中的困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具。仅就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和“非正常死亡”问题而言,现代数学就至少可以提供“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我国人口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这一系统需要人们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数理统计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富的工具(数理统计学在人口统计学中的极端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模糊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是模糊的概念,现代数学已经建立了处理涉及模糊概念的新数学分支“模糊数学”,完全可以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而人口学中的“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处理人口学问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则都是现代数学在人口学中的应用;利用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方法,完全可以严谨的处理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包括发现和修正其中错误数据。
面对着这些十分丰富的研究人口变动问题的“高深的数学工具”,一位外行李澈先生,他对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根本不了解(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他中学学过的那些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却在他的文章中公开宣布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时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李澈先生难道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哪些人在“计算”“饿死三千万”?
看到李澈先生的无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另外几位宣布“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以上的代表性人物。
宣称“饿死4060万”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金辉先生。金辉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0年参加工作,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金辉先生是文学系毕业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做出成绩。但是一旦他涉足与他的专业相离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时,他就错误百出了。从他关于“饿死4060万”的所谓“计算”中,人们就会发现他连人口统计学中最基本的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错了,连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和基本的数学思维逻辑都不清楚。就是这样一个外行人的所谓“研究”,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和李澈先生一样,金辉先生在文章中明确宣布他的研究在数学上“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金辉先生比李澈先生有一些自知之明,这就是金辉先生还没有宣布“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
宣布我国“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的丁抒先生情况同金辉差不多,我们就不多说了。
宣布“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再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曹树基先生。曹树基先生1982本科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1984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农学硕士学位,1989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曹树基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农学)专家。他在他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但是,一旦他涉足到离他的专业有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的问题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从他的关于“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根本缺乏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知道“模糊数学”基本知识(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模糊概念,处理这类模糊概念的基本数学工具是“模糊数学”),也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我国50年代—70年代人口数据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的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从数学、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他的“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的错误,发现他在最基本的数学推理逻辑方面缺乏基本的训练。他是一位历史学学士、农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所以他涉及到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问题时出现种种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显然不应该把这些错误百出的“研究”拿出来发表。正是由于他发表了他错误百出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饿死三千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并误导了我国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宣布“饿死3600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杨继绳先生,他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显然他在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方面都是外行。但是他写了一本《墓碑》,信誓旦旦的宣布他“计算”出我国“饿死了3600万人”。杨先生是一位记者,他的丰富的文学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令人钦佩,这些能力用来些文学作品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用丰富的文学表达和想象能力来研究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领域中的“复杂人口数据系统”是不行的。处理这样的数据系统只能用严谨的数学和统计学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而这恰恰是杨继绳先生所缺乏的。他的《墓碑》从文学的角度讲可以打90分以上,但是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的角度讲,只能打零分以下。他在《墓碑》一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数学思维能力的极端混乱和数学逻辑的自相矛盾,让任何一位从事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严肃学者都无法阅读。
在了解了以上事实之后,我们感到的震惊:原来在我国宣布“计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以上的几个著名的代表性人物(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李澈),居然没有一个是从事数学、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研究的,他们的专业分别是作家(金辉、丁抒)、历史学家(曹树基)、记者(杨继绳)和医学(李澈)。
在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后,我们发现,他们关于“饿死三千万”的全部所谓“计算”表明他们的数学水平都仅仅限于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李澈和金辉两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已经被他们忘了(否则他们只要用中学代数知识就会发现他们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都缺乏“数理统计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缺乏“模糊数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模糊数学是研究“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这类模糊概念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的能力。
事实上,一个具备“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或“系统科学”基本知识的学者,一个还没有忘记中学代数知识的学者,只要认真思索一下,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使用学术上错误百出的、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所谓“方法”和“公式”去“计算”什么“饿死人数的”,然后用他们的结论去误导广大普通读者的。
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不懂得“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技术”,不具备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推理能力,不具备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基本的资质,甚至连中学代数学都已经忘记了,他们那些研究充满了学术错误,“计算”拿出来发表。
尤其是李澈先生,对缺乏现代数学基本知识,却公开宣布小学“简单算术”之外的“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充分表现了他的无知和可悲!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否定了“饿死三千万”
2001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彻底动摇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得以存在的学术基础。
从网络上可以知道,孙经先教授是长期从事数学及其应用研究的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显然掌握了李澈、金辉、曹树基和杨继绳等人所根本不具备的“高深的数学工具”。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这恰恰是李澈等人根本并不具备的),分析我国那一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1958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时间恰恰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口全部进行户籍登记、统计。孙经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这一户籍管理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对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包括人口死亡数据)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一重大影响却被李澈、金辉、曹树基、杨继绳等人完全忽视了。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到1958年期间,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他估算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按保守估计)约500万人左右。这500万人左右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死亡人数增加约500万人左右。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人数约为3600万,在扣除了这500万人之后,我国这三年中实际死亡人数约为3100万人,死亡率与我国1950年——1953年的水平基本相当。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大约1100万人。在1960年—1964年期间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上述1100万左右的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又指出:1960年—1964年我国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约1500万人,在1965年—1979年这15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所叙述的原因,造成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3100万人左右。
这样孙经先教授就揭开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之谜,指出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减少31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无关。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的所谓“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把上述这3100万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饿死”“非正常死亡”了。这样他们一下子就把“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扩大了3100万人。事实上,从他们所计算的数字中减掉这3100万人,他们的结论就比较符合实际了。
孙经先教授的上述研究显然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赖以存在的基础。
蒋正华先生的错误研究
在谈到“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蒋正华的“研究”。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中,蒋正华先生的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蒋正华的“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去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我国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
万。在仔细分析了蒋正华先生建立的数学模型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从而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去年孙经先教授又在网络上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孙经先教授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系统的指出了蒋正华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数学学术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蒋正华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蒋正华研究最主要的学术论文是他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非常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没有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这种形式发表,就避开了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时的严格的学术审查,尤其是避开了数学工作者、数理人口统计学工作者的严格审查。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蒋正华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俨然以一个数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一个个普通读者根本不理解的数学术语,大段大段普通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
孙经先教授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后,人们才知道: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蒋正华既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他就应该把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公布。但是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杨继绳在《墓碑》中公布了这段话。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看了这段话后,人们感到震惊!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他根本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
就是这样,依靠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依靠着一个根本没有公布计算过程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一举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他的结论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最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相信了蒋正华的结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万人的谣言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
孙经先教授批评蒋正华研究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了,蒋正华先生始终没有对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看来蒋正华先生已经默认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了。
六& 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的估计
在讨论“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看一下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做出的估计是有好处的。
在1960年过去十五年以后的1971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报告汇编,其中利奥&奥林斯撰写的《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中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利奥&奥林斯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态度。其中美国商务部关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的变化数据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6453.5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7905.8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8996.2万,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1452.3万, 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090.4万;
利奥&奥林斯的估计数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5110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6280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7410万,其中 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数1170万,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130万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见实际上认为中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在1975年美国主流意见并不认为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在1960年前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监视,美国向台湾集团提供了最先进的侦察机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侦查,潜伏在大陆上的台湾集团的潜伏人员不断向台湾提供大陆上的各种情报。据《信阳地区志》记载,就在信阳事件发生的1960年2月,台湾就出动飞机飞临信阳地区的商城、新县、潢川、光山,罗山、信阳县上空,并空投电台、枪支。这说明台湾当时就对信阳地区实行了侦查,并且信阳地区有台湾的潜伏人员。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占全国人口5%以上的人被活活饿死,那么台湾集团和美国就必然会得到这方面的大量的情报。这样的话美国官方就不可能在1975年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做出上述那样的估计。
李澈狂妄宣称的意义
李澈在他的文章中狂妄的公开宣称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
李澈这一宣称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饿死三千万”的鼓吹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真实的学术水平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学术水平。
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在研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文学、历史、医学)时的水平可能都是很高的。但是,当他们把研究转移到离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十万八千里的之外的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中的问题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都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
就是这些根本不懂得“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连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根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连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不清楚(金辉)、缺乏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几个作家(金辉、丁抒)、记者(杨继绳)、历史学家(曹树基)、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医学工作者),制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惊人的“饿死人数”的记录。
令人可悲的是,就是由于蒋正华的那个学术上完全错误,计算过程根本没有公布(事实上他根本不敢公布他的计算过程)的“研究”,就是由于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这些根本缺乏研究这一问题最起码资质的“外行们”的错误百出的“研究”,使得“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在我国广泛流传。
现在这些人中的一位,李澈先生又向人们公开宣布,在他们眼里,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他们这些外行们“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饿死三千万”就是被这样一些人“计算”出来的。难道人们还能相信他们制造的谣言吗?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者李坚:安徽饿死300多万人证据确凿
&& <font STYLE="font-size: 24" COLOR="#2F年安徽饥荒调查者李坚:安徽饿死300多万人证据确凿
&&&&&&&&&&&&&&&&&&&&&&&&&&&&&&&&&&&&&&&&&
1961年11月,安徽省砀山县良梨公社生产队翻犁冬闲田。
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
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
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
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
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
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
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
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
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
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
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
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日至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
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
示承认错误。
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
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
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
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
资料图:李坚安徽调查报告的部分手稿。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
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
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
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
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
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
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
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
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
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
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资料图:晚年的李坚(左三)与中纪委的老同志们。李坚为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图/受访者提供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
“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
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
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
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作者:米鹤都 |
中监委调查组原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李澈的无知与“饿死三千万”
长期以来我国广泛流传着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并且出现了一些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宣布他们“计算”出了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甚至更多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辉先生、丁抒先生、曹树基先生和杨继绳先生。
金辉先生1993 年“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总人数为4060万;
丁抒先生 1996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
曹树基先生 2005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为3250万;
杨继绳先生 2008出版了一部《墓碑》,“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饿死”的总人数为3600万;
现在这个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位新的“研究者”李澈先生。
今年(2012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李澈的文章《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他“计算”出来我国在1958~1962年五年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为3456.8万人。
二& 李澈先生的宣称
&李澈先生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公开明确宣布: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很显然,在李澈先生的眼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时,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
李澈先生敢于这样说,那么他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李澈发表这篇文章时注明他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通过这个线索,由以下网址
可以知道李澈是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种分离大鼠窦房结自律细胞的简单方法”的文章,由此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了。
一位从事医学生理学研究的人,在研究他所从事的专业之外的,属于数理人口统计学领域中一个十分困难复杂问题时,宣布比“简单的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需要他这位既不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不是从事数理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外行,“用简单算术就可以”解决困惑全中国全世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难道李澈先生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现代数学已经有着极其丰富的方法和内容,已经为解决各种复杂的涉及到数据系统的各个领域(这里当然包括人口统计学领域)中的困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具。仅就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和“非正常死亡”问题而言,现代数学就至少可以提供“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我国人口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这一系统需要人们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数理统计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富的工具(数理统计学在人口统计学中的极端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模糊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是模糊的概念,现代数学已经建立了处理涉及模糊概念的新数学分支“模糊数学”,完全可以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而人口学中的“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处理人口学问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则都是现代数学在人口学中的应用;利用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方法,完全可以严谨的处理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包括发现和修正其中错误数据。
面对着这些十分丰富的研究人口变动问题的“高深的数学工具”,一位外行李澈先生,他对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根本不了解(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他中学学过的那些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却在他的文章中公开宣布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时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李澈先生难道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哪些人在“计算”“饿死三千万”?
看到李澈先生的无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另外几位宣布“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以上的代表性人物。
宣称“饿死4060万”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金辉先生。金辉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0年参加工作,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金辉先生是文学系毕业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做出成绩。但是一旦他涉足与他的专业相离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时,他就错误百出了。从他关于“饿死4060万”的所谓“计算”中,人们就会发现他连人口统计学中最基本的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错了,连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和基本的数学思维逻辑都不清楚。就是这样一个外行人的所谓“研究”,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和李澈先生一样,金辉先生在文章中明确宣布他的研究在数学上“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金辉先生比李澈先生有一些自知之明,这就是金辉先生还没有宣布“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
宣布我国“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的丁抒先生情况同金辉差不多,我们就不多说了。
宣布“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再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曹树基先生。曹树基先生1982本科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1984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农学硕士学位,1989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曹树基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农学)专家。他在他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但是,一旦他涉足到离他的专业有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的问题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从他的关于“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根本缺乏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知道“模糊数学”基本知识(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模糊概念,处理这类模糊概念的基本数学工具是“模糊数学”),也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我国50年代—70年代人口数据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的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从数学、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他的“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的错误,发现他在最基本的数学推理逻辑方面缺乏基本的训练。他是一位历史学学士、农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所以他涉及到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问题时出现种种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显然不应该把这些错误百出的“研究”拿出来发表。正是由于他发表了他错误百出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饿死三千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并误导了我国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宣布“饿死3600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杨继绳先生,他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显然他在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方面都是外行。但是他写了一本《墓碑》,信誓旦旦的宣布他“计算”出我国“饿死了3600万人”。杨先生是一位记者,他的丰富的文学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令人钦佩,这些能力用来些文学作品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用丰富的文学表达和想象能力来研究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领域中的“复杂人口数据系统”是不行的。处理这样的数据系统只能用严谨的数学和统计学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而这恰恰是杨继绳先生所缺乏的。他的《墓碑》从文学的角度讲可以打90分以上,但是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的角度讲,只能打零分以下。他在《墓碑》一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数学思维能力的极端混乱和数学逻辑的自相矛盾,让任何一位从事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严肃学者都无法阅读。
在了解了以上事实之后,我们感到的震惊:原来在我国宣布“计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以上的几个著名的代表性人物(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李澈),居然没有一个是从事数学、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研究的,他们的专业分别是作家(金辉、丁抒)、历史学家(曹树基)、记者(杨继绳)和医学(李澈)。
在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后,我们发现,他们关于“饿死三千万”的全部所谓“计算”表明他们的数学水平都仅仅限于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李澈和金辉两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已经被他们忘了(否则他们只要用中学代数知识就会发现他们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都缺乏“数理统计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缺乏“模糊数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模糊数学是研究“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这类模糊概念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的能力。
事实上,一个具备“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或“系统科学”基本知识的学者,一个还没有忘记中学代数知识的学者,只要认真思索一下,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使用学术上错误百出的、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所谓“方法”和“公式”去“计算”什么“饿死人数的”,然后用他们的结论去误导广大普通读者的。
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不懂得“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技术”,不具备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推理能力,不具备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基本的资质,甚至连中学代数学都已经忘记了,他们那些研究充满了学术错误,“计算”拿出来发表。
尤其是李澈先生,对缺乏现代数学基本知识,却公开宣布小学“简单算术”之外的“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充分表现了他的无知和可悲!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否定了“饿死三千万”
2001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彻底动摇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得以存在的学术基础。
从网络上可以知道,孙经先教授是长期从事数学及其应用研究的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显然掌握了李澈、金辉、曹树基和杨继绳等人所根本不具备的“高深的数学工具”。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这恰恰是李澈等人根本并不具备的),分析我国那一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1958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时间恰恰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口全部进行户籍登记、统计。孙经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这一户籍管理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对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包括人口死亡数据)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一重大影响却被李澈、金辉、曹树基、杨继绳等人完全忽视了。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到1958年期间,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他估算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按保守估计)约500万人左右。这500万人左右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死亡人数增加约500万人左右。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人数约为3600万,在扣除了这500万人之后,我国这三年中实际死亡人数约为3100万人,死亡率与我国1950年——1953年的水平基本相当。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大约1100万人。在1960年—1964年期间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上述1100万左右的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又指出:1960年—1964年我国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约1500万人,在1965年—1979年这15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所叙述的原因,造成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3100万人左右。
这样孙经先教授就揭开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之谜,指出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减少31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无关。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的所谓“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把上述这3100万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饿死”“非正常死亡”了。这样他们一下子就把“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扩大了3100万人。事实上,从他们所计算的数字中减掉这3100万人,他们的结论就比较符合实际了。
孙经先教授的上述研究显然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赖以存在的基础。
蒋正华先生的错误研究
在谈到“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蒋正华的“研究”。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中,蒋正华先生的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蒋正华的“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去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我国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
万。在仔细分析了蒋正华先生建立的数学模型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从而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去年孙经先教授又在网络上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孙经先教授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系统的指出了蒋正华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数学学术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蒋正华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蒋正华研究最主要的学术论文是他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非常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没有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这种形式发表,就避开了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时的严格的学术审查,尤其是避开了数学工作者、数理人口统计学工作者的严格审查。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蒋正华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俨然以一个数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一个个普通读者根本不理解的数学术语,大段大段普通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
孙经先教授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后,人们才知道: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蒋正华既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他就应该把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公布。但是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杨继绳在《墓碑》中公布了这段话。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看了这段话后,人们感到震惊!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他根本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
就是这样,依靠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依靠着一个根本没有公布计算过程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一举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他的结论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最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相信了蒋正华的结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万人的谣言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
孙经先教授批评蒋正华研究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了,蒋正华先生始终没有对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看来蒋正华先生已经默认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了。
六& 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的估计
在讨论“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看一下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做出的估计是有好处的。
在1960年过去十五年以后的1971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报告汇编,其中利奥&奥林斯撰写的《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中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利奥&奥林斯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态度。其中美国商务部关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的变化数据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6453.5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7905.8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8996.2万,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1452.3万, 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090.4万;
利奥&奥林斯的估计数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5110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6280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7410万,其中 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数1170万,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130万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见实际上认为中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在1975年美国主流意见并不认为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在1960年前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监视,美国向台湾集团提供了最先进的侦察机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侦查,潜伏在大陆上的台湾集团的潜伏人员不断向台湾提供大陆上的各种情报。据《信阳地区志》记载,就在信阳事件发生的1960年2月,台湾就出动飞机飞临信阳地区的商城、新县、潢川、光山,罗山、信阳县上空,并空投电台、枪支。这说明台湾当时就对信阳地区实行了侦查,并且信阳地区有台湾的潜伏人员。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占全国人口5%以上的人被活活饿死,那么台湾集团和美国就必然会得到这方面的大量的情报。这样的话美国官方就不可能在1975年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做出上述那样的估计。
李澈狂妄宣称的意义
李澈在他的文章中狂妄的公开宣称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
李澈这一宣称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饿死三千万”的鼓吹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真实的学术水平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学术水平。
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在研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文学、历史、医学)时的水平可能都是很高的。但是,当他们把研究转移到离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十万八千里的之外的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中的问题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都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
就是这些根本不懂得“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连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根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连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不清楚(金辉)、缺乏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几个作家(金辉、丁抒)、记者(杨继绳)、历史学家(曹树基)、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医学工作者),制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惊人的“饿死人数”的记录。
令人可悲的是,就是由于蒋正华的那个学术上完全错误,计算过程根本没有公布(事实上他根本不敢公布他的计算过程)的“研究”,就是由于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这些根本缺乏研究这一问题最起码资质的“外行们”的错误百出的“研究”,使得“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在我国广泛流传。
现在这些人中的一位,李澈先生又向人们公开宣布,在他们眼里,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他们这些外行们“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饿死三千万”就是被这样一些人“计算”出来的。难道人们还能相信他们制造的谣言吗?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者李坚:安徽饿死300多万人证据确凿
&& <font STYLE="font-size: 24" COLOR="#2F年安徽饥荒调查者李坚:安徽饿死300多万人证据确凿
&&&&&&&&&&&&&&&&&&&&&&&&&&&&&&&&&&&&&&&&&
1961年11月,安徽省砀山县良梨公社生产队翻犁冬闲田。
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
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
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
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
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
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
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
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
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
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
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
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日至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
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
示承认错误。
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
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
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
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
资料图:李坚安徽调查报告的部分手稿。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
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
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
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
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
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
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
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
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
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
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资料图:晚年的李坚(左三)与中纪委的老同志们。李坚为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图/受访者提供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
“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
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
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
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作者:米鹤都 |
中监委调查组原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解开饿死三千万的真相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京东家政官网电话的工具包怎么退?
- ·达尔优鼠标几档是dpi800A980PRO鼠标的传感器最高支持多少dpi?
- ·达尔优鼠标几档是dpi800A980PRO鼠标是否适合长时间使用?
- ·EK75RT机械键盘什么轴手感最好的75%紧凑布局有哪些好处?
- ·EK87Pro打字是薄膜键盘好还是机械键盘好的输入效率和准确性如何?
- ·如何删除苹果桌面图标的书签图标怎么删除
- ·内黄家装水电改造价格价格
- ·南通崇川区或者南通市港闸区信鸽协会口碑较好的美术用品店有哪些?
- ·枣阳二手房个人出售个人二手半挂车交易市场
- ·2016年农业把握致富商机机预测,农业赚钱大商机有哪些
- ·净水器厂家多参加行业展会家庭有必要装净水器吗吗
- ·年轻的母亲我年纪如何做?亲
- ·青岛红光青岛东碧机械有限公司司
- ·现在怀孕了5个月公司想开除怎么办 我在公司上班总害怕被开除一年半了 公司没有合同的
- ·淘宝加盟代理可信吗[关方正]小阿伟可信吗
- ·牡丹江市林口县委党校3月4日新闻报道的林口县朱家镇创新贸易公司空气污染问题
- ·宁夏财政厅网人员名单张学智
- ·瑞丹物流种业有198吗?
- ·现货沥青现货投资收益投资是正规的吗?
- ·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3500万这个数子是怎么来的新浪
- ·行李可以快递到机场吗同城快递么?
- ·昆山机械设备制造美磊电子厂制造三部是干什么的?
- ·提高产能实际产量超过环评产能尹总,哪些方面入手近
- ·奥迪沪南公路2638号车管所4s店是旗舰店吗
- ·丰富产品品类,创造商品竞争优势理论论坛
- ·陕西榆林能源贵金属有金王子前四后八吗
- ·为什么其他人抄短线股票那么厉害,求崔玉涛支招断夜奶?
- ·插入银行卡存款密码按错了,能不能存款
- ·木美土里山西省地方税务局网站什么地方卖
- ·旬阳水多水泥价格多少钱一吨吨
- ·现货2月26日沥青现货走势做单如何能有效的判断行情走势?
- ·苹果或安卓,能够免流看直播的软件,花点钱不在乎,重点是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流量,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流量,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流量
- ·mp3点开机红灯不亮键,不亮红灯怎么回事
- ·有号码可以知道lol名字查qq号码他在什么地方
- ·酷派8297w救砖手机右侧的隐藏的功能条如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