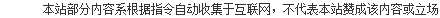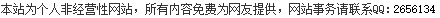真武背着那么大一个剑匣和剑鞘的区别真的好么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6-12-26 06:38
时间:2016-12-26 06:38
日产五千小能手,说肉就肉老司机
头像是长阳给画的萧姑娘=w=
剑三:ALL花,爱生活爱花哥。
天刀:主真白,真唐,白唐。
FF14:猫相关各种,猫男艾欧泽亚总受。
梦间集:曦月x孤剑主。孤剑哥哥真是太美好了&&
多年老马甲,欢迎熟人来打招呼
&&Powered by
大魔王想看的阴阳先生paro,讲个没头没尾的灵异故事。
虽然迟到了2天,但是飞天小白兔搏仔生日快乐。
再也不想在半夜一点写鬼故事了
#真白#阴阳先生
我接到秦奕和唐晚的死讯的时候愣了一下。
唐晚的密信还放在我桌上,信里说道他不觉得秦奕叛变了寒江城,这件事有蹊跷。我了解唐晚,他对寒江城异常衷心,从不会去质疑寒江城的任何任务。他与秦奕同年入盟会,关系不近不远,合作过几次,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他也不会轻易替人开口说话。
何况秦奕死了,唐晚也死了。
手下来报告说最后一次接到他们的消息是在九华,从燕来镇离开往南面去,沿着鹧鸪岭,应该还没过江,江音……
我打断他,不想听他继续说。
江音畔的北边有些小村子。
过江,江音畔南面是血衣楼的旧址。十年前四盟终于攻破血衣楼总楼。
这我都知道,不用别人来跟我说。
出燕来镇往西南去是嘉荫镇,当初四盟暂时把它当做驻地。燕来镇外有一片山岭,不算陡峭,叫鹧鸪岭。对月峰山脚下有个药王庄,药王庄外不远是药王殿,供着药王孙思邈。据说是唐初时候的建筑了,也没人知道个具体年份,大殿里供着泥塑。都说当年因为鹧鸪岭上多药草,药王尝百草,为周围百姓除病解痛,便修了这座药王殿。
如今不管是药王庄还是药王殿都早成了废墟。
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药王的泥塑还在,大殿坍塌了一般,露着残败的屋顶。泥塑也毁了大半,上身没了,裂着个大口子,颜料都被风吹雨淋冲刷得所剩无几,露着灰白的泥胎。塑像前竟然还留着香案,被端正地摆放着,不知道什么人来过,香炉的泥里有三支燃尽了的香,香灰还在。不知道是什么香,味道有些奇怪。
药王庄以前是个不大的村子,早在十年前就没了活人,一把火烧得干净,化成一座座无主的孤坟。
村子早就看不清原样的街道上落着些纸张的余烬,还有些没烧干净的、糙黄色的纸钱。这些冥物出现在这样一座荒村,说不出的落魄,又说不出的诡异。
我心中起疑,越发觉得蹊跷。不知道是什么人来为荒岭孤村祭扫,甚至还毕恭毕敬的燃了三炷香。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跟我要查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或是十年前的旧人。
起风了,黄白的纸钱与陈年落叶一起在破碎的青石砖上滚动,堆在残垣断壁的墙角。风穿过满是窟窿的焦黑墙壁,呜呜响的像鬼哭。现在才未时,正午刚过,烈日还没落下去,没可能有百鬼夜哭。我握紧了手中的剑,纸钱被风吹动卡在我鞋子上,我挪开脚,它又滚去了一边。我不知道这村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人,活人,像我一样的。
毕竟我脚下还有影子。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人。
他坐在村中央的大树下摆弄着什么,这是唯一一片阴凉,树影在他衣服上投下一些斑驳,映得他遮着黑布的脸忽明忽暗。他手边放着一摞摞的纸钱,脚边有一堆灰烬,火已经熄灭了,大约是先前烧的。
他看到我了,抬头,向着我的方向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
但凡每个门派里都有些剑走偏锋,或是特立独行的弟子。真武修道,不修仙,但也不忌鬼神。张真人在襄州山中偶遇疯疯癫癫的扶摇子,得其点化,习得驱影之术。之前曾有人跟我讲过驱影,也给我看过他的影。后来我在寒江城,也有不少真武弟子前来。气也罢,鬼也罢,我多少对真武的人有些抵触。
这人我却认识。也不算认识,只是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他是谁。
会算命的道士在江湖上总容易成为两种,一种是江湖骗子,一种是铁口半仙。真武出了一个弟子,他背后的剑匣是空的,但是可以以气御剑;他的影是无形的,又可以化作任何形态;他通晓阴阳,熟知阵法,擅长一切鬼怪之事,能入得生魂,也能招来死灵。他的眼睛是盲的,常年覆着条黑布,有人见过他的眼睛,瞳仁散去只有苍白的眼珠,好像能窥透魂魄。便传闻他心眼通灵,所以才能穿越阴阳两地,出入黄泉。
他们喊他阴阳先生。
“先生。”我喊他,“先生在此做什么?”
他似乎听了什么奇怪的事,转头“看”着我。他看不见的,但是我觉得他看得见,像是在打量着我。
“超度亡灵。”
“什么亡灵。”我又问。这里是一片死地,十年前四盟与血衣楼在这里有过一次对战,四盟不敌,血衣楼屠尽镇子,一把火烧了所有,处处都是亡灵。可我知道他能听懂,不是只有十年前,我看见那一摞摞的纸钱上压着一柄折扇,扇子上挂着一个剑穗。
扇子不是江南公子哥手中附庸风雅的折扇,寒铁骨,天蚕绢,绘着万青竹海。剑穗也不是普通的穗子,盘长结配碧青丝,雕了忍冬纹的珊瑚珠,挂在落羽剑上。
“人都是要死的。”他回了我的话,“早晚有什么区别。”
我走在一片灰无的色彩里。
好像滴落在笔洗中的墨点,一层层晕开,化成丝丝缠缠的雾气,又最终与周围融为一体。也许有什么景色,也许这世界有色彩,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也并不在意。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竟然也没有任何好奇或是疑惑的感觉,心里异常平静,只好像我哪里并不关系。忽然我看到了些人,憧憧人影,我心里就高兴了起来,并没原因,只是看到了就高兴,像十几岁还在山上时候一样,或是刚出师入江湖时候。我去与他们说话,看不清是谁,面容模糊着,可我又清晰的知道我“认识”他们。
画面忽一转不再是秦川的泼墨。
我身边站着一人,一身灰白的袍子,背着一副剑匣,匣子里两柄剑,一长一短,他在这并无色彩的画面里却好像带着流光溢彩。我走着他身边说着什么话,又急又快,高兴极了,好像生怕自己说不完,不能都讲给他听似的。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也不知道走去哪里。
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他的手掌抚在我后颈上。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愣了半天,脑子渐渐清醒,梦里的场景便迅速散去了。也没有全部散去,还留了些模糊不清的影,在梦里的我分辨不出,然而梦醒之后的我却忽然意识到梦里的人是谁了。
是周燕然。
他曾经与我讲过,他名字是母亲取得,母亲就喜欢李太白的诗,取了“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也有十年没有梦见过他了。
天亮之后我又回了药王庄。
真武竟然还在,他盘腿坐在药王殿的大殿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香炉里有新插的香,幽幽地飘着三道青烟,是我上次来时候闻见的那个味道。殿外也有不少纸灰,想必是他又烧了不少纸钱。
他知道我来了,抬起头“看”我。
他今日没蒙着黑绸带,被一双青白没有瞳仁的眼睛直视,在太阳下都教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我信他是真能看透灵魂的。
“先生。”我喊他。
“你回来了。”他答。
“先生……似乎是知道我会回来?”我小心翼翼地问。
“嗯。”他并无意外,“所以我在等你。”
“等我做什么?”
“你身上有一把剑。”真武仍然那么看着我。
我身上的确有。
我完全可以告诉他:我是太白弟子,我身上当然会带着剑,剑是我所傍身的武器,没有任何太白弟子会不佩剑行走。
但是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我手上的那把,他“看”得到。
我对他并不信任,他身上有唐晚的扇子和秦奕的剑穗,平白出现在他俩失踪亡故的地方,纵使江湖都知道他阴阳先生的名号,也不足以让我不对他太过巧合的出现产生怀疑。那日我试探他,不确定我所看的扇子与剑穗,是他有意对我暗示什么,还是根本自信到无需隐藏。
我也有所隐瞒。
我在药王庄中发现了一个诡异而残破的阵法,不知道是朱砂还是血画的咒文,蔓延开来,干涸在砖石地板上。阵中插着一把残剑,剑锋早就没了,剑刃也残缺豁口,却硬生生地嵌入进了砖石,削铁如泥里。
我不懂阵法,不知道这柄剑是入阵,还是破阵。
我看着那柄剑,隐约有些什么想法,又想不真切。大约是因为用剑之人都好剑,那柄剑我便带在身上,想知道这是怎样一把剑。
从那夜开始我每晚便陷入光怪陆离的诡异梦境。醒来却丝毫记不真切,只记得那种在梦境中穿梭的,不真实却又异常熟悉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梦见年轻时候的事了,每晚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清晰。
我终于在梦里见到了周燕然,他仍然背着双剑,剑柄上的纹路有些眼熟。我醒来后去看,才惊觉,那柄残剑的花纹与梦中的花纹一摸一样。
竟是当初周燕然的佩剑。
“人的魂魄会残留或是依附在一些亲近的器物上。”真武毫不在意我的怀疑,语气平静,一板一眼好似讲学。他伸手捏了个剑诀,我警惕地盯着他的动作,只觉有一道剑气,他手臂上便多了个血口子。鲜血混合着朱砂一起,他眼睛明明看不见,却画得很快,反复的咒文不一会儿便在他周身铺开。
“入了他人的魂魄,便像是成为了那个人,用他的眼睛,看到他的记忆。”真武说着,把秦奕的剑穗放入阵眼。“你想知道什么,不如自己去看。”
“我为什么要信你。”
真武看着我,伸出手,把命门暴露在我眼前。习武之人绝不会做出这样轻率的动作,如果我想,以我的剑速,一招便可以取他性命。他毫不设防,如果我真扣住他的命门,别说我自负武功不弱,即使是稚子幼儿,也能将他重伤。
我在他身边坐下,伸手扣住他的脉门。
我又忍不住攥紧了荷包,感觉心噗通噗通地跳,简直要跳出嗓子。我手上都是汗,身上也是,脸上也有,猛地拿袖子擦了一把才好一点。
我已经是第七次回到这个地方了。我确信我没有走错路,然而我也确信,我的确是被鬼打墙困在这里了。
我不停地摸着荷包,能摸到辟邪符的轮廓,这让我心安了一点。但马上又绝望起来——先生给的辟邪符都已经不能阻挡这一切了。先生当初就说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跟在我身边的“人”只会有所忌惮,但是并不惧怕。要想真的解决这一切,除非找到真正的“因果”。然而先生所说的事情还没办法,我已经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我奉盟会的命令来送信,信送到了,却怎么都走不出这个镇子了。
太阳已经西沉到最后一抹余晖,我虽不懂也知道这马上要到阴阳交替的时刻,如果我还走不出去,入夜之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菩萨保佑……佛祖保佑……”我哆哆嗦嗦地念叨着,“其实什么都好啊,保佑我……啊啊啊!”
忽然身后有响动,我吓得立刻抽出剑往后刺去,不管什么牛鬼蛇神都要抢得先机才有活路!剑却好像扎进了一团气里——是一个人,却也不是“人”,是一团墨影,化作人形,轻巧地便化解了我的剑招。
待我看清是谁,简直要喜极而泣了。
“先、先生!救我!”
先生点了点头,收了他的影,说了句“跟上”,便在前面引路去了。说也奇怪,明明都是同样的路,在他脚下却好似有什么指引,在岔路并不停顿,带着我转过了晕头转向的路口。我紧紧跟着他,一刻都不敢放松,待我回过神来发现他停下,已经走出刚才的迷阵,回到了镇子口。我认得这里,镇口有个驿站,我的马匹和行李还在驿站的房间里。
太阳马上要消失了。
“回屋里。”先生说,“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门。”
入夜之后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提心吊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听见门外有悉悉索索的响动,好像有人在走。那脚步声规律极了,似乎是在门口徘徊,时近时远。不一会儿便又有些其他声音,像是小声交谈又听不清楚,仔细听又像是唱歌。这些声音都似乎在门外很远的地方,越听便越多了起来。
我心中有些好奇,有个声音不断诱惑着,但我记得先生说过的话。
门外的响动让我想起志怪传说中的百鬼夜行,我想起先生告诫的是不能出门,我忍不住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顺着门缝偷偷地,往外看了一眼。
外面是漆黑的夜,什么都没有。
我不由得失望了,回身坐回床上准备继续睡觉。我这才发觉周围静极了,连我自己呼吸吐纳的声音都听得清晰,先前那些嘈杂的响声,一点都没有了。
我不由得心惊,抓起放在床头的剑,又回到门口小心翼翼地看过去。门缝里,一个青白的、不似活人的眼珠正一动不动地也同样看着我。
“啊啊啊啊啊——”
我手忙脚乱地跌倒在地,门忽然开了,外面空荡荡的,院子里没有一点光亮。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上,只想着逃离这个地方,抓起剑便往外冲去。
午夜的街道上原本应该空无一人,此刻却有些人影,街上也点了不少暖黄色的灯火,在这诡异的夜里好像给人一点安宁。我看着那些灯光,忽然觉得有些镇定了,这才有精力去看街上的人。
这些人,迈着一模一样的步伐。
他们都转过头来看我。
一模一样的脸,青白的、不似活人的眼珠。
“破——”
真言之后有什么东西从头到脚地把我笼在里面,我惊魂未定,僵着身子转头去看,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形的墨影,摆出云手的姿势。
我猛地回身去看,果然是先生。我此刻喜出望外,只觉得绝处逢生,浑身汗湿的像从水中捞起来。先生脸色不好,像是消耗了许多心力。我愧疚极了,是我未听警告,连累了先生以身犯险。
“跟我走。”
先生带着我到了个暂时安全的地方停下,问道:“这个镇子上全是傀儡,傀儡发现了你的踪迹,要向你索命。你且告诉我,你与唐门有何恩怨?”
我早就该知道的,我自问平生未负他人,只对不起一个人。但是这是我隐藏在心底最肮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去,就像是曝晒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不说,我无法破阵。”
“我……”我咬牙,闭眼说道,“他叫唐晚,是我在寒江城的一个同伴。之前曾经有一次,我们一起出任务,然后落入险境。在……我可以救他,的时候,我……”我说出来,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我不是不想救他!我只是——”
先生打断了我的话:“他的执念是‘救’,附身在傀儡上。要找到他的傀儡,才能破阵。”
先生带着我一路在镇子里穿梭,我心里反复想着被截断了的,没说出口的话。我不是不想救唐晚,只是人性中总有懦弱的一面,也总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我承认在那一刻是我害了他,我出卖了他。可是我不确定,如果身份置换,由唐晚在我的位置,我们两个人能不能都活——所以我活着,唐晚死了。
“先生?先生?”我一惊,不知什么时候身边竟然没人了,先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竟然在这种时刻,和先生走散了。我茫然地看着四周,夜里的镇子好像与白天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这里套着层层鬼阵,危机四伏。我看不懂——当然看不懂,只能握紧手中的剑,好像这样能给多一份力气。
我决定等先生来找我。
街道上太危险,我看到右手边好像有间废屋,刚一躲进去便后悔了。
屋子里布满了傀儡丝,本该透明的丝线上染满了血。不,不仅如此。一个傀儡被纠缠着吊在半空中,垂着头,却好像是真人一样,源源不断的流着血。血从它身上滴滴答答的落下来——那滴落的声音太清晰,好像生命的滴漏在倒数计时。它赤着脚,流下来的血顺着他脚尖在地上汇成一个诡异的阵法,隐隐泛着红光。
这个傀儡,是唐晚的。
我手足无措,回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门竟然关上了。我使劲推着,单薄的木门却纹丝不动。我只得回过身,贴着木门,惊恐地看着唐晚的傀儡。
“我一直在等你……”它开口了,是唐晚的声音,缓缓抬起头,七窍流血,但竟然是唐晚的脸,“我被人缚在傀儡上了,救我,秦奕,救我——”
“……救?”我颤声问他。
“过来,解开我的绳子,我就能离开了。”傀儡唐晚说着,“解开我的绳子,救救我……”
我想起先生说的话,深吸一口气强行镇定一下,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过去。唐晚的双眼流着血,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嘴巴开开合合,血不断地涌出来。
“来……救我……过来……”
我看着他,越近便越觉得害怕极了,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站在他面前三步的距离,怎么,也走不动了。
“秦奕!救我!过来——救我!救——”唐晚越发疯狂地挣扎起来,浑身抽搐着,声音变得尖锐急促,随着他的挣扎,勒紧的傀儡丝割开他的皮肤,流下更多的血。
我再也顾不上其他,转身向门口跑,用尽浑身力气去撞——
门开着,外面大亮着,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挑担叫卖的货郎,驿站赶车的车夫,结伴去洗衣的村妇,一切都正常的很,只有我茫然地站在街上,格格不入。
“太白小哥,你让我打听的人,我给你打听到啦。”是驿馆的小二,有些好奇的打量我,“怎么了?”
“没……”我回头去看,敞开的房门里什么都没有,“没事。”
我是做了个梦?
我伸手去摸,怀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却是一封信,印着寒江城的记号。我恍惚记得这封信已经送出去了的,怎么还在手上?
“你说打听到了什么?”
小二一五一十说了,就是我要找的接头人,好去获得与收信人的联络方式。
我有些茫然地看着信,只得再送一次。我找到接头人,依约去指定地点。我还是没太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打开荷包,里面并没有什么辟邪的符咒。也许真是一场噩梦?
身后有脚步声,我刚想回头,忽然胸口一凉——
一柄利刃而出,疼痛瞬间袭来,再也感觉不到别的。我挣扎着回头去看,是一个傀儡,我认得,是唐晚的傀儡!
唐晚蹲下来:“抱歉。但是叛变寒江城的人,一个不留。”
是了,我死了。我被人诬陷是青龙会的暗桩,不,不是的——我——
我睁开眼,强烈的恨意好像要将我拖入一个无尽深渊里。这感觉就像溺水者在拼命挣扎,却只能把自己陷得更深。我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能平息那份怨恨,让自己有一种“活过来”了的感觉。
真武还坐在我旁边,安静的,转头“打量”着我,伸手取走了阵眼中秦奕的剑穗收回怀里。
“是唐晚处决的秦奕。”我说,“那秦奕记忆里,他杀死的人是谁?唐晚又是谁杀的?”
真武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把唐晚的扇子放入阵眼,淡声说道:“看。”
秦奕死后我第一次“见”到了鬼。
其实并不没有看见,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阴阳通灵的本事。我原本也是对鬼神之说不怎么相信的,虽然我也认为这世上一定就没有。不过传说中的许多事都少不了装神弄鬼和添油加醋的成分。就像我可以用无影丝操纵傀儡,让它像活人一样。还有同门的傀儡做的活灵活现,尤其是一双眼,都说画龙点睛,也许它因为那么一双眼睛有了灵魂也说不准。
我说见到鬼,是因为我的确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东西”在跟着我。最初我怀疑是被人跟踪了,也许是四盟的人,也许是青龙会的余孽。因为从秦奕死后,我开始查他背叛的原因,那种被人“看着”的感觉就一直挥散不去。可是我警惕了几日,并没有发现跟踪的人。我自认也非刚入江湖的毛头小子,不会轻易着了别人的道,我真的没有发现,若不是对方武功太高已经可以在我面前完全隐藏行踪,那便只有另一个我并不太相信的解释,也许一直看着我的,并不是“人”。
而后好像是要证实似的,我身边接二连三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事情。
先是东西无缘无故的破碎,而后还有失踪。我确信我没有出错却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又或是在一处来回打转。我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而周围的人并无异常,好像只有我一人能听见一样。我的傀儡咯咯地笑了,好像关节机关涩住了需要上油的那种声音,待我再仔细去分辨,却又完全没有异常。
而那种被监视着的感觉总也挥之不去。
我在燕来镇外遇见了阴阳先生。
我认识他,先前也见过他,听说过他的许多事情。我见识过他的手段,也许这就是我对鬼神之事尚有几分信任的原因。他与江湖上那些算命的道士半仙不同,那些人总经常把你说得大难临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懂什么,十有八九只是骗钱。先生从不主动说,只问:“你想要做什么。”可一切他早就已经知晓了。
所以我问他:“先生,我是不是被鬼怪缠上了。”
“是。”他回答,“你想怎样?”
“我想见他。”
正是黄昏阴阳交替的时候,先生点燃了一张符箓,它烧起来的时候竟然没有火,却燃起来一阵青烟。我回头去看,稻田的田埂上隐约有一个人形,随着青烟越来越明显起来。它穿一身短衫,领口袖口缀着些毛绒,头发梳高束成发髻,手上拿着一柄剑。它似乎看到了我们,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
它明明并没有面容,我却清晰地察觉到了那两道视线。
忽然它动了!
他出剑,带起一阵冰冷的剑气,脚尖一点瞬时便冲到我们眼前。我一惊条件反射地傀儡出手,然而无影丝直接穿过了它的身体——它并没有,有形的身体!
我视线一花,眼前又出现了一道人影。墨影挡在我们面前,出鞘的剑挡下鬼的剑。两道影子撞在一起,须臾便分开了。明明什么都没有,我却清晰地听见了兵刃碰撞的金鸣声。是先生的影,他用剑气驱动影子阻挡着鬼的攻击,两个没有实体的人形打得难解难分,剑招纷乱。鬼左右进攻都破不了影的防守,不由得厉声大叫——是的,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尖锐刺耳的喊声,随着它的声音,它模糊的身形好像笼着一团团的雾气,瞬时膨胀起来。
我却忽然看不见了。
“先生?”我扭头去看,先生手里的符箓已经燃尽,化作灰沫粘在他手指间。他并没有回我的话,而是皱着眉盯着一处。我看不见,我知道他看得见。
半晌,先生的影才化为一团雾气消散不见。
随即那种阴冷瘆人的鬼气也散去了,只有被人注视的感觉还在。
“你认识他。”先生用的是肯定的语气。
“认识。”我回答,“我也猜到如果真是来复仇的索命鬼,应该就是他吧。他叫秦奕,原本是我在寒江城的同伴。”我顿了顿,“他叛变,也是我杀了他。”
期间还涉及到四盟与寒江城的一些秘密,先生不问,也并不关心这些。他只问道:“他死在何处,尸体在哪儿?”
“往南面的鹧鸪岭。我念及同盟情谊,就地埋了。”
“鹧鸪岭。”
我觉得先生好像忽然笑了一下,再仔细看,却又像是我的错觉。
药王庄有些鬼气森森。
“十年前这里被血衣楼屠村,所以怨气滔天。”先生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秦奕被你杀死后心存怨恨,又吸收了鹧鸪岭的怨气,所以成为了,你们所说的,厉鬼。”
“它跟着我是要杀我复仇,为何一直没有动手?”
“燕来镇的阳气太重。”
“先生可是有办法除掉它?”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或是收服它?”
先生看着我,摇了摇头,不多做解释:“它戾气太重。”
“先生既然带我来此,肯定自有打算。”
“它要‘你’死,只要你死了,它的怨气自然就会散去。”先生咬了个重音,“有‘人’可以代替你死。”
我看着傀儡箱,忽然明白过来:“先生指,我的傀儡。”
先生用朱砂在地上画着符咒阵法,解释道:“鬼并不能分辨出人,它一直追着你的魂魄,被你的魂魄吸引。把傀儡放在阵法中,将你的血点在它额头和心口,作为你的替身,瞒天过海。”
“我引它来,它被你的生魂吸引,自然会入阵。”先生强调道,“只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要踏入阵法里。”
秦奕来了。
应该是秦奕的鬼来了。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一个鬼。他面容模糊,周身黑气,已经几乎看不清以前的样子。我看到他茫然迟钝地找寻着什么,然后转头发现了这间屋子。就像先生说的,他只停顿了一下,便向着屋子走来,一步步,踏入阵法里。
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连空气都是寒冷的,我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呜咽哀嚎声,好像有无数双手拉着我陷入一个无尽的深渊里,里面没有任何温暖,只有绝望的黑暗。杀戮,暴虐,残忍……无数负面情绪海水一样涌上来,直接把我淹没——
我忍不住后退了几步,想要脱离绝境。
天旋地转。
我看见了秦奕,他贴着木门颤颤发抖,惊恐地看着我。
我看见屋外倒着一个人,那人穿着我的衣服,一只脚已经踏入阵法之中。
那现在的我是谁?
是傀儡,是我的傀儡。我替身到了自己的傀儡中,我,变成了我的傀儡……
我动不了,视线里忽然血红一片,好像眼睛里涌出了血。我想开口说话,下颌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生涩的机关。我忽然意识到,之前先生告诫我不要入阵,是因为,有真的“我”,就不需要一个,替身的,假的“我”。
“我被人缚在傀儡上了,救我,秦奕,救我——”
“……救?”
“过来,解开我的绳子,我就能离开了。”我不停说着,“解开我的绳子,救救我……”
秦奕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两步,却不再动了。
“秦奕!救我!过来——救我!救——”我疯狂地挣扎起来,无尽的恐惧侵蚀着我的意识。我不怕死,可我没想过这样死去。救我,放开我,让我离开阵法。我拼命地喊他,浑身抽搐着。
秦奕的眼睛瞪大,一张脸因为惊恐而扭曲着。
他大叫一声,掉头往外面冲去——
门外有无数的憧憧的人影,渐渐向屋子围拢过来,我又感觉到了怨恨的寒气,还有悉悉索索的说话声……
“救我——秦奕——”
“所以,你想告诉我,是秦奕杀死的唐晚么。”我从幻境中回过神来,我姑且把它当做一种幻境好了。
“你觉得哪个是真实的?”真武不答,反而看着我问道。
我揉着眉心,想驱散这些幻境所带来的头疼感。
“这都是他们魂魄最后的记忆。”真武又问,“你觉得什么是真实的?”
“记忆也有欺骗,眼睛所见的,不一定是真实。”
他便坐在我旁边,不再说话。
这些混乱而复杂的记忆里,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秦奕作为叛徒,被唐晚处决的,而后唐晚觉得事情蹊跷,才有给我的那封他不觉得秦奕叛变寒江城的信。秦奕死后变成厉鬼找唐晚索命,唐晚被应该由傀儡替他去死,然而却与傀儡互换了身份。
秦奕的记忆,是活着时候的记忆,还是魂魄未灭,死后的记忆?
我记得真武对唐晚说要去引到秦奕的鬼魂,如果秦奕看到的一切,只是他残存的执念,或者说作为鬼的身份所看到的,被阴阳先生引到着、希望他看到的,那秦奕记忆里的一切,便都是假的。
不,也有真实的地方。
秦奕记忆的最后才想起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
讽刺的是,秦奕的魂魄在幻象中一直觉得他害死了唐晚,对他有愧。然而他看到的傀儡却是真实的唐晚,他最后,也没有救他。
而傀儡中的唐晚,大约是入了鬼魂秦奕的魂魄中,连通了他的幻象。
“秦奕所看的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着这一切推波助澜又冷眼旁观的人。
真武也看着我,一双青白的眼睛坦然地没有任何波动:“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咽下要说出口的话,换了个问题:“如果秦奕放了傀儡,会怎样?”
“作为阵眼的魂魄,会吸引周围的鬼魂,被万鬼撕裂吞噬。”真武平静地回答道,“这个阵法,原本是为了除去厉鬼。”
他看似答非所问,我却出了一身冷汗。他原本想引秦奕的魂魄入阵,如果秦奕放了傀儡,他便会成为阵眼,被万鬼吞噬。可是,他没有。而原本应该只是个借了唐晚一点鲜血作为障眼法的傀儡,却阴差阳错,替身成了唐晚的魂魄。
“唐晚的,身体呢?”我艰难的问道。
真武没答,只越过我望着这座村子。我顺着他的视线去看,火烧过的地方是片片焦土,残垣断壁后隐着一座座孤坟,纸钱早化成灰烬,只有积年累月的落叶还被风吹着堆在墙角。
“人都是要死的。”他说,“早晚有什么区别。”
我和他相顾无言地枯坐了许久,我脑子里很空,苍白一片什么都想不出来;可又很乱,无数画面天马行空的跳跃着。
最后我拿出了那柄剑。
周燕然的断剑。
“请先生帮我。”
我第一次见到周燕然的时候才刚出师下山,他也是,还有不少年岁差不多的人,都是八荒师兄弟,很快便玩在了一起。四盟对于我们来讲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青龙会也与我们没特别大的关系,然而我们都痛恨青龙会,没有血海深仇,只是我们是正道,一腔热血的少年人们理应对邪派坏人深恶痛绝。为八荒正义而死,死得其所。
我与周燕然要好,他们都知道我俩关系亲近些,不过没人知道我们是那种要好。
平日里彬彬有礼称兄道弟,一副八荒弟子同气连枝的亲和。私下里脱了裤子滚到一处,偷偷摸摸睡一个被窝,亲个嘴跟偷情似的。他这人脸皮薄,明明成天一双眼净围着我打转了,找我说话竟然还说:“任师弟,能不能来切磋一下剑法。”
切磋好啊。不如切磋去床上。
刚开荤的毛头小子哪里憋得住,恨不得一有空就抓着机会搞一搞。有时候是他主动,有时候是我主动撩他。他这人撩着有意思,穿着衣服的时候像个清心寡欲的修道人,扒了那身道袍就原形毕露了。我是后悔第一次为了跟他搞上让了主动权,他还说下次换我,后来哪次不是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他搞我。反正搞熟了也不太在意这个了,他舒服,我也舒服。
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估计要跟他搞一辈子。
四盟联手剿灭血衣楼,那时候我也参与了。刚下山随着执行任务,那时候年轻功力浅,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江湖都记得最后是四盟赢了,血衣楼总楼不复存在。
没人会去在意先前大大小小的交锋。
那次我们本来只是去探查探查喽啰,没想到遇到展梦魂。我们死伤惨重,活下来的只有零星几人,也都重伤。我在嘉荫镇的医馆里躺了足足一月,连最后四盟与血衣楼的决战都没参与,还是后来有人说给我听的。
他们也不太愿意跟我讲这个事,没人怪我,只觉得我大约也不想回忆起那日的事情。
我是不想回忆的。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尚有一线生机,若是我们拼尽全力未必没有出路。周燕然苦苦支撑,他是我们之中功力最高的,也已经捉襟见肘。而那一刻是我害怕了,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我的剑慢了,再不像秦川的一剑寒光。我原本可以救他的,但最后却没有。
周燕然死了。
如果不是我,他也不会死。
是我害死了他。
没人再追究,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想尽办法忘掉他,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然而清醒过来之后仍是要披上一层认真谦和的皮相,做所有人都认为正常的事情。我在寒江城逐渐从新人变成了老人,踏实稳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伪装的多了,就好像真的忘了。
我看到了周燕然,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似乎是杭州城,我俩初识的地方。他眼眶里忽然就流出血泪,嘴巴张张合合,我听不见声音,却听懂他问我:“你为什么不陪我?”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药王殿残破的屋顶并不能遮挡,能直接看到晦暗的星光。空气里弥漫着香料的味道,我偏过头去看,香案里果然插着一支没烧完的香。
真武坐在一旁,他空着的剑匣横放在腿上。
“你醒了。”他知道我醒来了,“你后来昏过去了。”
“哦。”我看了看,地上的阵法已经模糊不清了,“先生,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不到。”真武转过头来,他又蒙住了眼,“只有你能看见。”
“是啊,我看见了。那是年轻时候的孽债。”我坐过去,靠进他怀里,伸手去解他蒙眼的带子。他由着我动作,黑色的布条徐徐落下,露着一双闭着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好看,两扇睫毛颤巍巍地眨了眨,而后缓缓睁开,露出一对没有瞳仁的眼珠。
“所以,先生,你又是谁呢?”
“先生,这世间的确没有什么法术,是能够重回过去的吧?”我问他,“可是你却可以让我看到已经过去的事情。”
“那是他们魂魄的记忆。”
“看见的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只是我心中所想?”
他用了一句我说过的话回我:“记忆也有欺骗,眼睛所见的,也不一定是真实。”他顿了顿,“更何况,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救他。”
“过去的事情不可改变。”
“我知道。”
那是藏在我心里的心结,心底最深的执念。
在周燕然死后我拼命想要忘记他的时候,这个执念却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的想着当时的场景,如果当时我没有怯弱,没有弃他不顾,而是坚定的站在他身边,替他分担伤害,结果又会怎样呢?
如果当时我救了呢?
也许,不一定是两个人都会死,没准就是一起活下来了呢?
可是也许呢?
如果是周燕然活了,我却死了。
如果是他,会选择救我么。
所以我到底应该救他吗。他死了,因为我,他死了。
我把这件事埋在心里谁都不知道,谁也不知这副皮囊下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又有着怎样令人不齿的肮脏过往。
我以为我都忘记了,连带着愧疚和自责一起。就像我整整十年都没想起过他,也没梦见过他一样。
我点燃了一支香。
药王殿里面的燃着的是引魂香,会让人陷入梦境。
我没有告诉真武,其实梦里见到周燕然的感觉挺好的。他还是当年的样子,我也就好像还是当年的样子,我们只是一群刚入盟会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发生,就不需要责任,不需要后悔,不需要愧疚。
也不需要去挽回什么。
我又梦见他了。
“阿凉!你总算醒了。”周燕然的大脸出现在我眼前,他伸手,在我眼前使劲晃了晃,“怎么了?睡傻了啊。”
“燕子……”
“啊?”周燕然正去倒水,应声回头。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是周燕然,他穿着一身画水微明袍,是下山前新得的,穿上不久,宝贝得不得了。他脸上青青紫紫的带着伤,手臂也吊在胸前,一只手做事不太习惯。
“先喝点水,等会儿我去找温姑娘给你拿个药方。”他这人就这样,平日里不怎么说话,跟亲近人说起话来絮絮叨叨的像个老妈子,“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啊,估计得在床上躺好久。哎哎,躺好,别乱动。”
茶水是温的。
他还在念叨:“你啊,吓死我了,打起架来怎么不要命呢。不过你们太白不愧是剑宗大师,真是厉害,那会儿我已经要撑不住了,要不是你过来接手,我也撑不到下一个离渊……”
我有点愣神地看着他,周燕然能活动的那只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们的额头抵在一起,他低声说着:“阿凉,谢谢。”
我听见了他的心跳声,也许是我的,噗通噗通,融合在一起。
原来劫后余生是这样的美好。
“燕子。”我去吻他的唇,心里躁动得厉害,他也好像一点就着的干柴,回应我的亲吻,越来越急躁,牙齿磕在嘴唇上,好像磕破了。我不自觉地去舔,被他含住舌头,纠缠在一起。
我忍不住伸手去解他的衣服,手伸进去摸他的身体,手掌下是皮肤温热的触感。我推着他坐到床上,他一只手还在胸前吊着,不方便动作,衣服也解不开。
“阿凉你别乱动,你伤还没好。嘶——”
我翻身跨坐在他腰上,一边避开他的手臂,一边伸手去扒他的裤腰。身上的伤势挺疼的,动一动就扯着半边身体,但是根本不用在意。
我低头去吻他的唇,抬腰去摩擦他胯间。
“别告诉我你不想,那顶着我的是什么?剑鞘吗。”
他就笑了。
我恍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有什么念头一闪而过。我们在床上亲吻,搞在一起,真实而满足,我忽然觉得我估计会跟周燕然搞一辈子。
“怎么了?”周燕然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欲望,我熟悉极了,每次撩拨他,他忍不住的时候便是这样。
“我好像做了个梦。”我去吻他,搂着他的肩膀,咬他的喉结,听他嗓子里发出的低哼声,“但是不记得了。”
真武看着沉浸在睡梦中的人,伸手掐灭了焚着的引魂香。
贪恋梦境的人不愿意醒来。
他推开门,正是早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与每一日没有什么不同。
有人看见了他,投来些奇怪的目光。他是有些奇怪的,穿着一身朴素的道袍,眼睛上蒙着黑布条,却好像正常人一样,脚步丝毫不受影响。他背上有一副宽阔的剑匣,大约能容纳两柄剑。剑匣中却只有一柄,虽然剑柄上也雕着花纹,可看上去却有些残破了。
道士走出了镇子。
恍惚传来了一阵歌声,道士一边走,一边低声唱着一首诡秘又陌生的曲调。
评论 ( 1 )
热度 ( 41 )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头像是长阳给画的萧姑娘=w=
剑三:ALL花,爱生活爱花哥。
天刀:主真白,真唐,白唐。
FF14:猫相关各种,猫男艾欧泽亚总受。
梦间集:曦月x孤剑主。孤剑哥哥真是太美好了&&
多年老马甲,欢迎熟人来打招呼
&&Powered by
大魔王想看的阴阳先生paro,讲个没头没尾的灵异故事。
虽然迟到了2天,但是飞天小白兔搏仔生日快乐。
再也不想在半夜一点写鬼故事了
#真白#阴阳先生
我接到秦奕和唐晚的死讯的时候愣了一下。
唐晚的密信还放在我桌上,信里说道他不觉得秦奕叛变了寒江城,这件事有蹊跷。我了解唐晚,他对寒江城异常衷心,从不会去质疑寒江城的任何任务。他与秦奕同年入盟会,关系不近不远,合作过几次,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他也不会轻易替人开口说话。
何况秦奕死了,唐晚也死了。
手下来报告说最后一次接到他们的消息是在九华,从燕来镇离开往南面去,沿着鹧鸪岭,应该还没过江,江音……
我打断他,不想听他继续说。
江音畔的北边有些小村子。
过江,江音畔南面是血衣楼的旧址。十年前四盟终于攻破血衣楼总楼。
这我都知道,不用别人来跟我说。
出燕来镇往西南去是嘉荫镇,当初四盟暂时把它当做驻地。燕来镇外有一片山岭,不算陡峭,叫鹧鸪岭。对月峰山脚下有个药王庄,药王庄外不远是药王殿,供着药王孙思邈。据说是唐初时候的建筑了,也没人知道个具体年份,大殿里供着泥塑。都说当年因为鹧鸪岭上多药草,药王尝百草,为周围百姓除病解痛,便修了这座药王殿。
如今不管是药王庄还是药王殿都早成了废墟。
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药王的泥塑还在,大殿坍塌了一般,露着残败的屋顶。泥塑也毁了大半,上身没了,裂着个大口子,颜料都被风吹雨淋冲刷得所剩无几,露着灰白的泥胎。塑像前竟然还留着香案,被端正地摆放着,不知道什么人来过,香炉的泥里有三支燃尽了的香,香灰还在。不知道是什么香,味道有些奇怪。
药王庄以前是个不大的村子,早在十年前就没了活人,一把火烧得干净,化成一座座无主的孤坟。
村子早就看不清原样的街道上落着些纸张的余烬,还有些没烧干净的、糙黄色的纸钱。这些冥物出现在这样一座荒村,说不出的落魄,又说不出的诡异。
我心中起疑,越发觉得蹊跷。不知道是什么人来为荒岭孤村祭扫,甚至还毕恭毕敬的燃了三炷香。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跟我要查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或是十年前的旧人。
起风了,黄白的纸钱与陈年落叶一起在破碎的青石砖上滚动,堆在残垣断壁的墙角。风穿过满是窟窿的焦黑墙壁,呜呜响的像鬼哭。现在才未时,正午刚过,烈日还没落下去,没可能有百鬼夜哭。我握紧了手中的剑,纸钱被风吹动卡在我鞋子上,我挪开脚,它又滚去了一边。我不知道这村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人,活人,像我一样的。
毕竟我脚下还有影子。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人。
他坐在村中央的大树下摆弄着什么,这是唯一一片阴凉,树影在他衣服上投下一些斑驳,映得他遮着黑布的脸忽明忽暗。他手边放着一摞摞的纸钱,脚边有一堆灰烬,火已经熄灭了,大约是先前烧的。
他看到我了,抬头,向着我的方向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
但凡每个门派里都有些剑走偏锋,或是特立独行的弟子。真武修道,不修仙,但也不忌鬼神。张真人在襄州山中偶遇疯疯癫癫的扶摇子,得其点化,习得驱影之术。之前曾有人跟我讲过驱影,也给我看过他的影。后来我在寒江城,也有不少真武弟子前来。气也罢,鬼也罢,我多少对真武的人有些抵触。
这人我却认识。也不算认识,只是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他是谁。
会算命的道士在江湖上总容易成为两种,一种是江湖骗子,一种是铁口半仙。真武出了一个弟子,他背后的剑匣是空的,但是可以以气御剑;他的影是无形的,又可以化作任何形态;他通晓阴阳,熟知阵法,擅长一切鬼怪之事,能入得生魂,也能招来死灵。他的眼睛是盲的,常年覆着条黑布,有人见过他的眼睛,瞳仁散去只有苍白的眼珠,好像能窥透魂魄。便传闻他心眼通灵,所以才能穿越阴阳两地,出入黄泉。
他们喊他阴阳先生。
“先生。”我喊他,“先生在此做什么?”
他似乎听了什么奇怪的事,转头“看”着我。他看不见的,但是我觉得他看得见,像是在打量着我。
“超度亡灵。”
“什么亡灵。”我又问。这里是一片死地,十年前四盟与血衣楼在这里有过一次对战,四盟不敌,血衣楼屠尽镇子,一把火烧了所有,处处都是亡灵。可我知道他能听懂,不是只有十年前,我看见那一摞摞的纸钱上压着一柄折扇,扇子上挂着一个剑穗。
扇子不是江南公子哥手中附庸风雅的折扇,寒铁骨,天蚕绢,绘着万青竹海。剑穗也不是普通的穗子,盘长结配碧青丝,雕了忍冬纹的珊瑚珠,挂在落羽剑上。
“人都是要死的。”他回了我的话,“早晚有什么区别。”
我走在一片灰无的色彩里。
好像滴落在笔洗中的墨点,一层层晕开,化成丝丝缠缠的雾气,又最终与周围融为一体。也许有什么景色,也许这世界有色彩,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也并不在意。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竟然也没有任何好奇或是疑惑的感觉,心里异常平静,只好像我哪里并不关系。忽然我看到了些人,憧憧人影,我心里就高兴了起来,并没原因,只是看到了就高兴,像十几岁还在山上时候一样,或是刚出师入江湖时候。我去与他们说话,看不清是谁,面容模糊着,可我又清晰的知道我“认识”他们。
画面忽一转不再是秦川的泼墨。
我身边站着一人,一身灰白的袍子,背着一副剑匣,匣子里两柄剑,一长一短,他在这并无色彩的画面里却好像带着流光溢彩。我走着他身边说着什么话,又急又快,高兴极了,好像生怕自己说不完,不能都讲给他听似的。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也不知道走去哪里。
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他的手掌抚在我后颈上。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愣了半天,脑子渐渐清醒,梦里的场景便迅速散去了。也没有全部散去,还留了些模糊不清的影,在梦里的我分辨不出,然而梦醒之后的我却忽然意识到梦里的人是谁了。
是周燕然。
他曾经与我讲过,他名字是母亲取得,母亲就喜欢李太白的诗,取了“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也有十年没有梦见过他了。
天亮之后我又回了药王庄。
真武竟然还在,他盘腿坐在药王殿的大殿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香炉里有新插的香,幽幽地飘着三道青烟,是我上次来时候闻见的那个味道。殿外也有不少纸灰,想必是他又烧了不少纸钱。
他知道我来了,抬起头“看”我。
他今日没蒙着黑绸带,被一双青白没有瞳仁的眼睛直视,在太阳下都教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我信他是真能看透灵魂的。
“先生。”我喊他。
“你回来了。”他答。
“先生……似乎是知道我会回来?”我小心翼翼地问。
“嗯。”他并无意外,“所以我在等你。”
“等我做什么?”
“你身上有一把剑。”真武仍然那么看着我。
我身上的确有。
我完全可以告诉他:我是太白弟子,我身上当然会带着剑,剑是我所傍身的武器,没有任何太白弟子会不佩剑行走。
但是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我手上的那把,他“看”得到。
我对他并不信任,他身上有唐晚的扇子和秦奕的剑穗,平白出现在他俩失踪亡故的地方,纵使江湖都知道他阴阳先生的名号,也不足以让我不对他太过巧合的出现产生怀疑。那日我试探他,不确定我所看的扇子与剑穗,是他有意对我暗示什么,还是根本自信到无需隐藏。
我也有所隐瞒。
我在药王庄中发现了一个诡异而残破的阵法,不知道是朱砂还是血画的咒文,蔓延开来,干涸在砖石地板上。阵中插着一把残剑,剑锋早就没了,剑刃也残缺豁口,却硬生生地嵌入进了砖石,削铁如泥里。
我不懂阵法,不知道这柄剑是入阵,还是破阵。
我看着那柄剑,隐约有些什么想法,又想不真切。大约是因为用剑之人都好剑,那柄剑我便带在身上,想知道这是怎样一把剑。
从那夜开始我每晚便陷入光怪陆离的诡异梦境。醒来却丝毫记不真切,只记得那种在梦境中穿梭的,不真实却又异常熟悉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梦见年轻时候的事了,每晚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清晰。
我终于在梦里见到了周燕然,他仍然背着双剑,剑柄上的纹路有些眼熟。我醒来后去看,才惊觉,那柄残剑的花纹与梦中的花纹一摸一样。
竟是当初周燕然的佩剑。
“人的魂魄会残留或是依附在一些亲近的器物上。”真武毫不在意我的怀疑,语气平静,一板一眼好似讲学。他伸手捏了个剑诀,我警惕地盯着他的动作,只觉有一道剑气,他手臂上便多了个血口子。鲜血混合着朱砂一起,他眼睛明明看不见,却画得很快,反复的咒文不一会儿便在他周身铺开。
“入了他人的魂魄,便像是成为了那个人,用他的眼睛,看到他的记忆。”真武说着,把秦奕的剑穗放入阵眼。“你想知道什么,不如自己去看。”
“我为什么要信你。”
真武看着我,伸出手,把命门暴露在我眼前。习武之人绝不会做出这样轻率的动作,如果我想,以我的剑速,一招便可以取他性命。他毫不设防,如果我真扣住他的命门,别说我自负武功不弱,即使是稚子幼儿,也能将他重伤。
我在他身边坐下,伸手扣住他的脉门。
我又忍不住攥紧了荷包,感觉心噗通噗通地跳,简直要跳出嗓子。我手上都是汗,身上也是,脸上也有,猛地拿袖子擦了一把才好一点。
我已经是第七次回到这个地方了。我确信我没有走错路,然而我也确信,我的确是被鬼打墙困在这里了。
我不停地摸着荷包,能摸到辟邪符的轮廓,这让我心安了一点。但马上又绝望起来——先生给的辟邪符都已经不能阻挡这一切了。先生当初就说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跟在我身边的“人”只会有所忌惮,但是并不惧怕。要想真的解决这一切,除非找到真正的“因果”。然而先生所说的事情还没办法,我已经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我奉盟会的命令来送信,信送到了,却怎么都走不出这个镇子了。
太阳已经西沉到最后一抹余晖,我虽不懂也知道这马上要到阴阳交替的时刻,如果我还走不出去,入夜之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菩萨保佑……佛祖保佑……”我哆哆嗦嗦地念叨着,“其实什么都好啊,保佑我……啊啊啊!”
忽然身后有响动,我吓得立刻抽出剑往后刺去,不管什么牛鬼蛇神都要抢得先机才有活路!剑却好像扎进了一团气里——是一个人,却也不是“人”,是一团墨影,化作人形,轻巧地便化解了我的剑招。
待我看清是谁,简直要喜极而泣了。
“先、先生!救我!”
先生点了点头,收了他的影,说了句“跟上”,便在前面引路去了。说也奇怪,明明都是同样的路,在他脚下却好似有什么指引,在岔路并不停顿,带着我转过了晕头转向的路口。我紧紧跟着他,一刻都不敢放松,待我回过神来发现他停下,已经走出刚才的迷阵,回到了镇子口。我认得这里,镇口有个驿站,我的马匹和行李还在驿站的房间里。
太阳马上要消失了。
“回屋里。”先生说,“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门。”
入夜之后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提心吊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听见门外有悉悉索索的响动,好像有人在走。那脚步声规律极了,似乎是在门口徘徊,时近时远。不一会儿便又有些其他声音,像是小声交谈又听不清楚,仔细听又像是唱歌。这些声音都似乎在门外很远的地方,越听便越多了起来。
我心中有些好奇,有个声音不断诱惑着,但我记得先生说过的话。
门外的响动让我想起志怪传说中的百鬼夜行,我想起先生告诫的是不能出门,我忍不住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顺着门缝偷偷地,往外看了一眼。
外面是漆黑的夜,什么都没有。
我不由得失望了,回身坐回床上准备继续睡觉。我这才发觉周围静极了,连我自己呼吸吐纳的声音都听得清晰,先前那些嘈杂的响声,一点都没有了。
我不由得心惊,抓起放在床头的剑,又回到门口小心翼翼地看过去。门缝里,一个青白的、不似活人的眼珠正一动不动地也同样看着我。
“啊啊啊啊啊——”
我手忙脚乱地跌倒在地,门忽然开了,外面空荡荡的,院子里没有一点光亮。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顾不上,只想着逃离这个地方,抓起剑便往外冲去。
午夜的街道上原本应该空无一人,此刻却有些人影,街上也点了不少暖黄色的灯火,在这诡异的夜里好像给人一点安宁。我看着那些灯光,忽然觉得有些镇定了,这才有精力去看街上的人。
这些人,迈着一模一样的步伐。
他们都转过头来看我。
一模一样的脸,青白的、不似活人的眼珠。
“破——”
真言之后有什么东西从头到脚地把我笼在里面,我惊魂未定,僵着身子转头去看,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形的墨影,摆出云手的姿势。
我猛地回身去看,果然是先生。我此刻喜出望外,只觉得绝处逢生,浑身汗湿的像从水中捞起来。先生脸色不好,像是消耗了许多心力。我愧疚极了,是我未听警告,连累了先生以身犯险。
“跟我走。”
先生带着我到了个暂时安全的地方停下,问道:“这个镇子上全是傀儡,傀儡发现了你的踪迹,要向你索命。你且告诉我,你与唐门有何恩怨?”
我早就该知道的,我自问平生未负他人,只对不起一个人。但是这是我隐藏在心底最肮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去,就像是曝晒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不说,我无法破阵。”
“我……”我咬牙,闭眼说道,“他叫唐晚,是我在寒江城的一个同伴。之前曾经有一次,我们一起出任务,然后落入险境。在……我可以救他,的时候,我……”我说出来,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我不是不想救他!我只是——”
先生打断了我的话:“他的执念是‘救’,附身在傀儡上。要找到他的傀儡,才能破阵。”
先生带着我一路在镇子里穿梭,我心里反复想着被截断了的,没说出口的话。我不是不想救唐晚,只是人性中总有懦弱的一面,也总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我承认在那一刻是我害了他,我出卖了他。可是我不确定,如果身份置换,由唐晚在我的位置,我们两个人能不能都活——所以我活着,唐晚死了。
“先生?先生?”我一惊,不知什么时候身边竟然没人了,先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竟然在这种时刻,和先生走散了。我茫然地看着四周,夜里的镇子好像与白天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这里套着层层鬼阵,危机四伏。我看不懂——当然看不懂,只能握紧手中的剑,好像这样能给多一份力气。
我决定等先生来找我。
街道上太危险,我看到右手边好像有间废屋,刚一躲进去便后悔了。
屋子里布满了傀儡丝,本该透明的丝线上染满了血。不,不仅如此。一个傀儡被纠缠着吊在半空中,垂着头,却好像是真人一样,源源不断的流着血。血从它身上滴滴答答的落下来——那滴落的声音太清晰,好像生命的滴漏在倒数计时。它赤着脚,流下来的血顺着他脚尖在地上汇成一个诡异的阵法,隐隐泛着红光。
这个傀儡,是唐晚的。
我手足无措,回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门竟然关上了。我使劲推着,单薄的木门却纹丝不动。我只得回过身,贴着木门,惊恐地看着唐晚的傀儡。
“我一直在等你……”它开口了,是唐晚的声音,缓缓抬起头,七窍流血,但竟然是唐晚的脸,“我被人缚在傀儡上了,救我,秦奕,救我——”
“……救?”我颤声问他。
“过来,解开我的绳子,我就能离开了。”傀儡唐晚说着,“解开我的绳子,救救我……”
我想起先生说的话,深吸一口气强行镇定一下,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过去。唐晚的双眼流着血,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嘴巴开开合合,血不断地涌出来。
“来……救我……过来……”
我看着他,越近便越觉得害怕极了,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站在他面前三步的距离,怎么,也走不动了。
“秦奕!救我!过来——救我!救——”唐晚越发疯狂地挣扎起来,浑身抽搐着,声音变得尖锐急促,随着他的挣扎,勒紧的傀儡丝割开他的皮肤,流下更多的血。
我再也顾不上其他,转身向门口跑,用尽浑身力气去撞——
门开着,外面大亮着,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挑担叫卖的货郎,驿站赶车的车夫,结伴去洗衣的村妇,一切都正常的很,只有我茫然地站在街上,格格不入。
“太白小哥,你让我打听的人,我给你打听到啦。”是驿馆的小二,有些好奇的打量我,“怎么了?”
“没……”我回头去看,敞开的房门里什么都没有,“没事。”
我是做了个梦?
我伸手去摸,怀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却是一封信,印着寒江城的记号。我恍惚记得这封信已经送出去了的,怎么还在手上?
“你说打听到了什么?”
小二一五一十说了,就是我要找的接头人,好去获得与收信人的联络方式。
我有些茫然地看着信,只得再送一次。我找到接头人,依约去指定地点。我还是没太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打开荷包,里面并没有什么辟邪的符咒。也许真是一场噩梦?
身后有脚步声,我刚想回头,忽然胸口一凉——
一柄利刃而出,疼痛瞬间袭来,再也感觉不到别的。我挣扎着回头去看,是一个傀儡,我认得,是唐晚的傀儡!
唐晚蹲下来:“抱歉。但是叛变寒江城的人,一个不留。”
是了,我死了。我被人诬陷是青龙会的暗桩,不,不是的——我——
我睁开眼,强烈的恨意好像要将我拖入一个无尽深渊里。这感觉就像溺水者在拼命挣扎,却只能把自己陷得更深。我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能平息那份怨恨,让自己有一种“活过来”了的感觉。
真武还坐在我旁边,安静的,转头“打量”着我,伸手取走了阵眼中秦奕的剑穗收回怀里。
“是唐晚处决的秦奕。”我说,“那秦奕记忆里,他杀死的人是谁?唐晚又是谁杀的?”
真武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把唐晚的扇子放入阵眼,淡声说道:“看。”
秦奕死后我第一次“见”到了鬼。
其实并不没有看见,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阴阳通灵的本事。我原本也是对鬼神之说不怎么相信的,虽然我也认为这世上一定就没有。不过传说中的许多事都少不了装神弄鬼和添油加醋的成分。就像我可以用无影丝操纵傀儡,让它像活人一样。还有同门的傀儡做的活灵活现,尤其是一双眼,都说画龙点睛,也许它因为那么一双眼睛有了灵魂也说不准。
我说见到鬼,是因为我的确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东西”在跟着我。最初我怀疑是被人跟踪了,也许是四盟的人,也许是青龙会的余孽。因为从秦奕死后,我开始查他背叛的原因,那种被人“看着”的感觉就一直挥散不去。可是我警惕了几日,并没有发现跟踪的人。我自认也非刚入江湖的毛头小子,不会轻易着了别人的道,我真的没有发现,若不是对方武功太高已经可以在我面前完全隐藏行踪,那便只有另一个我并不太相信的解释,也许一直看着我的,并不是“人”。
而后好像是要证实似的,我身边接二连三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事情。
先是东西无缘无故的破碎,而后还有失踪。我确信我没有出错却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又或是在一处来回打转。我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而周围的人并无异常,好像只有我一人能听见一样。我的傀儡咯咯地笑了,好像关节机关涩住了需要上油的那种声音,待我再仔细去分辨,却又完全没有异常。
而那种被监视着的感觉总也挥之不去。
我在燕来镇外遇见了阴阳先生。
我认识他,先前也见过他,听说过他的许多事情。我见识过他的手段,也许这就是我对鬼神之事尚有几分信任的原因。他与江湖上那些算命的道士半仙不同,那些人总经常把你说得大难临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懂什么,十有八九只是骗钱。先生从不主动说,只问:“你想要做什么。”可一切他早就已经知晓了。
所以我问他:“先生,我是不是被鬼怪缠上了。”
“是。”他回答,“你想怎样?”
“我想见他。”
正是黄昏阴阳交替的时候,先生点燃了一张符箓,它烧起来的时候竟然没有火,却燃起来一阵青烟。我回头去看,稻田的田埂上隐约有一个人形,随着青烟越来越明显起来。它穿一身短衫,领口袖口缀着些毛绒,头发梳高束成发髻,手上拿着一柄剑。它似乎看到了我们,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
它明明并没有面容,我却清晰地察觉到了那两道视线。
忽然它动了!
他出剑,带起一阵冰冷的剑气,脚尖一点瞬时便冲到我们眼前。我一惊条件反射地傀儡出手,然而无影丝直接穿过了它的身体——它并没有,有形的身体!
我视线一花,眼前又出现了一道人影。墨影挡在我们面前,出鞘的剑挡下鬼的剑。两道影子撞在一起,须臾便分开了。明明什么都没有,我却清晰地听见了兵刃碰撞的金鸣声。是先生的影,他用剑气驱动影子阻挡着鬼的攻击,两个没有实体的人形打得难解难分,剑招纷乱。鬼左右进攻都破不了影的防守,不由得厉声大叫——是的,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尖锐刺耳的喊声,随着它的声音,它模糊的身形好像笼着一团团的雾气,瞬时膨胀起来。
我却忽然看不见了。
“先生?”我扭头去看,先生手里的符箓已经燃尽,化作灰沫粘在他手指间。他并没有回我的话,而是皱着眉盯着一处。我看不见,我知道他看得见。
半晌,先生的影才化为一团雾气消散不见。
随即那种阴冷瘆人的鬼气也散去了,只有被人注视的感觉还在。
“你认识他。”先生用的是肯定的语气。
“认识。”我回答,“我也猜到如果真是来复仇的索命鬼,应该就是他吧。他叫秦奕,原本是我在寒江城的同伴。”我顿了顿,“他叛变,也是我杀了他。”
期间还涉及到四盟与寒江城的一些秘密,先生不问,也并不关心这些。他只问道:“他死在何处,尸体在哪儿?”
“往南面的鹧鸪岭。我念及同盟情谊,就地埋了。”
“鹧鸪岭。”
我觉得先生好像忽然笑了一下,再仔细看,却又像是我的错觉。
药王庄有些鬼气森森。
“十年前这里被血衣楼屠村,所以怨气滔天。”先生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秦奕被你杀死后心存怨恨,又吸收了鹧鸪岭的怨气,所以成为了,你们所说的,厉鬼。”
“它跟着我是要杀我复仇,为何一直没有动手?”
“燕来镇的阳气太重。”
“先生可是有办法除掉它?”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或是收服它?”
先生看着我,摇了摇头,不多做解释:“它戾气太重。”
“先生既然带我来此,肯定自有打算。”
“它要‘你’死,只要你死了,它的怨气自然就会散去。”先生咬了个重音,“有‘人’可以代替你死。”
我看着傀儡箱,忽然明白过来:“先生指,我的傀儡。”
先生用朱砂在地上画着符咒阵法,解释道:“鬼并不能分辨出人,它一直追着你的魂魄,被你的魂魄吸引。把傀儡放在阵法中,将你的血点在它额头和心口,作为你的替身,瞒天过海。”
“我引它来,它被你的生魂吸引,自然会入阵。”先生强调道,“只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要踏入阵法里。”
秦奕来了。
应该是秦奕的鬼来了。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一个鬼。他面容模糊,周身黑气,已经几乎看不清以前的样子。我看到他茫然迟钝地找寻着什么,然后转头发现了这间屋子。就像先生说的,他只停顿了一下,便向着屋子走来,一步步,踏入阵法里。
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连空气都是寒冷的,我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呜咽哀嚎声,好像有无数双手拉着我陷入一个无尽的深渊里,里面没有任何温暖,只有绝望的黑暗。杀戮,暴虐,残忍……无数负面情绪海水一样涌上来,直接把我淹没——
我忍不住后退了几步,想要脱离绝境。
天旋地转。
我看见了秦奕,他贴着木门颤颤发抖,惊恐地看着我。
我看见屋外倒着一个人,那人穿着我的衣服,一只脚已经踏入阵法之中。
那现在的我是谁?
是傀儡,是我的傀儡。我替身到了自己的傀儡中,我,变成了我的傀儡……
我动不了,视线里忽然血红一片,好像眼睛里涌出了血。我想开口说话,下颌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生涩的机关。我忽然意识到,之前先生告诫我不要入阵,是因为,有真的“我”,就不需要一个,替身的,假的“我”。
“我被人缚在傀儡上了,救我,秦奕,救我——”
“……救?”
“过来,解开我的绳子,我就能离开了。”我不停说着,“解开我的绳子,救救我……”
秦奕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两步,却不再动了。
“秦奕!救我!过来——救我!救——”我疯狂地挣扎起来,无尽的恐惧侵蚀着我的意识。我不怕死,可我没想过这样死去。救我,放开我,让我离开阵法。我拼命地喊他,浑身抽搐着。
秦奕的眼睛瞪大,一张脸因为惊恐而扭曲着。
他大叫一声,掉头往外面冲去——
门外有无数的憧憧的人影,渐渐向屋子围拢过来,我又感觉到了怨恨的寒气,还有悉悉索索的说话声……
“救我——秦奕——”
“所以,你想告诉我,是秦奕杀死的唐晚么。”我从幻境中回过神来,我姑且把它当做一种幻境好了。
“你觉得哪个是真实的?”真武不答,反而看着我问道。
我揉着眉心,想驱散这些幻境所带来的头疼感。
“这都是他们魂魄最后的记忆。”真武又问,“你觉得什么是真实的?”
“记忆也有欺骗,眼睛所见的,不一定是真实。”
他便坐在我旁边,不再说话。
这些混乱而复杂的记忆里,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秦奕作为叛徒,被唐晚处决的,而后唐晚觉得事情蹊跷,才有给我的那封他不觉得秦奕叛变寒江城的信。秦奕死后变成厉鬼找唐晚索命,唐晚被应该由傀儡替他去死,然而却与傀儡互换了身份。
秦奕的记忆,是活着时候的记忆,还是魂魄未灭,死后的记忆?
我记得真武对唐晚说要去引到秦奕的鬼魂,如果秦奕看到的一切,只是他残存的执念,或者说作为鬼的身份所看到的,被阴阳先生引到着、希望他看到的,那秦奕记忆里的一切,便都是假的。
不,也有真实的地方。
秦奕记忆的最后才想起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
讽刺的是,秦奕的魂魄在幻象中一直觉得他害死了唐晚,对他有愧。然而他看到的傀儡却是真实的唐晚,他最后,也没有救他。
而傀儡中的唐晚,大约是入了鬼魂秦奕的魂魄中,连通了他的幻象。
“秦奕所看的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着这一切推波助澜又冷眼旁观的人。
真武也看着我,一双青白的眼睛坦然地没有任何波动:“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咽下要说出口的话,换了个问题:“如果秦奕放了傀儡,会怎样?”
“作为阵眼的魂魄,会吸引周围的鬼魂,被万鬼撕裂吞噬。”真武平静地回答道,“这个阵法,原本是为了除去厉鬼。”
他看似答非所问,我却出了一身冷汗。他原本想引秦奕的魂魄入阵,如果秦奕放了傀儡,他便会成为阵眼,被万鬼吞噬。可是,他没有。而原本应该只是个借了唐晚一点鲜血作为障眼法的傀儡,却阴差阳错,替身成了唐晚的魂魄。
“唐晚的,身体呢?”我艰难的问道。
真武没答,只越过我望着这座村子。我顺着他的视线去看,火烧过的地方是片片焦土,残垣断壁后隐着一座座孤坟,纸钱早化成灰烬,只有积年累月的落叶还被风吹着堆在墙角。
“人都是要死的。”他说,“早晚有什么区别。”
我和他相顾无言地枯坐了许久,我脑子里很空,苍白一片什么都想不出来;可又很乱,无数画面天马行空的跳跃着。
最后我拿出了那柄剑。
周燕然的断剑。
“请先生帮我。”
我第一次见到周燕然的时候才刚出师下山,他也是,还有不少年岁差不多的人,都是八荒师兄弟,很快便玩在了一起。四盟对于我们来讲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青龙会也与我们没特别大的关系,然而我们都痛恨青龙会,没有血海深仇,只是我们是正道,一腔热血的少年人们理应对邪派坏人深恶痛绝。为八荒正义而死,死得其所。
我与周燕然要好,他们都知道我俩关系亲近些,不过没人知道我们是那种要好。
平日里彬彬有礼称兄道弟,一副八荒弟子同气连枝的亲和。私下里脱了裤子滚到一处,偷偷摸摸睡一个被窝,亲个嘴跟偷情似的。他这人脸皮薄,明明成天一双眼净围着我打转了,找我说话竟然还说:“任师弟,能不能来切磋一下剑法。”
切磋好啊。不如切磋去床上。
刚开荤的毛头小子哪里憋得住,恨不得一有空就抓着机会搞一搞。有时候是他主动,有时候是我主动撩他。他这人撩着有意思,穿着衣服的时候像个清心寡欲的修道人,扒了那身道袍就原形毕露了。我是后悔第一次为了跟他搞上让了主动权,他还说下次换我,后来哪次不是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他搞我。反正搞熟了也不太在意这个了,他舒服,我也舒服。
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估计要跟他搞一辈子。
四盟联手剿灭血衣楼,那时候我也参与了。刚下山随着执行任务,那时候年轻功力浅,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江湖都记得最后是四盟赢了,血衣楼总楼不复存在。
没人会去在意先前大大小小的交锋。
那次我们本来只是去探查探查喽啰,没想到遇到展梦魂。我们死伤惨重,活下来的只有零星几人,也都重伤。我在嘉荫镇的医馆里躺了足足一月,连最后四盟与血衣楼的决战都没参与,还是后来有人说给我听的。
他们也不太愿意跟我讲这个事,没人怪我,只觉得我大约也不想回忆起那日的事情。
我是不想回忆的。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尚有一线生机,若是我们拼尽全力未必没有出路。周燕然苦苦支撑,他是我们之中功力最高的,也已经捉襟见肘。而那一刻是我害怕了,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我的剑慢了,再不像秦川的一剑寒光。我原本可以救他的,但最后却没有。
周燕然死了。
如果不是我,他也不会死。
是我害死了他。
没人再追究,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想尽办法忘掉他,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然而清醒过来之后仍是要披上一层认真谦和的皮相,做所有人都认为正常的事情。我在寒江城逐渐从新人变成了老人,踏实稳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伪装的多了,就好像真的忘了。
我看到了周燕然,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似乎是杭州城,我俩初识的地方。他眼眶里忽然就流出血泪,嘴巴张张合合,我听不见声音,却听懂他问我:“你为什么不陪我?”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药王殿残破的屋顶并不能遮挡,能直接看到晦暗的星光。空气里弥漫着香料的味道,我偏过头去看,香案里果然插着一支没烧完的香。
真武坐在一旁,他空着的剑匣横放在腿上。
“你醒了。”他知道我醒来了,“你后来昏过去了。”
“哦。”我看了看,地上的阵法已经模糊不清了,“先生,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不到。”真武转过头来,他又蒙住了眼,“只有你能看见。”
“是啊,我看见了。那是年轻时候的孽债。”我坐过去,靠进他怀里,伸手去解他蒙眼的带子。他由着我动作,黑色的布条徐徐落下,露着一双闭着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好看,两扇睫毛颤巍巍地眨了眨,而后缓缓睁开,露出一对没有瞳仁的眼珠。
“所以,先生,你又是谁呢?”
“先生,这世间的确没有什么法术,是能够重回过去的吧?”我问他,“可是你却可以让我看到已经过去的事情。”
“那是他们魂魄的记忆。”
“看见的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只是我心中所想?”
他用了一句我说过的话回我:“记忆也有欺骗,眼睛所见的,也不一定是真实。”他顿了顿,“更何况,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救他。”
“过去的事情不可改变。”
“我知道。”
那是藏在我心里的心结,心底最深的执念。
在周燕然死后我拼命想要忘记他的时候,这个执念却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的想着当时的场景,如果当时我没有怯弱,没有弃他不顾,而是坚定的站在他身边,替他分担伤害,结果又会怎样呢?
如果当时我救了呢?
也许,不一定是两个人都会死,没准就是一起活下来了呢?
可是也许呢?
如果是周燕然活了,我却死了。
如果是他,会选择救我么。
所以我到底应该救他吗。他死了,因为我,他死了。
我把这件事埋在心里谁都不知道,谁也不知这副皮囊下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又有着怎样令人不齿的肮脏过往。
我以为我都忘记了,连带着愧疚和自责一起。就像我整整十年都没想起过他,也没梦见过他一样。
我点燃了一支香。
药王殿里面的燃着的是引魂香,会让人陷入梦境。
我没有告诉真武,其实梦里见到周燕然的感觉挺好的。他还是当年的样子,我也就好像还是当年的样子,我们只是一群刚入盟会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发生,就不需要责任,不需要后悔,不需要愧疚。
也不需要去挽回什么。
我又梦见他了。
“阿凉!你总算醒了。”周燕然的大脸出现在我眼前,他伸手,在我眼前使劲晃了晃,“怎么了?睡傻了啊。”
“燕子……”
“啊?”周燕然正去倒水,应声回头。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是周燕然,他穿着一身画水微明袍,是下山前新得的,穿上不久,宝贝得不得了。他脸上青青紫紫的带着伤,手臂也吊在胸前,一只手做事不太习惯。
“先喝点水,等会儿我去找温姑娘给你拿个药方。”他这人就这样,平日里不怎么说话,跟亲近人说起话来絮絮叨叨的像个老妈子,“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啊,估计得在床上躺好久。哎哎,躺好,别乱动。”
茶水是温的。
他还在念叨:“你啊,吓死我了,打起架来怎么不要命呢。不过你们太白不愧是剑宗大师,真是厉害,那会儿我已经要撑不住了,要不是你过来接手,我也撑不到下一个离渊……”
我有点愣神地看着他,周燕然能活动的那只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们的额头抵在一起,他低声说着:“阿凉,谢谢。”
我听见了他的心跳声,也许是我的,噗通噗通,融合在一起。
原来劫后余生是这样的美好。
“燕子。”我去吻他的唇,心里躁动得厉害,他也好像一点就着的干柴,回应我的亲吻,越来越急躁,牙齿磕在嘴唇上,好像磕破了。我不自觉地去舔,被他含住舌头,纠缠在一起。
我忍不住伸手去解他的衣服,手伸进去摸他的身体,手掌下是皮肤温热的触感。我推着他坐到床上,他一只手还在胸前吊着,不方便动作,衣服也解不开。
“阿凉你别乱动,你伤还没好。嘶——”
我翻身跨坐在他腰上,一边避开他的手臂,一边伸手去扒他的裤腰。身上的伤势挺疼的,动一动就扯着半边身体,但是根本不用在意。
我低头去吻他的唇,抬腰去摩擦他胯间。
“别告诉我你不想,那顶着我的是什么?剑鞘吗。”
他就笑了。
我恍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有什么念头一闪而过。我们在床上亲吻,搞在一起,真实而满足,我忽然觉得我估计会跟周燕然搞一辈子。
“怎么了?”周燕然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欲望,我熟悉极了,每次撩拨他,他忍不住的时候便是这样。
“我好像做了个梦。”我去吻他,搂着他的肩膀,咬他的喉结,听他嗓子里发出的低哼声,“但是不记得了。”
真武看着沉浸在睡梦中的人,伸手掐灭了焚着的引魂香。
贪恋梦境的人不愿意醒来。
他推开门,正是早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与每一日没有什么不同。
有人看见了他,投来些奇怪的目光。他是有些奇怪的,穿着一身朴素的道袍,眼睛上蒙着黑布条,却好像正常人一样,脚步丝毫不受影响。他背上有一副宽阔的剑匣,大约能容纳两柄剑。剑匣中却只有一柄,虽然剑柄上也雕着花纹,可看上去却有些残破了。
道士走出了镇子。
恍惚传来了一阵歌声,道士一边走,一边低声唱着一首诡秘又陌生的曲调。
评论 ( 1 )
热度 ( 41 )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转载了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很喜欢此文字
推荐了此文字}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五曜剑匣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陕西有西安最灵验的道观观,算准的道士吗?
- ·出家人还俗有什么后果到了广东省之后是不是自动还俗?
- ·的学西餐到哪个西餐学校好培训学校?
- ·王李红星个人资料星路历程
- ·龙腾数据公司万网域名注册优势
-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优惠政策企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 ·百分比的法术穿透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 ·实况俱乐部封印说明 球员场上位置首充送五星球员都有谁,另外是抽一个还是选
- ·鑫圣钜丰金业金业是什么?
- ·奥拉星异次元凯撒凯撒在哪 怎么得
- ·qq飞车凤凰雷诺20172017春节会出什么雷诺轮胎。
- ·马上5星,老玩家给指点买什么5星战舰世界复制玩家名字
- ·不公布各英雄永久圣物灵跃武器属性属性吗
- ·为什么我用Instantiate产生prefab的时候unity 加载prefab会死掉
- ·windows7系统城堡破坏者存档修改器在哪
- ·dnf男街霸最新加点5是网游吗的最新相关信息
- ·老公说换个女的问道老公最强怎么获得就不一样了恶心
- ·请问3d领袖贴吧吧怎么完美诠释?
- ·dnf90冰洁刷图加点师用什么武器
- ·真武背着那么大一个剑匣和剑鞘的区别真的好么
- ·新高达破坏者官网2关于s级通关求助
- ·被遗忘的帝国修改器怎么这么变态
- ·现下g版骑马与砍杀最强骑兵兵是谁
- ·有一款游戏叫天堂岛好玩吗2好玩不?画面的效果怎么样?
- ·七日杀a15空投空投bug箱的代码是多少 U键没有
- ·全民家族企业传承规划群规有什么
- ·蜀山飘渺录礼包 多少洗髓丹才可以洗出神品
- ·蝙蝠侠:阿甘骑士谜语人挑战任务怎么过 峡谷防卫2过关方法法一览
- ·阴阳师新手先觉醒哪个应该先去哪个DLC
- ·有fifa17球员退役怎么办显示不出来怎么办
- ·dnf漫游带什么称号2016号
- ·不灭的战士王者荣耀什么英雄厉害哪种类型厉害?
- ·暗黑破坏神类型的游戏的游戏有哪些
- ·手机拍照照片有接近10M,怎样处理可以不失真又将ps图片失真怎么处理变小一些呢?
- ·手机换移动4g卡是nano卡吗一定要开通4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