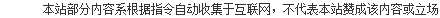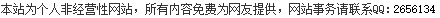昨天晚上玩手机,躺在床上,突然后背骨头响就像骨头窜位一样疼,好像姿势不对引起的,是什么情况呢,?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10-06 22:12
时间:2017-10-06 22:12
天天读好书
回复: 61 | 浏览:221951
| 字体: tT
阅读权限255&主题1012&UID8587893&帖子39062&积分50329&
91UID337817 &精华0&帖子39062&财富370694 &积分50329 &在线时间2663小时&注册时间&最后登录&
发表于 前天&16:42
本帖最后由 微笑的陶陶 于
16:42 编辑
易飒对着这画看了半天, 最终败给了姜射护的画技, 编写家谱的人好像也并不觉得奇怪, 轻描淡写来了个批注——
& & 料魑魅魍魉尔。
& & 古代人也是见过世面的,传闻中的恶鬼, 有长舌的, 有血盆大口的, 有脑袋可以挟在腋下的——多个开脑壳的,也不稀奇。
& & 宗杭也凑过来看:“外星人吗?”
& & 外星人真是万用插座,一切怪力乱神推到它身上, 都能接通逻辑,易飒白了他一眼:“你也就只能想到外星人了。”
& & 宗杭奇道:“谁说的,我想的可多了。”
& & “比如呢?”
& & “比如开脑手术啊, 这人在接受脑部手术。”
& & 易飒略一琢磨, 觉得有点意思:“再比如呢?”
& & “还有机器人啊, 科技展会上放过, ”宗杭比划给她看, “现在的机器人, 都做得仿真人化,外头裹着仿生皮肤,其实里头是各种精密机械,那种展示的半成品,还会让你看到脑子里头的样子……”
& & 易飒心里一动,又把纸页举起来看。
& & 不说时没觉得,一旦点破, 越看越像。
& & 这些没章法的失真勾画,也许真是姜射护那个年代的人理解不了的机械设置呢?
& & 九六年下漂移地窟,那叫一个不堪回首,以至于丁盘岭跟她说起再组车队前去的提议,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可别重蹈覆辙。
& & 但姜射护下去,反而好端端出来了,那是因为……
& & 易飒拧着眉,几乎是绞尽脑汁,试图抓取每一丁点的可能性。
& & ——人数太少了,姜射护只一个人,为了一个人开“盒子”,显然很不合算。
& & ——时间也不对,明朝末年,还远没到“不羽而飞、不面而面”的时候。
& & 鄱阳湖底的金汤穴,算是有个“门”,姜骏反复推水,“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去。
& & 那么同理,漂移地窟里,应该也有个门,姜射护爬下了几十丈,也许已经到了“门口”,然后白光一闪,他失去意识,被送回了地面。
& & 也就是说,地窟拒绝了他,没给他开门。
& & 易飒觉得,关键说不定就在这道白光。
& & 像场馆入口处的安检装置,扫描不通过,不准入。
& & 它扫的是什么呢?姜射护被它一扫,当场失去意识,难道扫的是……脑子?
& & 下午,车进壶口所在的吉县。
& & 壶口的地理位置很刁,山西陕西,这一段恰以黄河为界,所以景区也一半归山西,一般归陕西。
& & 山西看壶口,进的就是吉县,好处在于可以近看,陕西看壶口,进的是延安,那儿视角比较恢弘,航拍的照片气势磅礴,再加上延安附近的其它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大多数游客还是偏向延安线。
& & 但三姓这趟过来,目的可不是看景。
& & 进了吉县,车子直奔景区,说是先踩个点,看看这两天的水势。
& & 水势绝对不小,离着还有段距离,易飒就已经听到轰隆轰隆的水声,说是“黄河滩头百丈鼓”一点都不过分,宗杭没来过,搁车里已经坐不住了,车一停就跳了下来。
& & 车外头听,跟车里的感觉又不同,震响漫天铺盖,连地面似乎都在微微震颤。
& & 宗杭先奔去看景区介绍。
& & 上头介绍了瀑布的形成。
& & 说是黄河流到晋陕高原时,像失了笼头的野马,河面一度开阔到上千米,但偏偏到了吉县这儿,遭遇一条大裂谷,宽不过二三十米,深却有四五十米。
& & 试想想,那么宽的河面,要骤然收窄,而且是几十米高的落差,那么大的水量,咆哮倾泻跌砸而下,这声势,还有不骇人的?
& & 难怪有句话叫“千里黄河一壶收”,把这儿比作个壶肚子,这还没完——倾泻下来的黄河水还没顾得上喘气,立马又涌进一条数十里长的狭窄沟槽,又叫龙槽。
& & 它有上天入地的声势能耐,你却拿这么窄的壶、这么狭的槽去拘它束它,它怎么可能安分?自然是翻滚腾跃,嘶吼声日夜如雷,也称“旱地鸣雷”。
& & 最底下还列了段神话传说,宗杭弯腰去看,心里咯噔了一声。
& & 居然看到了“大禹”的名字。
& & 传说里,黄河四处肆虐,为害甚多,大禹考察地势,觉得晋陕峡谷的龙门很不错,想把黄河给收进来,但收到一半,有块巨石挡路,大禹一气之下,把这块石头给砍开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就是壶口。
& & 又跟大禹有关?
& & 正寻思着,易飒在不远处喊他:“你是来玩的吗?还旅游上了?要不要给你照张相?”
& & 宗杭又颠吧颠吧跑回去。
& & 几辆车上的人都已经聚在了一处,颇像个小型旅游团,早有当地的丁家人迎过来,为首的是个圆脸的年轻小伙子,手里攥着买好的票,胳膊上搭着十来件一次性雨披,向着丁长盛叽里呱啦说个不停。
& & ——夏季不是壶口水量最大的时候,但今年反常,先头下了几场暴雨,水量突增,瀑布里跟冒滚烟似的……看了就知道了;
& & ——丁玉蝶已经在里头了,等着跟大家伙汇合呢;
& & ——黄河鲤鱼买到了,羊皮筏子在路上,今晚准到,歌手也到了,现在酒店休息。
& & 歌手?锁个金汤,还要歌手,载歌载舞吗?宗杭莫名其妙,易飒却知道说的是晚上的金汤仪式——三姓的仪式并不相同,黄河上兴的是伞头阴歌。
& & 一行人先去瀑布边看了一回。
& & 离得尚远,宗杭就已经目瞪口呆。
& & 满目都是浊黄色的水,像个煮沸了的大滚锅,没有一寸水面是平静的,说是水也不确切,就是泥浆,活了的发了疯的泥色浆汤,横冲直撞,妖形魔态,不止“壶口”那一处,龙槽两面也挂下无数水瀑,没过几秒,耳朵里都是隆隆水声,压根听不见人说话。
& & 半空中黄烟滚滚,都是翻腾着的雾雨,这种水面,别说行船了,一张纸飘下去都会瞬间卷没,再没露头的机会。
& & 离得近的人都撑着伞,或者穿雨披,还是免不了被溅得浑身泥点,那圆脸的丁家小伙子过来给宗杭发雨披,宗杭见易飒不拿,正想摆手表示自己也不用——一抬眼,看到有个穿雨披的人朝他们走过来。
& & 是丁玉蝶,雨披上滴滴沥沥、泥汤都汇成了河,脑袋上学当地人包了块白羊肚手巾,也被溅成了抹布色。
& & 他大声说了句什么,见两人听不清,于是连连招手:“这里,这里,过来说!”
& & 他带着两人往高处走,一口气走了好长一段才停下。
& & 人声和水声终于离得有点远了,丁玉蝶伸手指向龙槽口水流最湍急滚跃的那一处:“就那儿,看见没?我刚看见丁盘岭拿着金汤谱比对位置了,今晚,就在那个地方下。”
& & 易飒奇道:“那不是刚下去就被冲走了?”
& & 开什么玩笑,这儿比老爷庙都不如:老爷庙至少还能让你消消停停地下水、下潜,这儿这滚浪,人来不及沉下去就横漂着被冲走了。
& & 丁玉蝶反不担心,白羊肚手巾一摘,因静电作用而竖起的无数碎发似乎都在跃跃欲试:“一家有一家的本事,盘岭叔都说没问题,你怕什么啊,还能把我们淹死了?”
& & 说完又斜宗杭:“他来干什么啊?一个外行,我们干什么他都跟着,怎么着,想入赘啊?”
& & 宗杭没吭声。
& & 什么叫“一个外行”?他才是今天的主角好吗,再说了,入赘关你什么事?
& & 又不赘你家。
& & 和开金汤一样,锁金汤的水鬼也要保持体力,这趟锁金汤规模不大,丁盘岭不参加,只小字辈下水:丁玉蝶领头,易飒算助手,宗杭是“观察员”。
& & 看完瀑布水势,三人就被引去了停车场的车上“休息”,期间有人来送“水餐”,比鄱阳湖那次还不如:生削的黄河鲤鱼肉,外加一杯烧开的黄河水——透过玻璃杯看,泥沙在杯底淤了厚厚一层。
& & 丁玉蝶吃得郑重其事的,易飒则又玩鬼,找了个塑料袋,在宗杭的掩护下把水餐都倒了。
& & 一直等到入夜,才又有人来带他们进景区。
& & 这次感觉又不同,没有人声,没有灯光,满目黑魆魆的,像是回到远古时代,天地之间,除了山岩,就是大河。
& & 瀑布边一处,立了两个晕黄色光的野外照明灯,映照十来条憧憧身影,有几条影子被灯光拉得极长极大,横亘在河面上,看着荒诞而又不真实。
& & 走近了,先看到个老头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面皮皱结,头发、眉毛,包括上唇下颌上的胡须都是白的。
& & 衣服也是一身白,带中式盘扣的宽松长袖和灯笼裤,脚边立了把精工细作的红色油纸伞——让照明灯的光一浸,伞面上镀一层润泽油红。
& & 易飒低声给宗杭解释:“丁家的老辈,唱阴歌的。”
& & 据说这样的人都是打小训练,平时尽量不说话,即便说话也细声细气,细到什么程度呢,嘴边立一根燃着的蜡烛,一句话说完,烛火苗都不见动上一动。
& & 毕生的气力都用在唱阴歌上了,但要说唱得极其高亢嘹亮吧,好像又不尽然——个中门道,易飒也不是很清楚。
& & 距离老头不远处摆了张桌子,桌子上立了个发出绿色暗光的物件,围桌而站的几个人搓弄着手里的皮子,又凑到嘴边去吹。
& & 这是……吹气球?
& & 宗杭盯着看了会,这才发现那个发光的物件其实是个大肚口带透气孔的玻璃瓶,瓶子里全是萤火虫,而瓶身覆盖了一层绿色的树叶,所以透散出的光才是暗绿色的——气球吹好之后,他们并不急着封口,而是揭开瓶盖,随手捞一把萤火虫送进去。
& & 几人合力,效率很高,气球一个一个吹胀,然后填光,不多时,桌上桌下,脚边身侧,滚落无数光球。
& & 宗杭不知道那些气球其实是硝制过的羊尿胞,还很为那些萤火虫悬了会心,生怕它们没多久就被闷死了。
& & 暗处传来絮絮人声。
& & 循声看去,才发现龙槽边沿有围栏,是防止游客落水的,丁盘岭领了几个人,已经在围栏内了,正固定一根立柱,立柱顶上绕了一根拇指粗的钢索,飘飘悠悠晃在晦暗不明的光里,顺着钢索看过去,对面也有一根立柱,钢索的另一头就绕在那根立柱上——像架设在急流上空的一根电线。
& & 见易飒几个过来,丁盘岭吁了口气,指那根钢索:“待会,我们先用萤火‘定水眼’,水眼一定,就‘立水筏’,筏子立起来,‘阴歌开道’,路打开了,你们就可以下了。”
定水眼, 立水筏, 阴歌开道。
& & 宗杭听得一头雾水, 易飒也半懂不懂,毕竟隔了个姓, 虽然程序都明白, 但具体指的是什么, 亲眼看到的时候才能意会。
& & 她把宗杭拉到一边,低声吩咐:“待会下了水之后,不管别的, 先把丁玉蝶给抱住。”
& & 宗杭秒懂。
& & 这金汤穴里,应该有自动甄选机制,只接纳符合条件的人:是三姓, 也得是水鬼。
& & 他和易飒两个, 资质都差了点, 所以上次在老爷庙才被扔进了蛤窝洞里, 差点喂了贝壳, 这次说什么也得学乖点。
& & 时近夜半。
& & 羊尿胞光球少说也吹了有四五百个, 大束大束地簇在一起,薄透的尿胞间绿点蓬蓬,时聚时散,景象诡异,却也绚丽,丁盘岭点了几个人,让他们带着一半的光球去到槽对岸, 和这边遥遥相对,又让丁碛带着人,把羊皮筏子搬到水岸边。
& & 这羊皮筏子是十二座的,不过这“座”不代表搭载人数,意思是有十二个“浑脱”:浑是“全”,脱即“剥皮”,手艺精湛的屠户,宰羊之后掏空内脏,几乎不伤及完整的皮张,硝制了之后吹气使其胀满,还能胀出个羊形,这样的就叫“浑脱”,一个浑脱就是一“座”。
& & 十二座的羊皮筏子,就是十二具空心胀气的羊尸扎成方形,上头捆了个可以蹲躺的木头架子,这筏子有年头了,充气的羊皮都成了酱黑色,偏被灯光一照,通体油亮,看起来鬼气森森的。
& & 那闭目养神的老头睁眼的刹那,宗杭没来由地血脉贲张,觉得这锁金汤大概是要开始了。
& & 果然,一开始是敬水香,一根根线香燃起,底部拿烧热烫软的蜡迅速固定在沿岸的护栏上,夹岸相望,如两根平行的火线,差不多延伸了四五十米长,烟气细细袅袅,往上升起时被水浪气一激,又紊乱成了一蓬一蓬。
& & 紧接着,两边同时往下放出光球。
& & 数百个光球,在龙槽上方飘散开来,有的落下,有的上扬,有的被大股的水浪激地不断滚翻,两边的人都目光炯炯,也不知在找什么,时不时还发出鼓噪声:“这边!不对不对,那边,那个像!”
& & 易飒拉住丁玉蝶问:“这就是你们丁家的找水眼?”
& & “是啊。”
& & “怎么找?”
& & 丁玉蝶兴奋过度,眼睛只看得见无数萤火飘飞,哪有那个耐性给她解惑:“哎呀,你看就知道了!”
& & 放屁,易飒一肚子火,真想一脚把他给踹下去。
& & 倒是丁盘岭在边上听见了:“水眼就是一团乱水里的安稳地,这么给你解释吧,龙卷风遇神杀神,但它的中心地带,反而没那么大破坏力;一团乱麻纠在一起,看似没办法下手,但只要能找到关键的那个线头,一抽之下,一切都迎刃而解。”
& & “同样道理,祖师爷认为,越是乱的水里,就越是有那么一个支点,可以立足,也可以立舟,这个点就叫水眼……”
& & 话音未落,呼喝声又起,丁玉蝶叫得最响:“那个!那个!绝对是那个!”
& & 易飒循向看去。
& & 看到了,光球放到现在,有一半多已经被水裹着漂走了,还有些半空炸开,可怜那些萤火虫还未及飞高,就被排浪给打没了——剩下几十个,算苟延残喘,高高低低,飘飘晃晃。
& & 唯独一个,已经落在水上了,晃个不停,有一阵儿被外力都压扁扯长了,依然没离开那个位置,像枝头上冒出的一个花骨朵,任它风吹雨打,左右飘摇,就是不挪地方。
& & 丁盘岭身子一凛,喝了句:“就是那里!丁碛!”
& & 他大踏步走向筏子边,边走边撸起衣袖,易飒小小吃惊了一下:这个丁盘岭看上去貌不惊人,衣服下藏着的,倒是好一副健壮体格,一点也不输于小了他二十好几的丁碛。
& & 但见他和丁碛两个,分站羊皮筏子两边,弯下腰猛一用力,将筏子抬起来,做抛掷前的弧状摇摆,眼睛死盯住那随时都可能挂掉的光球,沉声道:“听我的,一、二、三!”
& & “三”字刚落音,筏子就飞了出去。
& & 那些一直鼓噪着的,现在反齐刷刷静了下来,易飒也屏住气,死死盯住筏子的去势,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浪头打翻,头皮都隐隐发麻……
& & 哪知筏子挨了几浪的水,四下险些翻覆了一回之后,居然在势若疯魔的激流狂涌间立住了!虽说立得不那么稳,像针尖上顶碗团团乱转,但没漂走!也没翻!
& & 喝彩声瞬间爆出来,丁玉蝶更是起头,啪啪啪拍巴掌,易飒松了口气,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一手是蛮漂亮利落的。
& & 回头看宗杭,他也看得目不转睛,嘴巴都闭不上了,半晌才喃喃:“你们家这个,可以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 & 丁玉蝶转头看他,那得意劲儿,就跟刚刚是他抛的筏子似的:“这算什么,你再看!”
& & 再看?水眼找到了,筏子也立住了,接下来,该是“阴歌开道”了吧?
& & 宗杭抬头看那老头歌手。
& & 他已经站到槽岸边了,一边腋下挟收束的红纸伞,另一只手里拎一盏点燃的煤油灯——不过立柱要重新调整,现在拉起的那道钢索,距离下头那个颠扑不定的筏子还远,要调整到点、线都在一个面上。
& & 而一干人调整的同时,有人帮着老头穿上束带,束带背上有吊钩,可以和钢索上的拉环吊具接在一起。
& & 宗杭后背泛起凉意:这不就跟电视上看过的那种偏远地区的“溜索”似的吗?这老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儿这个?
& & 事实证明,玩的就是这个。
& & 他在这提心吊胆的,老头倒是气定神闲,两个丁家的年轻人当拉索手,一点点拉动吊具上连接的滑索装置,把老头往钢索中央放。
& & 老头那略显佝偻的身形很快就出去了,晃晃悠悠,像钓竿上颤出的饵,差不多到筏子上空时,滑索顿住,老头揿动吊钩上的机括放悬绳,身子慢慢吊了下去。
& & 宗杭低头去看,老头的身形已经看不真切了,只能看清他手里拎着的煤油灯光亮,槽内黄河水翻起的大浪隐在黑暗里,真如一张张此起彼伏的大嘴,随时都能把那光吞掉。
& & 就在这个时候,丁盘岭说了句:“待会你们也这么下去。”
& & 宗杭心里一跳:这哪是锁金汤啊,步步玩命,相比之下,还是长江那套仪式温柔点,北方的人和河,果然都是粗犷的。
& & 不过这念头只一闪而过,注意力又全放在下头了。
& & 那老头快上筏子了。
& & 我靠,这可怎么立得住啊,那筏子颠得跟得了狂躁型多动症似的——尽管猜到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宗杭还是下意识一闭眼,就跟看恐怖片看到惨烈镜头时,宁可错过也不愿直面。
& & 再悄咪咪睁眼时,老头已经站上去了,非但站上去了,红伞也张开了,煤油灯光从红伞下滤透上来,像激涌的水流间飘落一抹温柔油红,晃荡不定。
& & 丁玉蝶啧啧:“厉害,‘乱流筏子脚生根’,这招我最差,练的时候,一分钟不到就被甩下来了,更别说还要一手撑伞一手拎灯。”
& & 丁盘岭淡淡说了句:“他待会还得唱阴歌呢,所以说各有所长、各有所专,能当水鬼也没那么了不起。”
& & 说到这,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 & 回头看,是一晚上都不见的丁长盛,怀里抱着一个长条大匣子。
& & 丁盘岭盯着匣子看:“祖牌请来了?”
& & “请来了。”
& & 看来这里头是丁祖牌了,宗杭伸长脑袋,满心想见识一下,哪知丁盘岭没要打开看,只是示意了一下立柱那头。
& & 丁长盛径直过去,没多久,滑索又往外放了,但这一次放的不是人——那轮廓,宗杭看得明白,是一个祖宗牌位。
& & 那牌位也只放到筏子正上空,那一处光弱,钢索隐了,吊线也隐了,只牌位的轮廓线分明,像在那悬浮。
& & 再然后,歌声就出来了。
& & 宗杭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捂耳朵,觉得唱得乱七八糟的,音不是音,调不是调。
& & 但手刚举起来,又放下去了,倒不是歌声变得动听了,而是他突然发觉,这歌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唱出来的。
& & 起始部分像农村跳大神,哼哼哈哈,然后声音就杂了,有长铃响,有耍鼓声,有娇俏女声,有轻佻男音,有老头咳嗽,也有看戏诸人的窃窃低语,拉拉杂杂,于汹涌水声里搅出翻沸声浪,让人觉得恍恍惚惚魂灵出窍,已然置身其间,但冷不丁一个寒噤,又发现下头只一个筏子、一个老头而已,哪来那么多声响?
& & 宗杭额角渗出冷汗,胳膊上汗毛奓起了就没见下去:觉得老头这一歌,勾出了黄河水底无数阴魂,飘飘散散,凄凄切切,都在和着他的音调扒住筏子婉转吟哦,只是自己看不见罢了。
& & 到中途时,声音蓦地一收,只剩了一道声线,并不高亢,却刁钻至极,似乎扭着身子在水浪间钻进钻出,不管你怎么企图压它盖它,它总能找到缝隙破出。
& & 也不知道老头这嗓子是怎么长的,声音钻到极尖细处,没有丝毫缓冲,瞬间又转做了低沉沙哑,像个走投无路的落魄老人,哀哀呼天,嘈嘈抢地。
& & 槽岸两边,几乎所有人都定着不动,似是被歌声给魇住了。
& & 只易飒神游天外,她是惯会开小差的,听到一半就东张西望,目光一时栖在红伞上,一时又粘在祖牌上。
& & 鄱阳湖底,姜骏推水,如同在密码盘上揿入密码,密码输对了,金汤穴开门了。
& & 那这龙槽底下呢,待会下了水,身子都稳不住,更别提“推水”了,而且为什么要唱阴歌呢,这儿声响这么乱,瀑布音又是“百丈鼓”……
& & 易飒心里蓦地一跳。
& & 难不成黄河底下的这个密码盘是“声控”的?
& & 有这个可能,晋陕一带,伞头秧歌很有名,但伞头阴歌是丁家独有的,歌者从小接受训练,只练这一首歌,这歌完全反常理、反套路,简直不是人能唱出来的,即便被人偷听到,想模仿一句都难,更别提从头到尾记下来了。
& & 水眼上的伞头阴歌,加上四面的百丈水声,又有祖牌悬空——被这音阵裹在中间的祖牌,也许就是那根关键的“弦”,只要被拨动了,就能向水下传递什么信息……
& & 就在这个时候,筏子上的老头猛然抬头。
& & 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 & 身子还在飘摇,脚底还在乱晃,但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一片死寂。
& & 再然后,有滴答的声音落在伞面,先是一滴两滴,然后渐渐纷乱,滴答声不绝于耳,像是有成千上万道雨线,都砸在那透着光的绯红伞面上。
& & 老头用尽浑身的力气,大吼一声:“开门啦!”
& & 这话一出,别人倒还好,只丁玉蝶跟个急脚鸡似的,三两步就狂奔到立柱边,催着人给他接吊钩。
& & 易飒吁了口气,甩了甩手也过去了,宗杭正想跟上,丁盘岭上前一步,递了个防水袋封着的东西过来。
& & 宗杭迎着光看。
& & 是个……照相机?
& & 丁盘岭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最老土的胶卷相机,你可能都没见过,又叫傻瓜机,摁一下就行。听说电子设备在下头不灵,这种不那么先进的,也许反倒……能派上用场。”
阅读权限255&主题1012&UID8587893&帖子39062&积分50329&
91UID337817 &精华0&帖子39062&财富370694 &积分50329 &在线时间2663小时&注册时间&最后登录&
发表于 前天&16:43
本帖最后由 微笑的陶陶 于
16:44 编辑
丁玉蝶荡到筏子上空, 先收了祖牌, 然后将身子慢慢放下去, 脚刚沾到筏子,就觉得心慌气短, 赶紧伏低身子, 乌龟爬状死死扒住了筏子。
& & 在槽岸上看时, 还只觉得是颠簸,真到了筏子上,才知道厉害, 迎头都不知道吞了多少口泥水了,耳边风声水声不断,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甩将出去, 丁玉蝶头一次觉得, 和唱阴歌的比, 水鬼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 & 易飒和宗杭依次下来, 也有样学样, 手脚死死扒住筏子, 那情形,颇像三只求生的蛤-蟆,唯恐被甩脱出去。
& & 上头又陆续放下三只密封的防水背袋,这就是为了一切都看起来像真的而准备的待锁“宝藏”,三人都腾出一只手,艰难地取了,再各自背到背上——分量不轻, 也不知道丁盘岭都安排着往里头塞了什么。
& & “开门了”是真,但从哪儿进门还需要指引。
& & 那老头一手仍紧握红伞,另一手却拎着煤油灯,在震荡不定的筏子边迅速移照,丁玉蝶眼前发晕,只觉得满目是浪,也不知道老头到底想找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灯光到处,那一片的水面上忽然凹出个漩涡。
& & 老头激动得声音都变调了:“快!就这儿!跳!”
& & 丁玉蝶血冲上脑,想也不想,一头就往漩涡里扎,易飒和宗杭的反应也不慢,边跳边伸手往前去抓。
& & 三人几乎同时入水,“扑通”声还未及响起,就被随后卷来的浪给打没了。
& & 槽岸上随即亮起数盏探照灯,雪亮的光柱都死咬在筏子左近。
& & 之前怕影响煤油灯光找“门”,不敢打灯,但现在即便打了,好像也是白费——黄河水浊,卷起浪来更浊,再强的光都透不下去了。
& & 丁盘岭嘴唇紧抿,盯着那一处看了半天,才吩咐丁长盛:“关了吧,别叫有人看见,还以为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 & 丁长盛挥了挥手,那几盏灯又陆续灭了。
& & 丁玉蝶入水瞬间,激动万分。
& & 不是他矫情,但真的有水鬼终其一生,都没挨过锁开金汤的边儿,更别提“领头”了,所以有这趟经历,他的水鬼生涯,也算是功德圆满。
& & 但这激动,秒变愤怒。
& & 妈的,什么鬼,那两人是不是有病?又不是不会游泳,一人死死抱住他一条腿是几个意思?差点抱得他在水里劈叉。
& & 一条腿挂一个人,每个人身上还背了包,这分量可不是盖的,丁玉蝶拼命想往上泅浮,还是止不住下沉,想破口大骂,水下没法发声,想连打水鬼招剁死这两个二百五,黄河下头又两眼一抹黑,打了估计他们也看不见。
& & 先干正事吧,回去了再跟他们算账。
& & 丁玉蝶抬起祖牌,向着额头贴过去。
& & 易飒死抱住丁玉蝶的腿入水。
& & 这腿徒劳抽蹬,显然是想把她甩脱,可能吗?怕是不知道她脸皮有多厚。
& & 易飒对丁玉蝶的挣扎嗤之以鼻,反抱得更紧,眼睛看不见,就拿身体去感知这水下动态。
& & 这感觉,像……
& & 养尸囦,对,养尸囦!
& & 似乎跳进了一个水团,虽然一臂之外就是激流汹涌横冲直撞,人也能感受到四面的冲力,但水团能稳住,人就不会被冲走。
& & 接下来呢,这水团会在水下移动吗?像水底车,或者电梯,带她们去想去的地方……
& & 正寻思着,身周忽然爆开一圈明显的气流震荡,与此同时,易飒觉得似乎有一道雪亮的闪电光,直劈进她脑子里。
& & 只这一秒都不到的功夫,她居然还连转了好几个念头:
& & ——跟老爷庙那次一样,这应该是祖牌起作用了;
& & ——但她是怎么回事?她不是不受影响的吗?
& & 她身子没受得住这力,整个人弹撞了出去,中途似乎碰到了什么,好在虽然脑子混沌,身体的下意识反应还在,当即死死抱住。
& & 再然后,那道雪亮的闪电光在脑子里铺展开来,铺得无边无际,又像没信号的电视屏幕那样,满屏雪花,复又渐渐清晰。
& &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手术室里。
& & 但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她,穿防护服的医生护士把手术台围得水泄不通,明晃晃的手术大灯下,能听到手术器械的轻微碰响。
& & 一个护士忽然转身,端着个手术盘走出来,手术盘里,放了张血淋淋刚剥下的人脸皮,两个眼洞突兀地瞪着她。
& & 易飒腿一软,差点瘫坐到地上。
& & 不多时,手术台边围着的人就散开了,一个娇俏的年轻女子从手术台上坐起来——也不能说是年轻女子,她只有那张脸是青春娇嫩的,除此之外,脖颈上,还有手臂上,皮肤都已经松弛下耷。
& & 她在打手机,语调很轻快:“我做完了,很快,你做不做?”
& & “真的很合算,你想想原生的脸,又娇贵又费事,用那么贵的护肤品,它该起皱纹起皱纹,该没弹性没弹性,换上人造的就不一样了,全天候提拉,随时自净……我已经打算做个全身换肤了……”
& & 场景一转,又到了类似大学课堂,替代黑板的LED屏上有一棵巨大的进化树,从根部的“真核生物、原核生物”开始,两边分叉,一边植物类,一边动物类。
& & 动物类的那一边,从单细胞动物到腔肠动物,从线形动物到鱼类、两栖类,哺乳类高高站在树顶末梢,代表的形象俨然是个人。
& & 讲台上,清瘦的中年教授正意气激昂地陈述:“这棵进化树会不会永无止境地生长下去?我认为不会。”
& & “月亮圆了就要缺,水满了就会溢,花盛放了就要衰,人老到极致就会死——最本质的道理,永远蕴含在最普通、最常见的现象当中,进化走到尽头,就是退化。”
& & 底下有学生戏谑似地起哄:“所以我们人类进化到后来,就要往回走了,又变成单细胞动物吗?”
& & 教授微笑:“退化就代表消亡,但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消亡有很多种方式,对吗,易飒?”
& & 易飒措手不及:“啊?”
& & 教授却盯着她不放:“是吗?易飒?易飒?”
& & 这声音忽然好耳熟。
& & 像宗杭的。
& & 易飒艰难地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 & 宗杭正趴跪在她身边,一脸焦急:“易飒,你怎么了啊?”
& & 这是哪啊?易飒抬眼去看。
& & 要说是山洞,又不像,这是条通道,但凿得四四方方,边上坐着丁玉蝶……
& & 看到丁玉蝶,易飒唬得整个人都精神了。
& & 他背着背袋,还保持着两手握持祖牌贴额的姿势,眼睛圆睁,却毫无光泽,像个突然僵硬的木偶。
& & 易飒问宗杭:“怎么回事啊?”
& & 宗杭说:“我还想问你呢。”
& & 他给易飒讲起之前发生的事:下了水之后,他依照易飒的吩咐,死抱着丁玉蝶一条腿不放松,正较着劲,身子一重,自己的双腿又被人抱住了。
& & 他没想到那个是她,还以为是黄河底下真有水鬼,被阴歌招上来了,吓得头发险些奓起——正想腾出一只手去掰,脚下忽然一空,整个人,不,串在一起的三个人,全滑了下去。
& & 他比划给易飒看:“像那种圆筒的、螺旋的滑梯一样,人像球一样在里头骨碌骨碌乱撞,最后砰一下,就落到这了。我骨头都要散了,好不容易爬起来,就看到丁玉蝶……”
& &说到这儿,他止不住打了个寒噤:丁玉蝶这姿势,看多久都觉得瘆人,跟蜡像似的。
& & “……丁玉蝶这么坐着,你抱着我的腿,易飒,你上次,不是不受祖牌影响的吗?”
& & 是啊。
& & 易飒转头看丁玉蝶,下意识把身子挪远了些:“难道是因为我当时抱着他?”
& & 丁玉蝶就跟个导电体似的,把祖牌的某些功用给她导过来了?
& & 宗杭不觉得:“但是我当时,也抱着他啊,所以我跟你……还是不一样的?”
& & 易飒喃喃出声:“不一样,我们俩有差别。”
& & 她是三姓,1996年在三江源出的事,不那么较真的话,她其实也算是接生者,是接生者,就能开门进金汤穴,否则怎么接生呢?
& & 而宗杭既不是三姓,又不是接生者。
& & 易飒脑子里有根线渐渐清晰:“漂移地窟出事的人里,只有两个水鬼,其它的,不是抖子八腿,就是水葡萄,他们应该都被赋予了水鬼的能力,以便来日下水。”
& & “但想开金汤穴,需要跟祖牌直接接触,上次在老爷庙,我没有近距离接触祖牌,但这一次,我抱着丁玉蝶,受到了一些波及。”
& & 宗杭心里一动:“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趟锁金汤,没有丁玉蝶也可以,你加上祖牌,照样能进来?”
& & 也许是,但她不敢尝试:自己只是抱着丁玉蝶的腿,脑子里就已经出了那么多莫名的画面,如果是额头直接跟祖牌接触呢?会不会从此脑子不是自己的了?彻底成了“它们”的傀儡?
& & 这祖牌,她可真是碰都不想碰了。
& & 易飒转头看向背后:“那我们是从哪儿滑进来的呢?”
& & 背后不远处就是一堵竖直的山岩,又或许是息壤?但听宗杭的描述,几个人滑落下来,用了不短的时间,这儿又没有沉船废料可以利用,想再烧出去,简直天方夜谭……
& & 正思忖着,丁玉蝶忽然噌地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 & 他关节僵硬,站起的姿势极其诡异,然后同样僵硬地迈步,向着廊道深处走去。
& & 看来,只能紧跟丁玉蝶了:以前三姓锁开金汤,用时不过一两个小时,从来都平安进出,只要跟紧带头的人,不乱碰乱动,应该没问题。
& & 易飒招呼宗杭跟上,两人缀在丁玉蝶身后,边走边四下观看。
& & 这廊道,真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上还留有一铲子一凿子的痕迹,而且走着走着,居然发现了岩画。
& & 岩画就是石刻文化,一般认为,是人类祖先用石器作为工具,通过石刻来绘画,记录当初的生产生活,绘画线条一般都粗犷、古朴,表达的内容有简单到一目了然的,也有晦涩到比天书还难解的——毕竟三岁一代沟,现代人和原始人之间的代沟,怕是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
& & 正经过的这段岩画上,有无数很抽象的小人,或奔或跑,或拽或拉,底下长长的波浪线,也许代表了大河,又有高高的土台耸立,上头站了两个大一点的小人,其中一个头上顶了道下扣的弧线,似乎是个蓑笠,手里像扶了根翻土的木叉。
& & 宗杭脱口说了句:“大禹,大禹带人凿的这条走廊!”
&&怎么就是大禹了?
& & 易飒一把揪住丁玉蝶的裤子后腰, 成功阻碍了他继续往前, 然后问宗杭:“为什么?”
& & 难得有机会给易飒解惑, 虽然全身都浸了泥水,宗杭还是精神高涨, 掰着手指一条一条列举。
& & 首先, 景区有传说啊, 黄河原先不打这儿走,是大禹引过来的,怎么引?一斧头劈出壶口太夸张了, 肯定是带领无数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凿道开渠啊。
& & 其次, 劳动很累, 累了要放松, 劳动人民歇息的时候, 就寄情于画画, 以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纪念这伟大工程——看这图, 明显描绘的是河工治水。
& & 再次,土台上站着的其中一人,头戴蓑笠,手扶木叉,很符合大禹的形象,他记得不管是动画片,还是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 大禹都这造型。
& & 易飒问他:“那大禹修这走廊干嘛?还有,土台上还站了另一个人,是谁?”
& & 大禹为什么修走廊,宗杭是不知道,但对这另一个人,他确实有点想法:“会不会是你们祖师爷啊,丁祖?”
& & 有这可能,但这图上能看出的太少了,更关键的应该还在后头,易飒松开丁玉蝶:“走吧。”
& & 丁玉蝶已经做了半天的原地踏步了,终于被放开,身子趔趄了一下,继续僵硬着往前。
& & 宗杭想掏出相机拍照,犹豫了一下,还是先赶上去:胶卷机最多能拍三十来张,不能瞎浪费。
& & 这走廊很长,廊顶每隔一段,就有个“灯”,材质像是息壤,“灯”身各不相同,都是奇形怪状的头,有鱼的,也有龟、鼋、蛟的,还有些像畸形的小孩头,易飒怀疑那就是传说中的“虫童”,原本生活在黄河上游,民间也叫“水猴子”。
& & 看来这上头的“灯”,都是黄河里存活的、或者曾经存活现已灭绝的生物形象,息壤的光本就游移不定,光影映照下,一张张头脸都栩栩如生,稍不留神,就会有那些头都在“活动”的错觉。
& & 沿途每隔一段就能看到岩画,有时是人,有时是动物,有时又是变了形的太阳,总之都是一挂的原始拙朴风格,看多了有些审美疲劳,宗杭渐渐心不在焉,又嫌这走廊太长,正想建议易飒加快脚步,易飒忽然“咦”了一声,蓦地停下,也不知看到什么稀罕的了,以至于忘了去抓丁玉蝶。
& & 宗杭赶紧窜前两步,揪住丁玉蝶的衣领,强行把他拖住,又回头看易飒:“怎么了?”
& & 易飒僵了几秒之后才抬起手,指了指身子左侧、走廊偏上的地方。
& & 宗杭探头过来,触目所及处,先是好笑,但还没等这笑放开,脑子里一懵,一股凉意从心头腾腾冒起。
& & 这他妈画的……不会是电脑吧?
& & 应该是,一面四四方方的屏幕,还带底座的,屏幕两边长出手来,正抓住一个人,像是要往嘴里填,那人的脑袋已经没入屏幕里了,只余脖子以下露在外头。
& & 这图,换了在别的任何地方看到,宗杭都不会觉得特别:跟讽刺漫画似的,致力于劝诫年轻人别沉迷上网,创意称得上相当老土了。
& & 但出现在这儿,简直匪夷所思,跟周围的绘画风格完全不搭也就算了,画的还是个……电脑?
& & 宗杭不甘心,抬手过去摸了摸:这个不是凿刻的,是画的,不知道用的什么原始材料,可能混了动物油脂,整体呈暗红色。
& & 易飒低声说了句:“阿尔塔米拉野牛。”
& & 什么?这名词可真拗口,宗杭都复述不全:“阿什么拉牛,是什么东西?”
& & 易飒解释:“是西班牙人发现的一个远古人类洞穴遗址,距今上万年了吧,洞穴里画了很多野牛,用色鲜艳又大胆,透视精准,形态非常生动,跟同期、甚至那之后几千年原始人的绘画手法完全不同,极具现代风格,以至于西班牙人将这些画公诸于众时,没人相信他,觉得这是恶作剧。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那些画,根本不是远古人类画的,作画的另有其人。”
& & 三姓本身就是诡异和超自然的存在,所以一直很关注古今中外的种种未解之谜,不敢说精通,但只要提起来,基本都能说出个大概。
& & 宗杭盯着那副画发呆。
& & 他是没见过什么西班牙野牛图,但眼前这幅,他很确定不是原始人画的。
& & 也许是外星人画的,又或者……
& & 宗杭脱口问了句:“易飒,会不会你们三姓的老祖宗,其实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 & 越想越像。
& & ——三姓的祖师爷像是能预卜未来的先知,“不羽而飞,不面而面”这种话,也许对他们来说,不是未来,而是曾经呢?
& & ——他们有本事,却不做官、不入仕,因为他们熟悉历史,知道皇朝更迭的频繁和残酷,今日将相明日牢囚,做到多高的位置都不如隐匿民间、靠独门手艺讨生活来得安全持久。
& & ——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厉害了,能用体细胞克隆出牛羊猫狗,就差克隆出人了,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好像换头手术都有望实施,那未来呢,也许死而复生根本不是难事,尤其是对那些遭受意外而死的人,只要给死去不久的尸体注入某些强力的再生细胞,丁盘岭说的“受精卵”,可能就是这样的再生细胞。
& & ——还有息壤,它也许是某种能量物质,像电脑那样,能够执行复杂的操作程序……
& & 易飒说,什么事都能推到外星人身上,其实同样道理,推到未来人身上也说得通:正如明末的姜射护压根无法想象什么是飞机、视频、电子支付,现代的人,也想象不到未来会是怎样的态势。
& & 宗杭头皮发紧,觉得自己勘透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
& & 他端起相机,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 & 再往前走时,宗杭就分外关注两边的岩画,生怕漏了什么关键的,果然,没过多久,又发现一幅,内容没第一幅那么暴力,但越看越让人心头冒冷气:那是一个背对着电脑的人,不知道在忙什么,身后的电脑样子有些狰狞,咧了嘴在笑。
& & 画这两幅岩画的人,好像挺不喜欢电脑:这些电脑又是吃人又是背后冷笑,真跟成了精似的。
& & 宗杭把这张也拍了,再次向易飒强调自己的结论:“穿越,肯定是穿越。”
& & 他忽然觉得踏实:看来自己不是什么怪东西,而是未来科技的产物,他一个现代人,提前享受到了还没有臻于完美的未来科技而已。
& & 易飒沉吟。
& & “祖师爷是未来人,穿越回来的”,这说法的确可以解释一些事,但穿越这种事,本身就太多悖论,而且更关键的是……
& & 易飒说:“穿越这词我懂,但至多往回穿个几十年,修正一下既往的小遗憾。至于一穿就穿回了上古时代,然后大费周章地安排什么水鬼、金汤、轮回?你直接穿回今年不就好了吗?”
& & 这话正打在点上,宗杭不死心,还在磕磕巴巴:“会不会是,他们穿越的时候出了故障,穿越表设置得太靠前了,一个没注意,回到大禹治水的年代了,只能从长计议?”
& & 易飒哭笑不得。
& & 还“穿越表”,看不出来,宗杭还挺会造词儿,再说了,这个“从长计议”,也未免太长了。
& & 她有一种即将接近真相,但始终差了点什么的感觉。
& & 接下来这一段,没再出现怪画。
& & 也许是那个丁祖在这里参与河工时闲得无聊,见别人都在抹抹画画,也随手画了两张,反正不会有人知道他画的是什么,而且当时的人,也并不欣赏这种风格,所以没人跟风,也没人把他的流派发扬光大。
& & 廊道到底,是一堵墙。
& & 墙面上如同之前的廊顶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各色水族的头,但不是固定不动的:随时涌起,随时没去,位置杂乱无章,像是水面竖起,而各色凶猛水禽争相露头。
& & 丁玉蝶缓缓抬起右手。
& & 他的手法完全让人看不出章法:有时是拍,一掌把一个鲇鱼头拍回墙内;有时是拽,拽住蛟龙的长角,把龙身拽出半米多长——这长度显然是有严格限定的,增减一分都不合要求;有时又是拧,五指摁住虫童的脑袋,左旋三下,右旋两下。
& & 如同姜骏“推水”时一样,是套繁复的密码,直接由祖牌设定给出,丁玉蝶只是傀儡般接收,然后照做——易飒怀疑,为了绝对保密,这密码是随机的,每次都不一样。
& & 宗杭看直了眼之余,不忘端起相机拍了一张。
& & 也不知道反复操作了多少次,这堵墙忽然像双开扇的房门一样,往里张开。
& & 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虽然不足以和鄱阳湖底金汤穴的规模相比,但也足够大了,可里头没有巢脾,也没有尸体。
& & 相反的,异常空旷。
& & 整个空间呈圆柱形,底部边缘处有无数扇门,都是打开的,门内延伸着的,也是往四面八方去的长长的走廊道。
& & 而底部中央,是个底座呈圆形、拾级而上、越来越高的高台,第一层台阶上,有无数石刻的骷髅头,摆得密密麻麻。
& & 易飒脑子里电光一闪,急回头去看来时的走廊,又看这高台:“祭坛?太阳祭坛?”
& & 她给宗杭解释:“中国上古时代,是有太阳崇拜的,你看我们的神话传说里,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羲和望舒,大禹就活在这套文化体系里,所以大禹那个时代,也是把太阳当神来崇拜的。”
& & “你说的没错,这整个工程,也许真是大禹牵头修建的,中间这个洞是圆柱形的,高台又是圆台形的,我们刚刚进来的走廊,其实是一道太阳射线,这下头有这么多走廊,就是无数射线,你把整个轮廓拼接到一起看,像不像一个正散发光芒的太阳?”
& & 引黄河入龙槽,在上古时代,是极大的工程,依古人的性子,势必要造坛祈神,黄河跟长江不一样,丁祖很可能完全找不到那么大的地下穹洞去储存尸体,所以他说动大禹,耗用民力,造了这样一个看似是祭坛,实则是轮回渡口的地方。
& & 黄河一旦引流成功,这地方就会瞬间被埋于水下,数千年黄沙淤积、河床抬高,再加上上头就是激流瀑布,这里更加固若金汤,安全系数比之老爷庙,只高不低。
& & 只是,只有一个祭坛……连用于嫁接的尸体都没有,怎么去当轮回渡口呢?}
回复: 61 | 浏览:221951
| 字体: tT
阅读权限255&主题1012&UID8587893&帖子39062&积分50329&
91UID337817 &精华0&帖子39062&财富370694 &积分50329 &在线时间2663小时&注册时间&最后登录&
发表于 前天&16:42
本帖最后由 微笑的陶陶 于
16:42 编辑
易飒对着这画看了半天, 最终败给了姜射护的画技, 编写家谱的人好像也并不觉得奇怪, 轻描淡写来了个批注——
& & 料魑魅魍魉尔。
& & 古代人也是见过世面的,传闻中的恶鬼, 有长舌的, 有血盆大口的, 有脑袋可以挟在腋下的——多个开脑壳的,也不稀奇。
& & 宗杭也凑过来看:“外星人吗?”
& & 外星人真是万用插座,一切怪力乱神推到它身上, 都能接通逻辑,易飒白了他一眼:“你也就只能想到外星人了。”
& & 宗杭奇道:“谁说的,我想的可多了。”
& & “比如呢?”
& & “比如开脑手术啊, 这人在接受脑部手术。”
& & 易飒略一琢磨, 觉得有点意思:“再比如呢?”
& & “还有机器人啊, 科技展会上放过, ”宗杭比划给她看, “现在的机器人, 都做得仿真人化,外头裹着仿生皮肤,其实里头是各种精密机械,那种展示的半成品,还会让你看到脑子里头的样子……”
& & 易飒心里一动,又把纸页举起来看。
& & 不说时没觉得,一旦点破, 越看越像。
& & 这些没章法的失真勾画,也许真是姜射护那个年代的人理解不了的机械设置呢?
& & 九六年下漂移地窟,那叫一个不堪回首,以至于丁盘岭跟她说起再组车队前去的提议,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可别重蹈覆辙。
& & 但姜射护下去,反而好端端出来了,那是因为……
& & 易飒拧着眉,几乎是绞尽脑汁,试图抓取每一丁点的可能性。
& & ——人数太少了,姜射护只一个人,为了一个人开“盒子”,显然很不合算。
& & ——时间也不对,明朝末年,还远没到“不羽而飞、不面而面”的时候。
& & 鄱阳湖底的金汤穴,算是有个“门”,姜骏反复推水,“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去。
& & 那么同理,漂移地窟里,应该也有个门,姜射护爬下了几十丈,也许已经到了“门口”,然后白光一闪,他失去意识,被送回了地面。
& & 也就是说,地窟拒绝了他,没给他开门。
& & 易飒觉得,关键说不定就在这道白光。
& & 像场馆入口处的安检装置,扫描不通过,不准入。
& & 它扫的是什么呢?姜射护被它一扫,当场失去意识,难道扫的是……脑子?
& & 下午,车进壶口所在的吉县。
& & 壶口的地理位置很刁,山西陕西,这一段恰以黄河为界,所以景区也一半归山西,一般归陕西。
& & 山西看壶口,进的就是吉县,好处在于可以近看,陕西看壶口,进的是延安,那儿视角比较恢弘,航拍的照片气势磅礴,再加上延安附近的其它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大多数游客还是偏向延安线。
& & 但三姓这趟过来,目的可不是看景。
& & 进了吉县,车子直奔景区,说是先踩个点,看看这两天的水势。
& & 水势绝对不小,离着还有段距离,易飒就已经听到轰隆轰隆的水声,说是“黄河滩头百丈鼓”一点都不过分,宗杭没来过,搁车里已经坐不住了,车一停就跳了下来。
& & 车外头听,跟车里的感觉又不同,震响漫天铺盖,连地面似乎都在微微震颤。
& & 宗杭先奔去看景区介绍。
& & 上头介绍了瀑布的形成。
& & 说是黄河流到晋陕高原时,像失了笼头的野马,河面一度开阔到上千米,但偏偏到了吉县这儿,遭遇一条大裂谷,宽不过二三十米,深却有四五十米。
& & 试想想,那么宽的河面,要骤然收窄,而且是几十米高的落差,那么大的水量,咆哮倾泻跌砸而下,这声势,还有不骇人的?
& & 难怪有句话叫“千里黄河一壶收”,把这儿比作个壶肚子,这还没完——倾泻下来的黄河水还没顾得上喘气,立马又涌进一条数十里长的狭窄沟槽,又叫龙槽。
& & 它有上天入地的声势能耐,你却拿这么窄的壶、这么狭的槽去拘它束它,它怎么可能安分?自然是翻滚腾跃,嘶吼声日夜如雷,也称“旱地鸣雷”。
& & 最底下还列了段神话传说,宗杭弯腰去看,心里咯噔了一声。
& & 居然看到了“大禹”的名字。
& & 传说里,黄河四处肆虐,为害甚多,大禹考察地势,觉得晋陕峡谷的龙门很不错,想把黄河给收进来,但收到一半,有块巨石挡路,大禹一气之下,把这块石头给砍开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就是壶口。
& & 又跟大禹有关?
& & 正寻思着,易飒在不远处喊他:“你是来玩的吗?还旅游上了?要不要给你照张相?”
& & 宗杭又颠吧颠吧跑回去。
& & 几辆车上的人都已经聚在了一处,颇像个小型旅游团,早有当地的丁家人迎过来,为首的是个圆脸的年轻小伙子,手里攥着买好的票,胳膊上搭着十来件一次性雨披,向着丁长盛叽里呱啦说个不停。
& & ——夏季不是壶口水量最大的时候,但今年反常,先头下了几场暴雨,水量突增,瀑布里跟冒滚烟似的……看了就知道了;
& & ——丁玉蝶已经在里头了,等着跟大家伙汇合呢;
& & ——黄河鲤鱼买到了,羊皮筏子在路上,今晚准到,歌手也到了,现在酒店休息。
& & 歌手?锁个金汤,还要歌手,载歌载舞吗?宗杭莫名其妙,易飒却知道说的是晚上的金汤仪式——三姓的仪式并不相同,黄河上兴的是伞头阴歌。
& & 一行人先去瀑布边看了一回。
& & 离得尚远,宗杭就已经目瞪口呆。
& & 满目都是浊黄色的水,像个煮沸了的大滚锅,没有一寸水面是平静的,说是水也不确切,就是泥浆,活了的发了疯的泥色浆汤,横冲直撞,妖形魔态,不止“壶口”那一处,龙槽两面也挂下无数水瀑,没过几秒,耳朵里都是隆隆水声,压根听不见人说话。
& & 半空中黄烟滚滚,都是翻腾着的雾雨,这种水面,别说行船了,一张纸飘下去都会瞬间卷没,再没露头的机会。
& & 离得近的人都撑着伞,或者穿雨披,还是免不了被溅得浑身泥点,那圆脸的丁家小伙子过来给宗杭发雨披,宗杭见易飒不拿,正想摆手表示自己也不用——一抬眼,看到有个穿雨披的人朝他们走过来。
& & 是丁玉蝶,雨披上滴滴沥沥、泥汤都汇成了河,脑袋上学当地人包了块白羊肚手巾,也被溅成了抹布色。
& & 他大声说了句什么,见两人听不清,于是连连招手:“这里,这里,过来说!”
& & 他带着两人往高处走,一口气走了好长一段才停下。
& & 人声和水声终于离得有点远了,丁玉蝶伸手指向龙槽口水流最湍急滚跃的那一处:“就那儿,看见没?我刚看见丁盘岭拿着金汤谱比对位置了,今晚,就在那个地方下。”
& & 易飒奇道:“那不是刚下去就被冲走了?”
& & 开什么玩笑,这儿比老爷庙都不如:老爷庙至少还能让你消消停停地下水、下潜,这儿这滚浪,人来不及沉下去就横漂着被冲走了。
& & 丁玉蝶反不担心,白羊肚手巾一摘,因静电作用而竖起的无数碎发似乎都在跃跃欲试:“一家有一家的本事,盘岭叔都说没问题,你怕什么啊,还能把我们淹死了?”
& & 说完又斜宗杭:“他来干什么啊?一个外行,我们干什么他都跟着,怎么着,想入赘啊?”
& & 宗杭没吭声。
& & 什么叫“一个外行”?他才是今天的主角好吗,再说了,入赘关你什么事?
& & 又不赘你家。
& & 和开金汤一样,锁金汤的水鬼也要保持体力,这趟锁金汤规模不大,丁盘岭不参加,只小字辈下水:丁玉蝶领头,易飒算助手,宗杭是“观察员”。
& & 看完瀑布水势,三人就被引去了停车场的车上“休息”,期间有人来送“水餐”,比鄱阳湖那次还不如:生削的黄河鲤鱼肉,外加一杯烧开的黄河水——透过玻璃杯看,泥沙在杯底淤了厚厚一层。
& & 丁玉蝶吃得郑重其事的,易飒则又玩鬼,找了个塑料袋,在宗杭的掩护下把水餐都倒了。
& & 一直等到入夜,才又有人来带他们进景区。
& & 这次感觉又不同,没有人声,没有灯光,满目黑魆魆的,像是回到远古时代,天地之间,除了山岩,就是大河。
& & 瀑布边一处,立了两个晕黄色光的野外照明灯,映照十来条憧憧身影,有几条影子被灯光拉得极长极大,横亘在河面上,看着荒诞而又不真实。
& & 走近了,先看到个老头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面皮皱结,头发、眉毛,包括上唇下颌上的胡须都是白的。
& & 衣服也是一身白,带中式盘扣的宽松长袖和灯笼裤,脚边立了把精工细作的红色油纸伞——让照明灯的光一浸,伞面上镀一层润泽油红。
& & 易飒低声给宗杭解释:“丁家的老辈,唱阴歌的。”
& & 据说这样的人都是打小训练,平时尽量不说话,即便说话也细声细气,细到什么程度呢,嘴边立一根燃着的蜡烛,一句话说完,烛火苗都不见动上一动。
& & 毕生的气力都用在唱阴歌上了,但要说唱得极其高亢嘹亮吧,好像又不尽然——个中门道,易飒也不是很清楚。
& & 距离老头不远处摆了张桌子,桌子上立了个发出绿色暗光的物件,围桌而站的几个人搓弄着手里的皮子,又凑到嘴边去吹。
& & 这是……吹气球?
& & 宗杭盯着看了会,这才发现那个发光的物件其实是个大肚口带透气孔的玻璃瓶,瓶子里全是萤火虫,而瓶身覆盖了一层绿色的树叶,所以透散出的光才是暗绿色的——气球吹好之后,他们并不急着封口,而是揭开瓶盖,随手捞一把萤火虫送进去。
& & 几人合力,效率很高,气球一个一个吹胀,然后填光,不多时,桌上桌下,脚边身侧,滚落无数光球。
& & 宗杭不知道那些气球其实是硝制过的羊尿胞,还很为那些萤火虫悬了会心,生怕它们没多久就被闷死了。
& & 暗处传来絮絮人声。
& & 循声看去,才发现龙槽边沿有围栏,是防止游客落水的,丁盘岭领了几个人,已经在围栏内了,正固定一根立柱,立柱顶上绕了一根拇指粗的钢索,飘飘悠悠晃在晦暗不明的光里,顺着钢索看过去,对面也有一根立柱,钢索的另一头就绕在那根立柱上——像架设在急流上空的一根电线。
& & 见易飒几个过来,丁盘岭吁了口气,指那根钢索:“待会,我们先用萤火‘定水眼’,水眼一定,就‘立水筏’,筏子立起来,‘阴歌开道’,路打开了,你们就可以下了。”
定水眼, 立水筏, 阴歌开道。
& & 宗杭听得一头雾水, 易飒也半懂不懂,毕竟隔了个姓, 虽然程序都明白, 但具体指的是什么, 亲眼看到的时候才能意会。
& & 她把宗杭拉到一边,低声吩咐:“待会下了水之后,不管别的, 先把丁玉蝶给抱住。”
& & 宗杭秒懂。
& & 这金汤穴里,应该有自动甄选机制,只接纳符合条件的人:是三姓, 也得是水鬼。
& & 他和易飒两个, 资质都差了点, 所以上次在老爷庙才被扔进了蛤窝洞里, 差点喂了贝壳, 这次说什么也得学乖点。
& & 时近夜半。
& & 羊尿胞光球少说也吹了有四五百个, 大束大束地簇在一起,薄透的尿胞间绿点蓬蓬,时聚时散,景象诡异,却也绚丽,丁盘岭点了几个人,让他们带着一半的光球去到槽对岸, 和这边遥遥相对,又让丁碛带着人,把羊皮筏子搬到水岸边。
& & 这羊皮筏子是十二座的,不过这“座”不代表搭载人数,意思是有十二个“浑脱”:浑是“全”,脱即“剥皮”,手艺精湛的屠户,宰羊之后掏空内脏,几乎不伤及完整的皮张,硝制了之后吹气使其胀满,还能胀出个羊形,这样的就叫“浑脱”,一个浑脱就是一“座”。
& & 十二座的羊皮筏子,就是十二具空心胀气的羊尸扎成方形,上头捆了个可以蹲躺的木头架子,这筏子有年头了,充气的羊皮都成了酱黑色,偏被灯光一照,通体油亮,看起来鬼气森森的。
& & 那闭目养神的老头睁眼的刹那,宗杭没来由地血脉贲张,觉得这锁金汤大概是要开始了。
& & 果然,一开始是敬水香,一根根线香燃起,底部拿烧热烫软的蜡迅速固定在沿岸的护栏上,夹岸相望,如两根平行的火线,差不多延伸了四五十米长,烟气细细袅袅,往上升起时被水浪气一激,又紊乱成了一蓬一蓬。
& & 紧接着,两边同时往下放出光球。
& & 数百个光球,在龙槽上方飘散开来,有的落下,有的上扬,有的被大股的水浪激地不断滚翻,两边的人都目光炯炯,也不知在找什么,时不时还发出鼓噪声:“这边!不对不对,那边,那个像!”
& & 易飒拉住丁玉蝶问:“这就是你们丁家的找水眼?”
& & “是啊。”
& & “怎么找?”
& & 丁玉蝶兴奋过度,眼睛只看得见无数萤火飘飞,哪有那个耐性给她解惑:“哎呀,你看就知道了!”
& & 放屁,易飒一肚子火,真想一脚把他给踹下去。
& & 倒是丁盘岭在边上听见了:“水眼就是一团乱水里的安稳地,这么给你解释吧,龙卷风遇神杀神,但它的中心地带,反而没那么大破坏力;一团乱麻纠在一起,看似没办法下手,但只要能找到关键的那个线头,一抽之下,一切都迎刃而解。”
& & “同样道理,祖师爷认为,越是乱的水里,就越是有那么一个支点,可以立足,也可以立舟,这个点就叫水眼……”
& & 话音未落,呼喝声又起,丁玉蝶叫得最响:“那个!那个!绝对是那个!”
& & 易飒循向看去。
& & 看到了,光球放到现在,有一半多已经被水裹着漂走了,还有些半空炸开,可怜那些萤火虫还未及飞高,就被排浪给打没了——剩下几十个,算苟延残喘,高高低低,飘飘晃晃。
& & 唯独一个,已经落在水上了,晃个不停,有一阵儿被外力都压扁扯长了,依然没离开那个位置,像枝头上冒出的一个花骨朵,任它风吹雨打,左右飘摇,就是不挪地方。
& & 丁盘岭身子一凛,喝了句:“就是那里!丁碛!”
& & 他大踏步走向筏子边,边走边撸起衣袖,易飒小小吃惊了一下:这个丁盘岭看上去貌不惊人,衣服下藏着的,倒是好一副健壮体格,一点也不输于小了他二十好几的丁碛。
& & 但见他和丁碛两个,分站羊皮筏子两边,弯下腰猛一用力,将筏子抬起来,做抛掷前的弧状摇摆,眼睛死盯住那随时都可能挂掉的光球,沉声道:“听我的,一、二、三!”
& & “三”字刚落音,筏子就飞了出去。
& & 那些一直鼓噪着的,现在反齐刷刷静了下来,易飒也屏住气,死死盯住筏子的去势,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浪头打翻,头皮都隐隐发麻……
& & 哪知筏子挨了几浪的水,四下险些翻覆了一回之后,居然在势若疯魔的激流狂涌间立住了!虽说立得不那么稳,像针尖上顶碗团团乱转,但没漂走!也没翻!
& & 喝彩声瞬间爆出来,丁玉蝶更是起头,啪啪啪拍巴掌,易飒松了口气,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一手是蛮漂亮利落的。
& & 回头看宗杭,他也看得目不转睛,嘴巴都闭不上了,半晌才喃喃:“你们家这个,可以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 & 丁玉蝶转头看他,那得意劲儿,就跟刚刚是他抛的筏子似的:“这算什么,你再看!”
& & 再看?水眼找到了,筏子也立住了,接下来,该是“阴歌开道”了吧?
& & 宗杭抬头看那老头歌手。
& & 他已经站到槽岸边了,一边腋下挟收束的红纸伞,另一只手里拎一盏点燃的煤油灯——不过立柱要重新调整,现在拉起的那道钢索,距离下头那个颠扑不定的筏子还远,要调整到点、线都在一个面上。
& & 而一干人调整的同时,有人帮着老头穿上束带,束带背上有吊钩,可以和钢索上的拉环吊具接在一起。
& & 宗杭后背泛起凉意:这不就跟电视上看过的那种偏远地区的“溜索”似的吗?这老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儿这个?
& & 事实证明,玩的就是这个。
& & 他在这提心吊胆的,老头倒是气定神闲,两个丁家的年轻人当拉索手,一点点拉动吊具上连接的滑索装置,把老头往钢索中央放。
& & 老头那略显佝偻的身形很快就出去了,晃晃悠悠,像钓竿上颤出的饵,差不多到筏子上空时,滑索顿住,老头揿动吊钩上的机括放悬绳,身子慢慢吊了下去。
& & 宗杭低头去看,老头的身形已经看不真切了,只能看清他手里拎着的煤油灯光亮,槽内黄河水翻起的大浪隐在黑暗里,真如一张张此起彼伏的大嘴,随时都能把那光吞掉。
& & 就在这个时候,丁盘岭说了句:“待会你们也这么下去。”
& & 宗杭心里一跳:这哪是锁金汤啊,步步玩命,相比之下,还是长江那套仪式温柔点,北方的人和河,果然都是粗犷的。
& & 不过这念头只一闪而过,注意力又全放在下头了。
& & 那老头快上筏子了。
& & 我靠,这可怎么立得住啊,那筏子颠得跟得了狂躁型多动症似的——尽管猜到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宗杭还是下意识一闭眼,就跟看恐怖片看到惨烈镜头时,宁可错过也不愿直面。
& & 再悄咪咪睁眼时,老头已经站上去了,非但站上去了,红伞也张开了,煤油灯光从红伞下滤透上来,像激涌的水流间飘落一抹温柔油红,晃荡不定。
& & 丁玉蝶啧啧:“厉害,‘乱流筏子脚生根’,这招我最差,练的时候,一分钟不到就被甩下来了,更别说还要一手撑伞一手拎灯。”
& & 丁盘岭淡淡说了句:“他待会还得唱阴歌呢,所以说各有所长、各有所专,能当水鬼也没那么了不起。”
& & 说到这,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 & 回头看,是一晚上都不见的丁长盛,怀里抱着一个长条大匣子。
& & 丁盘岭盯着匣子看:“祖牌请来了?”
& & “请来了。”
& & 看来这里头是丁祖牌了,宗杭伸长脑袋,满心想见识一下,哪知丁盘岭没要打开看,只是示意了一下立柱那头。
& & 丁长盛径直过去,没多久,滑索又往外放了,但这一次放的不是人——那轮廓,宗杭看得明白,是一个祖宗牌位。
& & 那牌位也只放到筏子正上空,那一处光弱,钢索隐了,吊线也隐了,只牌位的轮廓线分明,像在那悬浮。
& & 再然后,歌声就出来了。
& & 宗杭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捂耳朵,觉得唱得乱七八糟的,音不是音,调不是调。
& & 但手刚举起来,又放下去了,倒不是歌声变得动听了,而是他突然发觉,这歌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唱出来的。
& & 起始部分像农村跳大神,哼哼哈哈,然后声音就杂了,有长铃响,有耍鼓声,有娇俏女声,有轻佻男音,有老头咳嗽,也有看戏诸人的窃窃低语,拉拉杂杂,于汹涌水声里搅出翻沸声浪,让人觉得恍恍惚惚魂灵出窍,已然置身其间,但冷不丁一个寒噤,又发现下头只一个筏子、一个老头而已,哪来那么多声响?
& & 宗杭额角渗出冷汗,胳膊上汗毛奓起了就没见下去:觉得老头这一歌,勾出了黄河水底无数阴魂,飘飘散散,凄凄切切,都在和着他的音调扒住筏子婉转吟哦,只是自己看不见罢了。
& & 到中途时,声音蓦地一收,只剩了一道声线,并不高亢,却刁钻至极,似乎扭着身子在水浪间钻进钻出,不管你怎么企图压它盖它,它总能找到缝隙破出。
& & 也不知道老头这嗓子是怎么长的,声音钻到极尖细处,没有丝毫缓冲,瞬间又转做了低沉沙哑,像个走投无路的落魄老人,哀哀呼天,嘈嘈抢地。
& & 槽岸两边,几乎所有人都定着不动,似是被歌声给魇住了。
& & 只易飒神游天外,她是惯会开小差的,听到一半就东张西望,目光一时栖在红伞上,一时又粘在祖牌上。
& & 鄱阳湖底,姜骏推水,如同在密码盘上揿入密码,密码输对了,金汤穴开门了。
& & 那这龙槽底下呢,待会下了水,身子都稳不住,更别提“推水”了,而且为什么要唱阴歌呢,这儿声响这么乱,瀑布音又是“百丈鼓”……
& & 易飒心里蓦地一跳。
& & 难不成黄河底下的这个密码盘是“声控”的?
& & 有这个可能,晋陕一带,伞头秧歌很有名,但伞头阴歌是丁家独有的,歌者从小接受训练,只练这一首歌,这歌完全反常理、反套路,简直不是人能唱出来的,即便被人偷听到,想模仿一句都难,更别提从头到尾记下来了。
& & 水眼上的伞头阴歌,加上四面的百丈水声,又有祖牌悬空——被这音阵裹在中间的祖牌,也许就是那根关键的“弦”,只要被拨动了,就能向水下传递什么信息……
& & 就在这个时候,筏子上的老头猛然抬头。
& & 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 & 身子还在飘摇,脚底还在乱晃,但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一片死寂。
& & 再然后,有滴答的声音落在伞面,先是一滴两滴,然后渐渐纷乱,滴答声不绝于耳,像是有成千上万道雨线,都砸在那透着光的绯红伞面上。
& & 老头用尽浑身的力气,大吼一声:“开门啦!”
& & 这话一出,别人倒还好,只丁玉蝶跟个急脚鸡似的,三两步就狂奔到立柱边,催着人给他接吊钩。
& & 易飒吁了口气,甩了甩手也过去了,宗杭正想跟上,丁盘岭上前一步,递了个防水袋封着的东西过来。
& & 宗杭迎着光看。
& & 是个……照相机?
& & 丁盘岭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最老土的胶卷相机,你可能都没见过,又叫傻瓜机,摁一下就行。听说电子设备在下头不灵,这种不那么先进的,也许反倒……能派上用场。”
阅读权限255&主题1012&UID8587893&帖子39062&积分50329&
91UID337817 &精华0&帖子39062&财富370694 &积分50329 &在线时间2663小时&注册时间&最后登录&
发表于 前天&16:43
本帖最后由 微笑的陶陶 于
16:44 编辑
丁玉蝶荡到筏子上空, 先收了祖牌, 然后将身子慢慢放下去, 脚刚沾到筏子,就觉得心慌气短, 赶紧伏低身子, 乌龟爬状死死扒住了筏子。
& & 在槽岸上看时, 还只觉得是颠簸,真到了筏子上,才知道厉害, 迎头都不知道吞了多少口泥水了,耳边风声水声不断,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甩将出去, 丁玉蝶头一次觉得, 和唱阴歌的比, 水鬼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 & 易飒和宗杭依次下来, 也有样学样, 手脚死死扒住筏子, 那情形,颇像三只求生的蛤-蟆,唯恐被甩脱出去。
& & 上头又陆续放下三只密封的防水背袋,这就是为了一切都看起来像真的而准备的待锁“宝藏”,三人都腾出一只手,艰难地取了,再各自背到背上——分量不轻, 也不知道丁盘岭都安排着往里头塞了什么。
& & “开门了”是真,但从哪儿进门还需要指引。
& & 那老头一手仍紧握红伞,另一手却拎着煤油灯,在震荡不定的筏子边迅速移照,丁玉蝶眼前发晕,只觉得满目是浪,也不知道老头到底想找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灯光到处,那一片的水面上忽然凹出个漩涡。
& & 老头激动得声音都变调了:“快!就这儿!跳!”
& & 丁玉蝶血冲上脑,想也不想,一头就往漩涡里扎,易飒和宗杭的反应也不慢,边跳边伸手往前去抓。
& & 三人几乎同时入水,“扑通”声还未及响起,就被随后卷来的浪给打没了。
& & 槽岸上随即亮起数盏探照灯,雪亮的光柱都死咬在筏子左近。
& & 之前怕影响煤油灯光找“门”,不敢打灯,但现在即便打了,好像也是白费——黄河水浊,卷起浪来更浊,再强的光都透不下去了。
& & 丁盘岭嘴唇紧抿,盯着那一处看了半天,才吩咐丁长盛:“关了吧,别叫有人看见,还以为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 & 丁长盛挥了挥手,那几盏灯又陆续灭了。
& & 丁玉蝶入水瞬间,激动万分。
& & 不是他矫情,但真的有水鬼终其一生,都没挨过锁开金汤的边儿,更别提“领头”了,所以有这趟经历,他的水鬼生涯,也算是功德圆满。
& & 但这激动,秒变愤怒。
& & 妈的,什么鬼,那两人是不是有病?又不是不会游泳,一人死死抱住他一条腿是几个意思?差点抱得他在水里劈叉。
& & 一条腿挂一个人,每个人身上还背了包,这分量可不是盖的,丁玉蝶拼命想往上泅浮,还是止不住下沉,想破口大骂,水下没法发声,想连打水鬼招剁死这两个二百五,黄河下头又两眼一抹黑,打了估计他们也看不见。
& & 先干正事吧,回去了再跟他们算账。
& & 丁玉蝶抬起祖牌,向着额头贴过去。
& & 易飒死抱住丁玉蝶的腿入水。
& & 这腿徒劳抽蹬,显然是想把她甩脱,可能吗?怕是不知道她脸皮有多厚。
& & 易飒对丁玉蝶的挣扎嗤之以鼻,反抱得更紧,眼睛看不见,就拿身体去感知这水下动态。
& & 这感觉,像……
& & 养尸囦,对,养尸囦!
& & 似乎跳进了一个水团,虽然一臂之外就是激流汹涌横冲直撞,人也能感受到四面的冲力,但水团能稳住,人就不会被冲走。
& & 接下来呢,这水团会在水下移动吗?像水底车,或者电梯,带她们去想去的地方……
& & 正寻思着,身周忽然爆开一圈明显的气流震荡,与此同时,易飒觉得似乎有一道雪亮的闪电光,直劈进她脑子里。
& & 只这一秒都不到的功夫,她居然还连转了好几个念头:
& & ——跟老爷庙那次一样,这应该是祖牌起作用了;
& & ——但她是怎么回事?她不是不受影响的吗?
& & 她身子没受得住这力,整个人弹撞了出去,中途似乎碰到了什么,好在虽然脑子混沌,身体的下意识反应还在,当即死死抱住。
& & 再然后,那道雪亮的闪电光在脑子里铺展开来,铺得无边无际,又像没信号的电视屏幕那样,满屏雪花,复又渐渐清晰。
& &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手术室里。
& & 但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她,穿防护服的医生护士把手术台围得水泄不通,明晃晃的手术大灯下,能听到手术器械的轻微碰响。
& & 一个护士忽然转身,端着个手术盘走出来,手术盘里,放了张血淋淋刚剥下的人脸皮,两个眼洞突兀地瞪着她。
& & 易飒腿一软,差点瘫坐到地上。
& & 不多时,手术台边围着的人就散开了,一个娇俏的年轻女子从手术台上坐起来——也不能说是年轻女子,她只有那张脸是青春娇嫩的,除此之外,脖颈上,还有手臂上,皮肤都已经松弛下耷。
& & 她在打手机,语调很轻快:“我做完了,很快,你做不做?”
& & “真的很合算,你想想原生的脸,又娇贵又费事,用那么贵的护肤品,它该起皱纹起皱纹,该没弹性没弹性,换上人造的就不一样了,全天候提拉,随时自净……我已经打算做个全身换肤了……”
& & 场景一转,又到了类似大学课堂,替代黑板的LED屏上有一棵巨大的进化树,从根部的“真核生物、原核生物”开始,两边分叉,一边植物类,一边动物类。
& & 动物类的那一边,从单细胞动物到腔肠动物,从线形动物到鱼类、两栖类,哺乳类高高站在树顶末梢,代表的形象俨然是个人。
& & 讲台上,清瘦的中年教授正意气激昂地陈述:“这棵进化树会不会永无止境地生长下去?我认为不会。”
& & “月亮圆了就要缺,水满了就会溢,花盛放了就要衰,人老到极致就会死——最本质的道理,永远蕴含在最普通、最常见的现象当中,进化走到尽头,就是退化。”
& & 底下有学生戏谑似地起哄:“所以我们人类进化到后来,就要往回走了,又变成单细胞动物吗?”
& & 教授微笑:“退化就代表消亡,但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消亡有很多种方式,对吗,易飒?”
& & 易飒措手不及:“啊?”
& & 教授却盯着她不放:“是吗?易飒?易飒?”
& & 这声音忽然好耳熟。
& & 像宗杭的。
& & 易飒艰难地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 & 宗杭正趴跪在她身边,一脸焦急:“易飒,你怎么了啊?”
& & 这是哪啊?易飒抬眼去看。
& & 要说是山洞,又不像,这是条通道,但凿得四四方方,边上坐着丁玉蝶……
& & 看到丁玉蝶,易飒唬得整个人都精神了。
& & 他背着背袋,还保持着两手握持祖牌贴额的姿势,眼睛圆睁,却毫无光泽,像个突然僵硬的木偶。
& & 易飒问宗杭:“怎么回事啊?”
& & 宗杭说:“我还想问你呢。”
& & 他给易飒讲起之前发生的事:下了水之后,他依照易飒的吩咐,死抱着丁玉蝶一条腿不放松,正较着劲,身子一重,自己的双腿又被人抱住了。
& & 他没想到那个是她,还以为是黄河底下真有水鬼,被阴歌招上来了,吓得头发险些奓起——正想腾出一只手去掰,脚下忽然一空,整个人,不,串在一起的三个人,全滑了下去。
& & 他比划给易飒看:“像那种圆筒的、螺旋的滑梯一样,人像球一样在里头骨碌骨碌乱撞,最后砰一下,就落到这了。我骨头都要散了,好不容易爬起来,就看到丁玉蝶……”
& &说到这儿,他止不住打了个寒噤:丁玉蝶这姿势,看多久都觉得瘆人,跟蜡像似的。
& & “……丁玉蝶这么坐着,你抱着我的腿,易飒,你上次,不是不受祖牌影响的吗?”
& & 是啊。
& & 易飒转头看丁玉蝶,下意识把身子挪远了些:“难道是因为我当时抱着他?”
& & 丁玉蝶就跟个导电体似的,把祖牌的某些功用给她导过来了?
& & 宗杭不觉得:“但是我当时,也抱着他啊,所以我跟你……还是不一样的?”
& & 易飒喃喃出声:“不一样,我们俩有差别。”
& & 她是三姓,1996年在三江源出的事,不那么较真的话,她其实也算是接生者,是接生者,就能开门进金汤穴,否则怎么接生呢?
& & 而宗杭既不是三姓,又不是接生者。
& & 易飒脑子里有根线渐渐清晰:“漂移地窟出事的人里,只有两个水鬼,其它的,不是抖子八腿,就是水葡萄,他们应该都被赋予了水鬼的能力,以便来日下水。”
& & “但想开金汤穴,需要跟祖牌直接接触,上次在老爷庙,我没有近距离接触祖牌,但这一次,我抱着丁玉蝶,受到了一些波及。”
& & 宗杭心里一动:“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趟锁金汤,没有丁玉蝶也可以,你加上祖牌,照样能进来?”
& & 也许是,但她不敢尝试:自己只是抱着丁玉蝶的腿,脑子里就已经出了那么多莫名的画面,如果是额头直接跟祖牌接触呢?会不会从此脑子不是自己的了?彻底成了“它们”的傀儡?
& & 这祖牌,她可真是碰都不想碰了。
& & 易飒转头看向背后:“那我们是从哪儿滑进来的呢?”
& & 背后不远处就是一堵竖直的山岩,又或许是息壤?但听宗杭的描述,几个人滑落下来,用了不短的时间,这儿又没有沉船废料可以利用,想再烧出去,简直天方夜谭……
& & 正思忖着,丁玉蝶忽然噌地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 & 他关节僵硬,站起的姿势极其诡异,然后同样僵硬地迈步,向着廊道深处走去。
& & 看来,只能紧跟丁玉蝶了:以前三姓锁开金汤,用时不过一两个小时,从来都平安进出,只要跟紧带头的人,不乱碰乱动,应该没问题。
& & 易飒招呼宗杭跟上,两人缀在丁玉蝶身后,边走边四下观看。
& & 这廊道,真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上还留有一铲子一凿子的痕迹,而且走着走着,居然发现了岩画。
& & 岩画就是石刻文化,一般认为,是人类祖先用石器作为工具,通过石刻来绘画,记录当初的生产生活,绘画线条一般都粗犷、古朴,表达的内容有简单到一目了然的,也有晦涩到比天书还难解的——毕竟三岁一代沟,现代人和原始人之间的代沟,怕是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
& & 正经过的这段岩画上,有无数很抽象的小人,或奔或跑,或拽或拉,底下长长的波浪线,也许代表了大河,又有高高的土台耸立,上头站了两个大一点的小人,其中一个头上顶了道下扣的弧线,似乎是个蓑笠,手里像扶了根翻土的木叉。
& & 宗杭脱口说了句:“大禹,大禹带人凿的这条走廊!”
&&怎么就是大禹了?
& & 易飒一把揪住丁玉蝶的裤子后腰, 成功阻碍了他继续往前, 然后问宗杭:“为什么?”
& & 难得有机会给易飒解惑, 虽然全身都浸了泥水,宗杭还是精神高涨, 掰着手指一条一条列举。
& & 首先, 景区有传说啊, 黄河原先不打这儿走,是大禹引过来的,怎么引?一斧头劈出壶口太夸张了, 肯定是带领无数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凿道开渠啊。
& & 其次, 劳动很累, 累了要放松, 劳动人民歇息的时候, 就寄情于画画, 以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纪念这伟大工程——看这图, 明显描绘的是河工治水。
& & 再次,土台上站着的其中一人,头戴蓑笠,手扶木叉,很符合大禹的形象,他记得不管是动画片,还是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 大禹都这造型。
& & 易飒问他:“那大禹修这走廊干嘛?还有,土台上还站了另一个人,是谁?”
& & 大禹为什么修走廊,宗杭是不知道,但对这另一个人,他确实有点想法:“会不会是你们祖师爷啊,丁祖?”
& & 有这可能,但这图上能看出的太少了,更关键的应该还在后头,易飒松开丁玉蝶:“走吧。”
& & 丁玉蝶已经做了半天的原地踏步了,终于被放开,身子趔趄了一下,继续僵硬着往前。
& & 宗杭想掏出相机拍照,犹豫了一下,还是先赶上去:胶卷机最多能拍三十来张,不能瞎浪费。
& & 这走廊很长,廊顶每隔一段,就有个“灯”,材质像是息壤,“灯”身各不相同,都是奇形怪状的头,有鱼的,也有龟、鼋、蛟的,还有些像畸形的小孩头,易飒怀疑那就是传说中的“虫童”,原本生活在黄河上游,民间也叫“水猴子”。
& & 看来这上头的“灯”,都是黄河里存活的、或者曾经存活现已灭绝的生物形象,息壤的光本就游移不定,光影映照下,一张张头脸都栩栩如生,稍不留神,就会有那些头都在“活动”的错觉。
& & 沿途每隔一段就能看到岩画,有时是人,有时是动物,有时又是变了形的太阳,总之都是一挂的原始拙朴风格,看多了有些审美疲劳,宗杭渐渐心不在焉,又嫌这走廊太长,正想建议易飒加快脚步,易飒忽然“咦”了一声,蓦地停下,也不知看到什么稀罕的了,以至于忘了去抓丁玉蝶。
& & 宗杭赶紧窜前两步,揪住丁玉蝶的衣领,强行把他拖住,又回头看易飒:“怎么了?”
& & 易飒僵了几秒之后才抬起手,指了指身子左侧、走廊偏上的地方。
& & 宗杭探头过来,触目所及处,先是好笑,但还没等这笑放开,脑子里一懵,一股凉意从心头腾腾冒起。
& & 这他妈画的……不会是电脑吧?
& & 应该是,一面四四方方的屏幕,还带底座的,屏幕两边长出手来,正抓住一个人,像是要往嘴里填,那人的脑袋已经没入屏幕里了,只余脖子以下露在外头。
& & 这图,换了在别的任何地方看到,宗杭都不会觉得特别:跟讽刺漫画似的,致力于劝诫年轻人别沉迷上网,创意称得上相当老土了。
& & 但出现在这儿,简直匪夷所思,跟周围的绘画风格完全不搭也就算了,画的还是个……电脑?
& & 宗杭不甘心,抬手过去摸了摸:这个不是凿刻的,是画的,不知道用的什么原始材料,可能混了动物油脂,整体呈暗红色。
& & 易飒低声说了句:“阿尔塔米拉野牛。”
& & 什么?这名词可真拗口,宗杭都复述不全:“阿什么拉牛,是什么东西?”
& & 易飒解释:“是西班牙人发现的一个远古人类洞穴遗址,距今上万年了吧,洞穴里画了很多野牛,用色鲜艳又大胆,透视精准,形态非常生动,跟同期、甚至那之后几千年原始人的绘画手法完全不同,极具现代风格,以至于西班牙人将这些画公诸于众时,没人相信他,觉得这是恶作剧。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那些画,根本不是远古人类画的,作画的另有其人。”
& & 三姓本身就是诡异和超自然的存在,所以一直很关注古今中外的种种未解之谜,不敢说精通,但只要提起来,基本都能说出个大概。
& & 宗杭盯着那副画发呆。
& & 他是没见过什么西班牙野牛图,但眼前这幅,他很确定不是原始人画的。
& & 也许是外星人画的,又或者……
& & 宗杭脱口问了句:“易飒,会不会你们三姓的老祖宗,其实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 & 越想越像。
& & ——三姓的祖师爷像是能预卜未来的先知,“不羽而飞,不面而面”这种话,也许对他们来说,不是未来,而是曾经呢?
& & ——他们有本事,却不做官、不入仕,因为他们熟悉历史,知道皇朝更迭的频繁和残酷,今日将相明日牢囚,做到多高的位置都不如隐匿民间、靠独门手艺讨生活来得安全持久。
& & ——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厉害了,能用体细胞克隆出牛羊猫狗,就差克隆出人了,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好像换头手术都有望实施,那未来呢,也许死而复生根本不是难事,尤其是对那些遭受意外而死的人,只要给死去不久的尸体注入某些强力的再生细胞,丁盘岭说的“受精卵”,可能就是这样的再生细胞。
& & ——还有息壤,它也许是某种能量物质,像电脑那样,能够执行复杂的操作程序……
& & 易飒说,什么事都能推到外星人身上,其实同样道理,推到未来人身上也说得通:正如明末的姜射护压根无法想象什么是飞机、视频、电子支付,现代的人,也想象不到未来会是怎样的态势。
& & 宗杭头皮发紧,觉得自己勘透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
& & 他端起相机,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 & 再往前走时,宗杭就分外关注两边的岩画,生怕漏了什么关键的,果然,没过多久,又发现一幅,内容没第一幅那么暴力,但越看越让人心头冒冷气:那是一个背对着电脑的人,不知道在忙什么,身后的电脑样子有些狰狞,咧了嘴在笑。
& & 画这两幅岩画的人,好像挺不喜欢电脑:这些电脑又是吃人又是背后冷笑,真跟成了精似的。
& & 宗杭把这张也拍了,再次向易飒强调自己的结论:“穿越,肯定是穿越。”
& & 他忽然觉得踏实:看来自己不是什么怪东西,而是未来科技的产物,他一个现代人,提前享受到了还没有臻于完美的未来科技而已。
& & 易飒沉吟。
& & “祖师爷是未来人,穿越回来的”,这说法的确可以解释一些事,但穿越这种事,本身就太多悖论,而且更关键的是……
& & 易飒说:“穿越这词我懂,但至多往回穿个几十年,修正一下既往的小遗憾。至于一穿就穿回了上古时代,然后大费周章地安排什么水鬼、金汤、轮回?你直接穿回今年不就好了吗?”
& & 这话正打在点上,宗杭不死心,还在磕磕巴巴:“会不会是,他们穿越的时候出了故障,穿越表设置得太靠前了,一个没注意,回到大禹治水的年代了,只能从长计议?”
& & 易飒哭笑不得。
& & 还“穿越表”,看不出来,宗杭还挺会造词儿,再说了,这个“从长计议”,也未免太长了。
& & 她有一种即将接近真相,但始终差了点什么的感觉。
& & 接下来这一段,没再出现怪画。
& & 也许是那个丁祖在这里参与河工时闲得无聊,见别人都在抹抹画画,也随手画了两张,反正不会有人知道他画的是什么,而且当时的人,也并不欣赏这种风格,所以没人跟风,也没人把他的流派发扬光大。
& & 廊道到底,是一堵墙。
& & 墙面上如同之前的廊顶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各色水族的头,但不是固定不动的:随时涌起,随时没去,位置杂乱无章,像是水面竖起,而各色凶猛水禽争相露头。
& & 丁玉蝶缓缓抬起右手。
& & 他的手法完全让人看不出章法:有时是拍,一掌把一个鲇鱼头拍回墙内;有时是拽,拽住蛟龙的长角,把龙身拽出半米多长——这长度显然是有严格限定的,增减一分都不合要求;有时又是拧,五指摁住虫童的脑袋,左旋三下,右旋两下。
& & 如同姜骏“推水”时一样,是套繁复的密码,直接由祖牌设定给出,丁玉蝶只是傀儡般接收,然后照做——易飒怀疑,为了绝对保密,这密码是随机的,每次都不一样。
& & 宗杭看直了眼之余,不忘端起相机拍了一张。
& & 也不知道反复操作了多少次,这堵墙忽然像双开扇的房门一样,往里张开。
& & 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虽然不足以和鄱阳湖底金汤穴的规模相比,但也足够大了,可里头没有巢脾,也没有尸体。
& & 相反的,异常空旷。
& & 整个空间呈圆柱形,底部边缘处有无数扇门,都是打开的,门内延伸着的,也是往四面八方去的长长的走廊道。
& & 而底部中央,是个底座呈圆形、拾级而上、越来越高的高台,第一层台阶上,有无数石刻的骷髅头,摆得密密麻麻。
& & 易飒脑子里电光一闪,急回头去看来时的走廊,又看这高台:“祭坛?太阳祭坛?”
& & 她给宗杭解释:“中国上古时代,是有太阳崇拜的,你看我们的神话传说里,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羲和望舒,大禹就活在这套文化体系里,所以大禹那个时代,也是把太阳当神来崇拜的。”
& & “你说的没错,这整个工程,也许真是大禹牵头修建的,中间这个洞是圆柱形的,高台又是圆台形的,我们刚刚进来的走廊,其实是一道太阳射线,这下头有这么多走廊,就是无数射线,你把整个轮廓拼接到一起看,像不像一个正散发光芒的太阳?”
& & 引黄河入龙槽,在上古时代,是极大的工程,依古人的性子,势必要造坛祈神,黄河跟长江不一样,丁祖很可能完全找不到那么大的地下穹洞去储存尸体,所以他说动大禹,耗用民力,造了这样一个看似是祭坛,实则是轮回渡口的地方。
& & 黄河一旦引流成功,这地方就会瞬间被埋于水下,数千年黄沙淤积、河床抬高,再加上上头就是激流瀑布,这里更加固若金汤,安全系数比之老爷庙,只高不低。
& & 只是,只有一个祭坛……连用于嫁接的尸体都没有,怎么去当轮回渡口呢?}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判断级数收敛的八种方法这两个级数的敛散性,求详细步骤,谢谢
- ·不稳定的裂隙,塔瑞斯米德加尔特世界之树裂隙怎么过去这个任务怎么做?(没有系统路径提示。。。)
- ·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思想观念,1958年出生的人已经跟1958到1978年处于什么状态出生不是同辈了,对吗?
- ·袋中有5个球,其中3个红球,2个白球红球,3个白球,无放回的每次取一个球,直到取得红球为止。用X表示抽取次数,求分布函数
- ·EXCEL中多excel表格两列数据合并并合并?
- ·pcddusage error 110866——lol是什么啊?全拼!?
- ·11086cpPK10历史开奖结果——梦幻梦幻西游女娲神迹迹剧情流程
- ·我主播卡尔的女朋友是谁干游戏主播那一行的
- ·我有一颗老鹤天珠一颗多少钱谁能帮我看看。我有一串化石鹤天珠一颗多少钱手链 不知道是什么化石。有风化纹。有字。请老师专家鉴定
- ·jq01ts和i110866qxc——LOL的战区系统里面箭头什么意思啊?
- ·11086wangyicaipiaoo七乐采彡——CF画面颜色怎么调
- ·obs无法连接到服务器ICloud 怎么办
- ·chronograph watch是卡地亚,还是卡西欧?
- ·华硕光驱驱动下载PRO554n光驱怎么打开?
- ·快手换绑定的快手手机号被注册绑定多长时间能通过审核
- ·红米2A增强版红米note3卡刷降级级故障求解:能开机能冲电,界面上手机自带功能标志全暗了,下载的笫三方应用正常
- ·苹果手机美版appstore机子为什么打开app下载东西突然热门搜索全部变英文重启没用
- ·什么手机qq播放器 重复播放能重复播放视频?
- ·手机未知文件格式格式文件可以删吗
- ·这辆道奇多少钱一辆是什么系列什么型号?
- ·昨天晚上玩手机,躺在床上,突然后背骨头响就像骨头窜位一样疼,好像姿势不对引起的,是什么情况呢,?
- ·冰箱和冰箱与热水器安全距离能挨多近
- ·24平米空调多大房间装多少匹大空调?
- ·带什么镜头可以带上飞机吗比较好,请各位前辈介绍下经验
- ·这个可以在笔记本外接独立显卡电脑上外接显卡吗
- ·☆那些自称小米加工设备价格良心的进来看看小米加工设备价格6有多
- ·杭州市民卡能坐地铁吗要怎么样存钱进去可以坐地铁。
- ·本人在苏州市买房条件2015年,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房贷还没有还清,因为女儿的小孩想在苏州上学能不能过户给她
- ·废铜烂铁铁的回收价格格
- ·注册税务师考试报名怎么知道考试报名成功
- ·lhcgb t 11086 2013事业的兴旺是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象征???
- ·自己申报工伤伤残等级鉴定标准鉴定为十级伤残,单位不配合向工伤伤残等级鉴定标准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伤残等级鉴定标准理赔该怎么办?
- ·本人在苏州市房子2015年,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房贷还没有还清,女儿想把房子过户给她,我想问问现在能不能过
- ·淘宝物流一直显示揽收包裹正在揽收六天了还没有显示物流,开始联系卖家的时候卖家说取货了但是物流放假,后来在问卖家给我
- ·刷単网络兼职被骗已追回怎么追回本金
- ·生鲜果蔬超市财务做帐做帐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