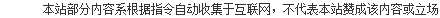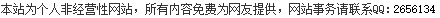引起脑衰的根夲原因是什么^?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6-23 08:40
时间:2022-06-23 08:40
每到这时候总是十分尴尬。
是啊是啊我也死了,没比你晚个百八十年还真是对不起呢。
我一边在心里吐槽,一边打开柜子取了茶罐出来。还是岁之迢最喜欢的那种绿茶,清明前的新叶,他自己炒的,不过现在大概不需要炒了——他永远有拿不完的茶了。
老头倒是挺意外。我过来时他正一副葛优躺样儿坐沙发上看电视,出口的却是少年声线。
然而其实我并没有把如上吐槽真的说出口。我只是草率地嗯了一声,一起蜷近沙发里。在这里,岁之迢并没有用他最后离世时用的那个身体,而是倒数第二副的面孔,这让我有点意外。我记得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那次药物事故,是见过一次青年的岁之迢的。
那真是个很意气风发的,明亮的,带着股侠客般的潇洒的人。
比起青年人的风度和健康,我不信他会更喜欢行将就木的身体。
岁之迢从刚刚起就不再看电视了,一直盯着我的脸。大概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表情管理技术一直没有长进,又或者岁之迢更厉害了,总之,他再一次窥破了我的所思所想,笑眯眯地解释道:“要做前台招待,太年轻总是不好。”
我心说屁,你个人老成精的怎么可能会为了这种理由做事,我又不是没听见你声音都变了。但面上总归不能显,只好敷衍地点了点头,随口问:“老江当年让我把那玩意放回来,是给你吗?”
“你觉得是给我吗,怀刑?”
我盯着他的眼睛。半分钟后,我也笑了起来,带上了应付那边儿的常用表情,作小姑娘式轻快状,声线提高了一个度,满是信任地说:“我觉得是啊。”
“不给老师,又能给谁呢?”
岁之迢打量我一眼,笑了笑。老年人站起来,鲜绿的光河从他身上褪去,穿着那套和叶归差不多的,洗的发白的棉质长袖,少年模样的老师笑着摊开手,道:“拿来。”
我用左手捏了捏右胳膊里包着的东西。
“那玩意儿”圆滚滚的,比起Sylvester当年塞进来的时候软了很多。好歹也填了我三十年的空眼眶,没说熟稔到烂熟于心的地步,也能分辨出到底是不是假的。徐褐羽这小孩果然聪明,不仅知道这东西离不得肉,还晓得挖出来后给我再添只电子眼。
只是可惜,原装货虽然应该也在这边,估计也早就腐化,再也找不着了。
电子眼其实也挺好。已经过了三十年一只眼的日子,一开始视宽骤然增大还不太习惯,这东西就像董九娘的人工耳蜗,一开始接收到的是一种滋滋的,无法言喻的电信号,习惯之后就能看到清晰度颇高的图像,像装了只近视的眼睛。人脑果然是最精密的处理器。
一边想着,我一边顺手拿来了桌上的水果刀,顺着缝隙小心挑开被缝了医用缝合线的伤口,绿色的小玩意在肉里适应良好,我看着有和真皮层长在一起的趋势,也不管痛不痛了,草草从伤口里揪出来——反正已经死了,也不可能因为细菌感染再死一次。果然,沾着血的“弹珠”在离开血肉的瞬间,马上还原为有着坚固外壳的种子,连接的缝隙出挑开了一线苍白的绿,正是刚刚苏生的新芽,趁着还没长成,我赶忙又在手指上开了条口子,才小心地捏着这东西递给了岁之迢。恢复年轻的老师笑了一下,不知从哪儿摸出片剃须刀片,面不改色地在手心滑了一下,然后,用沾着血的手心,他握住了我同样正在滴血的手指。
可能是这个世界观里最关键的东西,就这样又一次沉默地,无声无息地完成了寄生。
只是不知道他要把他带往哪里。
在我们开始用伤口凝胶各自止血时,我漫无边际地想。岁之迢似乎要分担疼痛带给他的精神压力,又或者他和我想的一样,的确和这玩意儿的匹配度不高,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用涣散的口吻询问着我的死法。
“怀刑。”他和气且虚弱地问,“你也是脑衰?”
“不。”我咧了咧嘴,“没脑衰,好着呢。”
我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才意识到他前年死的时候,法案还没有批下来,遂解释道:“是安乐死。”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怎么可能。”我说,“谁肯给我批啊。我只是偷偷的,小心一点,再用用从你们那儿学来的小技巧,再找个会来事儿的……你懂的,那一杯可要不少钱。”
“LC的现行法才通过几年,你就上赶着当出头鸟?”
“那无所谓,反正死都死了,还能鞭尸不成?”
年轻人微笑着凝视窗外。
“只是另一个开始。”
我笑嘻嘻地挨着他坐。
“哪里不算死?死就是断绝和人世的联系,不再与常世的人相见,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老师要是真说不过我就好了。”
岁之迢笑笑。他伸手按了按我的头发,那只手也不再是往日长着皱纹的手,年轻细长又有力。如果现在惹他生气,大概就不是被镇纸打打额头的事儿了,被一路从街头打到巷尾也说不定。我为这个想法抖了抖,明智地决定暂时装乖点,老师也不说破,只是握了握手心里的东西,说:“走吧。”
他笑着说,视线并不在我这里。
窗外还是LCST研究所当年的景象,灰白和淡青色的墙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装潢,一棵红缅树立在中庭里。他的办公室有深红的纱帘和已经不太新的纱窗,在如洗的,蔚蓝的晴空里,浸润着午后的悠闲气氛。
“已死的人,活着的人,都是可以的。这是你的世界,想见什么都行,想谈什么都好。”
“谈到什么时候?”
岁之迢看了一眼日历。
“现在是永昼。”他说,“过几个月,等到永夜来了,再回来找我。”
我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他的手。
“你还能回来吗?”
岁之迢露出一副和气又无害的表情。
“还有另一位朋友想见你。”
世界的交界线,荒谬的无端崖。无端崖下是时间的洪流,独木桥上一次只能过一个人,所以总得被挤得跳下去几次,我猜他也跳过,我们都是在这条时间线上垂死挣扎过的旅客……
我不再多言,像之前的无数次一眼,伸手推开了虚掩着的门,门外果然是深不可测的峭壁,是翻滚的浪花,只是这次,对岸没有一个空中花园系统去加载人最想见的东西,所以那里是它本来的样子:巨大的黑色实体,连光也无路可逃。
既然我能跳下无端崖,证明已经有人走了过去。
这个问题没留给我多想的时间,因为岁之迢在我身后轻轻推了一下,某种粘腻的液体沾在衣服上,这让我判断出那是他开过口子的手。
我平直地向前走了一步。
晋江APP→右上角人头→右上角小框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脑衰竭的症状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深圳理工大学将首次本科招生2024年在哪些省份招生?招生计划是多少?
- ·深圳理工大学将首次本科招生的本科招生方式如何?在哪个批次录取?
- ·qq三国晚上挂机自动掉线5月23日更新后云服务器上不能挂机了?
- ·魅励计划公认最好的减肥产品品怎么样?有人知道吗?哪里可以买到?
- ·平安养老社区人寿的社区网格服务具体是什么?是最近推出的新服务吗?
- ·Excel怎么实现下述动态数据的文字表示?
- ·温岭北纬28°,夏至日4点58分日出,天什么时候开始亮?
- ·菠萝啤可不可以和鸡精一起做菜吃?
- ·Excel中如何自动引用数据?
- ·这句话对不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表述,对不对?
- ·这句话对不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表述?
- ·矩阵的秩求解
- ·激光打码机打的字打一半就折返回来是怎么回事13991724569?
- ·目前,中椒生物具体有哪些产品?
- ·求解图文步骤,CAD轴测图,有高悬赏,谢谢
- ·maya是怎么给场景或模型的各个面贴上指定的纹理的?
- ·中国哪一年365天全部都下雨?是四川吗?
- ·问一下各位中椒生物的理念是啥?
- ·路人被椰子树叶砸倒颅内积血,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 ·引起脑衰的根夲原因是什么^?
- ·就目前而言,中椒生物的需求量大吗?
- ·maya建模时候一个面的四个点必须保持共面吗?
- ·word这条竖线怎么解决?
- ·对于目前来说,这个中椒生物有哪些竞争者?
- ·面积不变,长增加10米可以求出原来的宽,宽增加2米可以求出原来的长
- ·什么方向太阳最小?
- ·河南暴雨高温无缝衔接,天气复杂多变,我们需要防范些什么?
- ·乌鲁木齐新东方技工学校学费?
- ·好奇一下:广州东华博瀚学校适合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