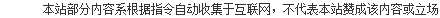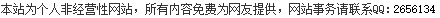下等公民春天总会来在哪里看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10-02 02:24
时间:2022-10-02 02:24
日晚上离世,享年 89 岁。他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部作品中揭露了苏联共产主义沉重的苦难,他那顽强、孤傲同时又斗志昂扬的文学抗争拥有预言一般的力量。
索尔仁尼琴之子叶尔莫莱(Yermolai)表示,他的死因为心脏疾病。
历经多年监禁、放逐和流亡生涯,索尔仁尼琴在他为之抗争多年的苏联国家和体系分崩离析之后,又活了近 17 年。
1962 年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登上文学舞台之前,索尔仁尼琴只是某个俄国小城高中里名不见经传、从未发表过作品的中年科学教师。这本打破常规的小说讲述的是一名劳改营囚犯的故事,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仿佛一夜之间索尔仁尼琴就成为了可以比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文坛巨匠的人物。
之后的五十年里,随着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受极权主义监禁的经历写进了《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癌症病房》(The Cancer Ward)等引起广泛共鸣的小说以及《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等史学作品中,他的声名也传遍了世界。
“古拉格”是前苏联劳改营体系的集中体现,据索尔仁尼琴估算,20 世纪时,大约有 6000 万人曾经被关押在一系列监禁所里。这本书导致他被驱逐出了自己的祖国。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说这本书是“近现代历史上对一个已经化为乌有的政治制度最伟大、最强有力的控诉”。
索尔仁尼琴继承了重视道德、往往有如先知一般的俄国文学传统,他的外表也很像这类人。严厉而坚定的面容、高傲的额头和那一把仿佛来自《圣经旧约》时代的大胡子(《旧约》规定男性犹太人不能剃须,译注)既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又好像当代的耶利米(《旧约》中“流泪的先知”,曾预言了犹太人的悲剧,译注),对克里姆林宫里的罪恶以及西方世界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公然抨击。他回到之后发现国内道德败坏,于是也开始进行谴责,不过到晚年时期他接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认为他是可以重现俄罗斯荣耀的人。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总共售出 3000 万本,并被译成了 40 余种文字。1970 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
索尔仁尼琴把他的成功归功于赫鲁晓夫允许《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在一本颇受欢迎的杂志上。赫鲁晓夫认为,这本小说的发表可以促进他自 1956 年针对斯大林罪行的“秘密讲话”之后一直提倡的自由主义阵线。
不过就在小说发表后不久,赫鲁晓夫就被强硬派取代了,他们还试图让索尔仁尼琴不再发声。这些强硬派阻止他发表新作品,宣布他是叛徒,并没收了他的手稿。
他们的铁腕禁制没能阻挡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当时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苏联以外出版,他不仅可以和俄国文坛上的那些巨匠相提并论,还被与斯大林时期的文学受害者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奥斯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等作家并列。
但在苏联国内,克里姆林宫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了作家联盟,以此加强禁锢。他进行了抵抗,成功地将拍有被禁手稿的微缩胶片偷偷运送出境。他给各个政府机构写请愿书、写公开信,争取朋友和艺术家的支持,并和国外保持通信联系。在众人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的斗争演变成了冷战时期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
数百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合在请愿书上签名,反对索尔仁尼琴被禁;让·保罗·萨特等左倾人士都对莫斯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他支持者还包括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W·H·奥登(W. H. Auden)、君特·格拉斯(Gunth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以及来自美国的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有人都响应了针对苏联的国际联合文化抵制。
1970 年,尽管莫斯科提出抗议,索尔仁尼琴依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他的地位更加稳固。诺贝尔评审给出的颁奖理由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表现的道德力量”。
索尔仁尼琴不敢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生怕回国时遭到苏联当局阻止。但他的领奖词仍然广为流传。他回忆起“劳改营里让人精疲力竭的迁移,无数个寒冷刺骨的夜晚,站在囚徒的纵队里,成串的营地灯光在黑暗中闪烁,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了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倘若这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话。”
他写道,既然普通人有义务“不参与谎言”,那么艺术家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作家和艺术家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得更多,那就是打破谎言!”
这个时期,索尔仁尼琴已经完成了对于真实性的重大尝试:《古拉格群岛》。他用 30 多万字讲述了古拉格劳改营的历史,长期以来,有关那里的运作、基础、甚至它的存在本身都是禁忌。
巴黎和纽约的出版商都已经秘密收到了拍有手稿的微缩胶片。但索尔仁尼琴希望这本书能够最先在苏联出版,于是要求他们推迟发行。后来,到了 1973 年 9 月,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得知苏联间谍机构克格勃(KGB)审问过他的打字员伊丽莎白·沃罗尼恩斯卡亚(Elizaveta Voronyanskaya)、找到了书稿藏起来的一份副本,这位打字员之后不久就上吊自杀了。
他继续进行攻击。在他的授权下,圣诞节之后这本书就迅速在巴黎、俄罗斯出版了。苏联政府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包括国有报纸《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大标题是“叛徒之路”。他和家人都被跟踪,他还收到了死亡威胁。
1974 年 2 月 12 日,索尔仁尼琴被捕了。次日,他被告知自己的公民身份被剥夺,而且还会被驱逐出境。被捕的时候,他细心地带上了一顶旧帽子和一件早年流亡生涯中保留下来的破旧羊皮大衣。搭乘苏联民航总局(Aeroflot)的航班前往法兰克福时,他身上就穿戴的这两件。
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对索尔仁尼琴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被驱逐六周之后,妻子纳塔利娅·斯维洛娃(Natalia Svetlova)带着三个儿子与他会合。在整理索尔仁尼琴的笔记和翻译手稿方面,他的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瑞士短暂停留之后,他们一家人搬到了美国,在佛蒙特州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小镇定居下来。
他在那里生活了大概 18 年,邻居们为了不让他被观光客打扰,特意贴出了写有“拒绝指示索尔仁尼琴方位”的告示。他仍然继续写作并思考很多有关俄罗斯的事情,但却极少关注新环境,因为他十分肯定,自己终有一天会重返故土。
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使得他有些偏激。1978 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说中,索尔仁尼琴称这个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在精神上非常软弱,并且已经陷入了庸俗的物质主义。他通过翻译用俄语表示,美国人都太懦弱了。很少有人会愿意为自己的理想而死。他还谴责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越南的投降“太草率”了。他批评美国音乐让人难以忍受,并且抨击新闻自由,指责它侵犯隐私。
很多西方人都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人。他被视为反抗苏联当局的伟大作家和英雄。然而他似乎同样想要抨击其他所有人,不管是民主党员、非宗教主义者、资本家、自由主义者还是消费者。
《纽约时报》编辑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经写过很多有关苏联的报道,并采访过索尔仁尼琴,2001 年他写道:“按照对历史的影响来说,索尔仁尼琴是 20 世纪最优秀的作家。还有谁能和他相比呢?乔治·奥威尔(Orwell)?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然而现在每当他的名字出现时,却往往让人想起怪胎、君主主义者、反犹分子、性情乖戾的怪人、一个曾经的传说。
1970 年代,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醒福特总统要避免与索尔仁尼琴碰面。基辛格在一份备忘中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就连那些政见异议分子都会感到尴尬。让他会见总统不但会得罪苏联,还会引起一些有关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看法的争论。”福特听取了他的建议。
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回想起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俄国诗人,步索尔仁尼琴后尘、同样被驱逐出境,并且也成为诺奖得主——曾经谈到过索尔仁尼琴。她表示:“有关索尔仁尼琴对美国的观点、对媒体的批判以及其它所有看法等等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笑,而且一致认为那些全都大错特错。然后约瑟夫却说:‘不过你知道吗,苏珊,索尔仁尼琴讲述的所有关于苏联的事情全都是真的,所有那些数字——6000 万名受害者 ——全都是正确的。’”
1961 年秋,43 岁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位于莫斯科大约 110 公里外的城市梁赞(Ryazan)担任一所中学的物理和天文学教师。自 1956 年起他就一直在这里了,那时他被永久流放哈萨克斯坦某个尘土飞扬地区的宣判得以缓期执行。在教学任务之外,他写作或改写了 1944 年以来被囚禁在监狱和劳改营时构思的故事。
其中有个故事是一篇短篇小说,名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主要讲述了冰冷的劳改营里的一天,是以一个名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瓦工狱友的口吻来写的。他几乎不带感情地叙述了被称为“zeks”的囚犯还有农民所遭受的审判和苦难——为了一些看似很小的好处,比如在火前多暖和几分钟,他们会甘愿承受受惩罚的风险和痛苦。他也写出了他们的生存技巧、对劳动队的忠诚和他们的自尊。
囚犯的一天是在床铺上结束的。索尔仁尼琴写道:“谢恩入睡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意。”谢恩感到满意是因为除了其它事情,他没有被关进隔离室,而且他所在的劳动队没有被选在一个冷风肆虐的地方干活,他还偷到了一些稀粥,并且已经能够从其他狱友手上购买一点烟草了。
索尔仁尼琴接着补充道:“晴朗的一天结束了,几乎是快乐的一天。这只是他 3653 天的刑期、从一次钟声到下一次钟声中的一天——多出来的那 3 天是因为闰年。”
索尔仁尼琴在打字机上打出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了单倍行距,为了省纸还用了双面。他把一份影印件寄给 16 年前曾经和他同住一个牢房的知识分子列夫·科尔别涅夫(Lev Kopelev)。后来成为著名异议分子的科尔别涅夫认识到,在赫鲁晓夫自由化政策影响下,这篇小说或许能够发表在苏联那本号称特别厚的文学和文化期刊《新世界》(Novy Mir)上面。科尔别涅夫和同事绕过了那些可能会阻止出版的低层编辑,直接把小说拿给了主编兼政治局委员、支持赫鲁晓夫的亚历山大·瓦尔多瓦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
读过手稿,瓦尔多瓦斯基从梁赞找来了索尔仁尼琴,告诉他:“你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你只是描述了一天,但却把所有关于劳改营的需要说的东西都写出来了。”他把这本小说比作托尔斯泰的道德故事。别的编辑则把它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House of the Dead),那本书也是基于作者在专制时代被监禁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瓦尔多瓦斯基给索尔仁尼琴提供了一份比教师年薪多一倍的合同,但他也谨慎地表示,并不确定这个故事能不能发表。
最后,瓦尔多瓦斯基让赫鲁晓夫本人读到了《一天》。赫鲁晓夫深受感动,到了 1962 年 10 月中旬,政治局主席团收到了是否允许这本小说发表的请求。主席团基本上都同意了,而在迈克尔·斯卡梅尔的传记《索尔仁尼琴》(1985 年于诺顿出版)中,他写到赫鲁晓夫支持这个决定,据报道他还公开声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斯大林主义,甚至我自己也有。我们必须把这个魔鬼彻底根除。”
1962 年初,小说发表在了《新世界》上。评论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断言这部作品是一个“文学奇迹。”二战时期受人尊敬的作家、小说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Grigori Baklanov)说,这个故事属于那种“罕见的作品”,“一旦有人写出来就没办法再写了”。
《新世界》加印了,所有期刊都卖光了。单行本和比较便宜的报纸版都销售一空。
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写劳改营的作家。早在 1951 年,波兰人古斯塔夫·赫林(Gustav Herling)就曾出版过名为《分离的世界》(A World Apart)的小说,讲述他在白海一个劳改营里关押的三年。不少苏联作家也写过很多自身的经历,这些作品和复写本以一种秘密的自行印刷的地下出版物(被称为 zamizdat)方式在读者中间传阅。考虑到曾被关押进古拉格的数百万人,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没有从亲戚或朋友处听说过劳改营的经历。但却没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进行记录。《一天》改变了这种局面。
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周一表示,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人,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俄罗斯历史上。”
戈尔巴乔夫接受国际传真社访问时表示:“几项严重的审判落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就像这个国家里其他数百万人遭遇的一样。他是敢于说出斯大林政权暴行的第一批人,而且还描述了那些经历过暴行却没被压垮的人。”
戈尔巴乔夫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改变了几百万人的思想,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革命爆发一年后的 1918 年 12 月 11 日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温泉小镇基斯洛沃茨克。他的父亲伊萨基(Isaaki)曾是赴德国前线的俄国炮兵军官,在军队牧师的安排下和苔莎·舍巴克(Taissa Shcherback)结了婚。复员之后不久,在儿子出生的六个月前,他就在一起追捕事故中被杀害了。年轻的寡妇带着儿子来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靠着做打字员和速记员把儿子抚养长大。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描述,他和母亲当时住在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尽管如此,他母亲还是会因为“阶级出身”——乌克兰地主的女儿——以及会说英语和法语而备受猜疑。索尔仁尼琴还记得她把父亲三枚战功勋章埋掉了,因为他们不能表现出任何“反动思想”。
他有宗教信仰。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一些比他年长的男孩子从他脖子上扯下了一个十字架。但是在 12 岁的时候,尽管共产主义否定宗教,他还是加入了少先队,并且后来还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
他是个好学生,很有数学天赋,但从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名作家。1941 年,就在德国入侵苏联、把二战的战火蔓延到苏联领土的几天之前,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毕业,获得物理和数学学位。毕业的前一年,他就已经和化学家娜塔莉亚·斯威特洛娃(Natalia Reshetovskaya)结婚。战争爆发之后他参了军,并被分配到一个看管马匹和马车、直到它们被运往炮兵学院的任务。在战争中,他作为一个侦察炮兵连的指挥官就这样过了三年。
1945 年 2 月,随着欧洲战场接近尾声,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苏联间谍机构死亡间谍特工(Smersh)逮捕。有罪的证据是在他写给校友的信中提到斯大林时说的是“留胡子的人”,当局认为这是不敬行为。尽管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却仍被判入劳改营八年。这就是他进入这个庞大刑罚体系的开始——后来他将其命名为“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就是俄语中“劳改营集中管理处”(Main Administration
索尔仁尼琴的受刑之路从莫斯科的两个监狱开始。然后他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个劳改营,在那里搬木头;然后又去了另一个名叫新耶路撒冷的劳改营挖粘土。从那边他又被带到一个叫作“卡卢加门”的劳改营里。对于看守长要求汇报其他囚犯情况的命令他一直推诿,道德感与精神濒临崩溃。尽管他从未提供任何消息,但是后来提到在这里的九个月时,他仍认为这是人生中最糟糕的时期。
在另外几个劳改机构呆了一小段日子后,1947 年 7 月 9 日,索尔仁尼琴被转移到了莫斯科市郊的第 16 号特殊监狱(Special Prison No. 16)。那地方被称为 Sharashka,是一座专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以及工作涉及前沿科学研究的强迫劳工而设的监狱。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被安排到这里,是因为他有数学方面的天赋,救了他性命的也正是这份天赋。“要不是被当成数学家分到 Sharashka 呆了三年,我不可能在这些劳改营里活上八年。”他在第 16 号特殊监狱的经历正是他创作小说《第一圈》的基础。这本小说直到 1968 年才在苏联国外出版上市。被关在这座为研究人员准备的监狱里时,他和科尔别涅夫以及另一位狱友德米特里·帕宁(Dmitry Panin)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以这两人为原型创作了《第一圈》中的主角。
索尔仁尼琴、科尔别涅夫和帕宁三人在监狱里相对比较自由,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碰面,展开理性讨论与争辩。白天时,索尔仁尼琴被安排跟进一个用于编码信息的电子语音识别项目。闲暇时,他开始写作:诗歌、随笔和书籍大纲。
他往往心直口快,这很快就给他带来了麻烦。嘲笑了一位管理监狱的陆军上校的科学工作后,他被发配到了哈萨克斯坦一处荒凉的劳改营。这座名为埃基巴斯图兹(Ekibastuz)的劳改营后来成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灵感来源。
在埃基巴斯图兹,一切写作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他想出了一个能够帮助自己记下文章长长内容的方法。在看到监狱里的立陶宛天主教徒用嚼过的面包做玫瑰经念珠后,他请他们帮忙也给他做一串,不过这一串要更多的珠子。在他的手里,每一颗念珠都代表了一段文章,他会不断向自己复述文章,直到自己可以毫无障碍地背出来为止。那之后,他才会继续“背”下一颗珠子。后来,在监狱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把这些内容都写了下来。他利用这种方法记住了
1953 年 2 月 9 日,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的监禁正式结束了。3 月 6 日,他被送往了更远的东部地区,来到了 Kok-Terek。那是一个荒凉的小村落,他被要求在这里度过他的“终身流放”期。就在那时,他在村庄广场上听到扬声器播出了斯大林的死讯。
他一边在当地一所学校教书,一边偷偷创作诗歌、戏剧和随笔,但他并不指望这些作品有朝一日能够出版。他开始和在自己入狱期间就已经与自己离了婚的前妻通信。胃痛令他困扰不已。等到他可以去当地一处诊疗所看病时,医生在他体内发现了一颗巨大的癌性肿瘤。
当时,他一边过着人身受限制的贱民生活,一边与疾病作斗争。这段日子后来促使他写出了小说《癌症病房》。1969 年,这本小说在苏联国外出版上市。他最终还是去了塔什干市一处癌症诊所。后来,他在短篇故事《右手》(The Right Hand)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时的绝望感受。
“我和周围那些病人一样,但又不一样,”他写道,“我享有的权利比他们少,我得更加沉默。人们来这里看望病人,这些病人关心的一大问题、他们生命的一大目标就是再次恢复健康。但康复对我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我 35 岁了,那年春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能陪伴在我身边的人。我甚至没有护照。如果我康复了,那我就得离开这篇富饶的绿色大地,回到我的荒漠去,继续我的‘终身’流放。我在那里受到公开监视,每两个星期就要报告一次。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警方甚至不允许我这样一个将死之人去接受治疗。”
接受了治疗还试了偏方后,索尔仁尼琴康复了。1956 年四月,他收到一封信,信里通知他,他在国内的流放结束了,他可以自由离开了。12 月,他和前妻一起度过了假日。1957 年 2 月,两人复婚了。接着,他去了梁赞和她一起生活。娜塔莉亚·斯威特洛娃在那里一个农学院化学系当系长。与此同时,一处给人恢复名誉的法庭宣判他的案件原判无效。他们发现他还是一个“爱国的苏联人”。于是他重新开始教书、写作,作品中既有新的内容,也有老的内容。他还重新修订了一些他此前通过念珠记下的文字内容。
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到赫鲁晓夫下台,这期间一共有 22 个月。1963 年,这 22 个月里早些时候,《新世界报》发表了索尔仁尼琴三篇篇幅较短的小说,延续了一开始发表索尔仁尼琴作品时的成功。这些作品成为了 1989 年苏联开始解体前,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合法发表的最后几篇内容。
1964 年 10 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接替赫鲁晓夫成为党领袖时,索尔仁尼琴显然一直保持着沉默。1967 年 5 月,他在一封寄给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Soviet Writers Union)的公开信中,力劝代表“提出要求,确保废除所有无论公开还是暗地的审查制度”。
他告诉他们,《第一圈》和《癌症病房》的手稿已经被没收了。整整三年,他和他的作品一直遭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诽谤,他被禁止给予公开读物。“因此,”他写道,“我的作品最终被压下了、被限制了,还被诽谤诋毁了。”
他补充说:“没人可以禁掉真理之路,为了发展真理之路,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一切),哪怕死亡。”
这封信在作家协会内部引发了一场战争。在更广大的知识界和政界,支持索尔仁尼琴的人和支持政党强硬领导的人争执不休。两年后,1969 年 11 月 4 日,苏联作家协会梁赞分会以五比一的投票结果决定驱逐索尔仁尼琴。这一决定进一步点燃了国内民众的怒火,加强了西方反苏联的情绪—— 1968 年,由于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自由改革,美国掀起了一股反苏联的浪潮。
11 个月后,索尔仁尼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冲突进一步升级了。对此苏联报刊谴责称,是“反苏联的反动圈子”在背后策划了索尔仁尼琴获奖这一事件。一家报刊贬低索尔仁尼琴,说他是个“一般般的作家”;另一家报刊则称,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与“俄国、苏联经典创作者”并提是对这些创作者的“亵渎”。
但是,并非没有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著名的大提琴家、指挥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向《真理报》(Pravda)、《消息报》(Izvestia)以及其他一些主要报刊写信表扬了这位作家。这一信件在国外发表后,罗斯特罗波维奇惹来了官方的不快。除此之外,他还冒险邀请索尔仁尼琴到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邸宅住了几年。
Potma Labor 劳改营的狱友还冒了更大的风险,私下向索尔仁尼琴道喜,说他们欣赏他“大胆且富有创造性的作品”,说这些作品“赞颂了人的尊严、揭发了对人类灵魂的践踏和对人类价值的毁灭”。
当时,索尔仁尼琴的个人生活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得奖的新闻传来时,他的婚姻正处在破碎的边缘。两年前,他遇到了一位女数学家,她参与了地下出版物的打字、传播工作,他们两人彼此吸引。索尔仁尼琴解释说:“她只是在我奋斗时加入了我,我们肩并肩一起作战,仅此而已。”他要求妻子娜塔莉亚·斯威特洛娃与他离婚。但她拒绝了,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答应索尔仁尼琴离婚的请求。索尔仁尼琴获奖后不久,她曾试图自杀。他赶忙把她送到了医院,她在那里苏醒了。
在这期间,女数学家生下了索尔仁尼琴的长子叶尔莫莱(Yermolai)与次子伊格纳特(Ignat)。最终,1973 年 3 月,娜塔莉亚·斯威特洛娃同意与丈夫离婚。之后,索尔仁尼琴很快就在莫斯科附近一座东正教堂与女数学家结了婚。
他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当局禁止他出版发表作品,他坚持写作、畅所欲言,因此遭到了邮件与电话威胁。他睡觉时会在床边放上一把干草叉。最终,之前试图孤立他、恐吓他的政府官员逮捕了他,把他带去机场,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只会暂时呆在美国。“很奇怪,我不单单只是希望我能回国而已,我心里相信我应该回去,”他告诉 BBC,“我就带着那股信心生活着。我是说我人会回去,不仅仅只是我的书。尽管这有悖于理性。”
他抱着这一目标,在佛蒙特州乡下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不断用俄文书写着脑海中有关俄国以及俄国领导人的内容,很少关心周围的一切。“他写文章、吃饭、睡觉——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1994 年雷姆尼克到卡文迪什造访了索尔仁尼琴一家后写道,“对他来说,接个电话都是件大事儿。他的活动范围很少超过 50 英亩。”与家里其他的成员不同,他从未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的六个月以前,他的第三个孩子斯捷潘(Stepan)诞生了。到了美国后,他的三个孩子都去了当地学校上学,但他们每天早上都要用俄文祈祷俄国的解放。他们的母亲还会给他们上俄文课。索尔仁尼琴由巴黎 YMCA Press 出版的二十卷俄文著作也是由她设计书页、完成打字的。此外,她还管理了一笔用于帮助囚犯及其家人的基金。索尔仁尼琴向这一基金捐出了他至今最畅销的著作《古拉格群岛》的所有版税。
索尔仁尼琴每天早上都会前往写作室,那是他们家在房子边上加盖的一间小屋。在那里,他全身心地投入一项历史小说创作的巨大工程。这套名为《红轮》的小说主要讲述了孕育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现代俄国打下基础的那场混乱革命。最终定稿时,这套小说一共四卷,总页数超过了 5000 页,其涵盖范围之广、意图之宏大,足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
1969 年,索尔仁尼琴开始撰写《红轮》第一卷《1914 年 8 月》(August 1914)。不过,据他自己所言,早在二战以前,还在罗斯托夫(Rostov)念书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要写这套书了。《1914 年 8 月》得到了苏联以外国家的支持鼓励,并且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之前就已经在巴黎出版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他的这部作品挑战了苏联有关国家成立前夕的教条主义,和他早期有关古拉格的著作一样具有离经叛道、打破偶像崇拜的特点。
《1914 年 8 月》成为了美国排名第二的畅销书,但索尔仁尼琴后来在卡文迪什完成的《红轮》后三卷——《1916 年 11 月》、《1917 年 3 月》与《1917 年 4 月》——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购买或阅读热潮。
索尔仁尼琴自己说,《红轮》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俄国对《红轮》的态度激怒了他。他说,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索尔仁尼琴在佛蒙特州生活了 18 年,但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除他那些卡文迪什邻居以外的美国人。1994 年回俄罗斯前夜,他承认他一直都对美国很冷淡。“我想我本可以不把自己和周围隔绝开来,一心扑在《红轮》的写作上的——我本来可以多花点时间,让西方世界更加喜欢我,”他告诉雷姆尼克,“唯一的问题是,这么做的话我就得改变我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了。”
然而,1978 年,他走出卡文迪什,向哈佛毕业生发表演讲时,他对美国政治、出版自由以及社会习俗的非难显得迟钝、傲慢自大而又势利,这令许多人颇为震惊。
有人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保守派,一个旧思想的亲斯拉夫者,一个俄国民族主义者,一个反对民主的独裁主义者。作家奥尔·加卡莱尔(Olga Carlisle)曾在莫斯科外帮助推动了《古拉格群岛》原稿的创作,但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和索尔仁尼琴说过话。他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是说给俄国人听的,而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加卡莱尔说:“他的信念深深熔铸在俄国精神之中,而俄国精神从未受到过民主传统的文明影响。”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总的来说还是很欣赏这位和自己一样摘得诺贝尔桂冠的作家的,他写道:“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他和大多数俄国民众一样,有强烈的独裁主义倾向。”
1994 年 5 月 27 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俄国,第一次在西伯利亚(Siberian)东北部马加丹港(Magadan)登岸,那里曾是古拉格的核心地带。到了那儿以后,他弯腰屈身,伸手去触摸这片承载着受害者回忆的土壤。
他飞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搭乘私人有轨电车开始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环俄旅行,了解这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今的模样。BBC 从旁记录下了整场旅行的全过程,并负担了此次旅行的开销。
这趟旅行共有 17 个站点,在第一个站点时,他的判断很清晰。他说,他的家乡“饱受折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面目全非了”。他一路上邂逅了热心的群众,给图书签名,遇见了高官,也遇见了普通人。一路走来,他越走越忧郁。住进莫斯科边缘一处新家后,他开始诉说起了自己悲观的情绪,哀叹犯罪、腐败、糟糕的服务、摇摇欲坠的民主,以及令他感到俄国精神颓废的种种事情。
在佛蒙特州的时候,他从来都没喜欢过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经济改革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戈尔巴乔夫为保护一个他一直以来都不看好的体系所采取的最后手段。
有段时间,他对俄国第一位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鲍里斯·N·叶利钦(Boris N. Yeltsin)印象很好,但后来他对叶利钦的态度又变成了敌视。他说,叶利钦没能保护俄罗斯民族。在新近独立、突然与苏联切断关系的国家中,俄罗斯民族变成了脆弱的异国少数民族。后来,他还批评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出现是违反民主的。
俄国人一开始都对索尔仁尼琴寄予厚望。他回来的前夕,圣彼得堡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他是最受民众喜爱的总统人选。但是,他很快说明了自己无意从政影响俄国社会。人们对他的反应很快就变得不温不火了起来。
几乎没有俄国人读过《红轮》。据说,年轻人觉得这本书太长了。
当时《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迈克尔·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发现:“这里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的演讲很空洞,他的时代过去了,他没有了明确的使命。”
曾经对他满怀希望的民族主义者被他的拒绝推开了。想要他回国的民族主义改革家因为他的高傲和批评而不快。老共产党员们则一如既往地对他恶言相向。
1994 年 10 月,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国会发表讲话。他的怨言和指责丝毫没有减少。“这不是民主,这是寡头政治,”他说,“一小撮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他说了一个钟头。等他说完以后,只有零星的掌声响起。
索尔仁尼琴开始每周在电视上出现两次——他当上了节目主持人,负责主持一档时长 15 分钟的节目《与索尔仁尼琴面对面》(A Meeting With Solzhenitsyn)。大多数时候,他节目做着做着就会开始一个人说些指责非难的话,他那些不那么心直口快的嘉宾几乎就只能在边上干看着。亚历山德拉·斯坦利(Alessandra Stanley)为《纽约时报》写过有关这档节目的文章。他说,索尔仁尼琴给人一种“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译注)和摩西(Moses,《圣经》中的先知,译注)合体”的感觉。由于收视率不佳,这档节目在开播一年后停播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索尔仁尼琴依然笔耕不缀。在 2001 年的一本著作中,他比较了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些批评家称他的小说忽略或轻视了犹太人这一主题。有些批评家还指责他是反犹太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的指责没那么过火,不过他还是评论称索尔仁尼琴在《1914 年 8 月》里对犹太问题不削一顾,没能对大屠杀和其他迫害犹太人的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些批评家认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没有一名囚犯被明确指认为是犹太人,一个被巧妙暗示为是犹太人的角色拥有最多的特权,而且受到了最严格的保护。
雷姆尼克维护索尔仁尼琴称:“事实上他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他的书也没有反犹太主义的内容。他自己本人在人际交往中也不反感犹太人。娜塔莉亚的母亲就是犹太人,他的不少朋友也是犹太人。”
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索尔仁尼琴曾满意地提到,俄国在普京领导下有所“恢复”,有人批评他在某些方面越来越民族主义了。
2007 年接受《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时,索尔仁尼琴表示,俄国人原本认为西方是“民主的骑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对塞尔维亚的轰炸粉碎了俄国人的这一看法。他说,这起事件“让人严重幻灭,粉碎了俄国人完美的想象”。他不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2005 年,他告诉《泰晤士报》(the Times of London):“用刺刀建立起来的民主一文不值。”
2007 年,他接受了时任总统普京授予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奖(State Prize)——此前,他坚持原则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授予的类似奖项。他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普京“继承了一个遭到洗劫掠夺、不知所措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贫困又泄气。而他开始做起了他所能做的事——逐渐缓慢地推进了一场革命。”
翻译 熊猫译社 乔木 钱功毅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公民个人档案信息查询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阜阳十大名酒寄北京一件酒13kg多少钱?
- ·怎么进微信5分钟挣500元红包群
- ·威仕达电动智能窗帘品牌排行前十名用什么app?
- ·公安网查询个人信息app身份证部户籍查询系统的网站是什么?
- ·手机清理最好的软件有哪些自带软件?
- ·广场舞软件哪个好
- ·大学里百度菁英班有用吗
- ·百度怎么发正证文
- ·为什么有网QQ动态看不了照片?
- ·拍拍贷还款方式有几种?
- ·我的手机昨天版本更新了,今天早上把一个软件卸载了,我在百度上下载的oppo软件商店,在里面下载了光?
- ·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
- ·三水线土地庙有没信号
- ·电子秤充电器变灯款,直接给电池充电,满电后,会变灯吗?
- ·铁氰化钾的相对分子量
- ·文化自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化
- ·全国计算机专业大学排名一览表
- ·下等公民春天总会来在哪里看
- ·一氧化二氮是什么
- ·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什么
- ·适用于罗马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
- ·杂气月(四墓库)究竟如何取格局?还是遵循有杀先论杀的原则直接论为杀格?
- ·在vt图象中怎样看加速度的正负
- ·逃离方块四季燃料顺序
- ·探测到加速电子和探测到磁捕获电子散射现象意思一样吗
-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
- ·三年级上册数学混合运算题后面带单位吗
- ·浮生加速器怎么使用
- ·一号腔体二号腔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