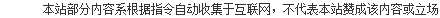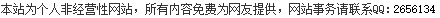三星阿兰德·德·卡瓦略厉害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09-11 11:25
时间:2017-09-11 11:25
通俗哲学家阿兰·德·波顿:我为什么开始搞新闻
Stephen Heyman
[摘要]“我们的想法是,思想清高的人们在象牙塔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德·波顿在伦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走出来到街上,到喧嚣的集市上向普通人阐述他们的观点。”出生于瑞士、在伦敦定居的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致力于把哲学和文学中的伟大思想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他认为艺术可以代替心理治疗,而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则可以当做励志手册。几年前,他把自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困了一个星期,来思考机场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德·波顿先生最近的生活调查《新闻:使用者手册》(The News:A User’s Manual)的主题是新闻。用德·波顿的话来说,新闻是一股无处不在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信息,但却很少能带给我们启迪。阿兰·德波顿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德·波顿近著出版的同时,他策划的“哲学家邮报”(The Philosophers’ Mail)网站也上线了。“哲学家邮报”是一个新闻网站,由“人生学校”——一个位于伦敦的通俗哲学学院出资。该学院开设一些诸如“如何独处”这样的讲座。“哲学家邮报”网站基于英国小报《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网站的模式。但是却致力探究名人八卦和世界时事背后的哲学涵义。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霍尔姆斯(Katie Holmes)的狗仔照片会配有叔本华关于爱之徒劳的语录。对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和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灵魂”的假想采访其实是关于坚忍克己,持之以恒品德的讨论。一篇关于乌克兰警民冲突的报道变成了关于冷漠的探讨——该报道的标题是“基辅在烈焰中燃烧,而我根本不在乎”。网站的主编是《每日邮报》前执行主编理查德·艾迪斯(Richard Addis)。网站的内容并没有署名,是由与“人生学校”的哲学学者们执笔,供稿人包括戴蒙·杨(Damon Young)和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我们的想法是,思想清高的人们在象牙塔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德·波顿在伦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走出来到街上,到喧嚣的集市上向普通人阐述他们的观点。”以下是关于德·波顿新项目的采访,内容经过编辑。问:你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需要一个由哲学家们执笔的新闻网站?答:六个月前,在和一些哲学家朋友聚会时,有人告诉我,现当代哲学家的著作平均下来每人只能卖出去300本。然后又有人提到《每日邮报》网站每天有四千万的点击量,是世界上点击量最高的英语新闻网站。于是在一个失眠的晚上,我突然就想到:如果照搬《每日邮报》——报道些谋杀,自杀,乱伦什么的——但是却给图片配上不同的解说。可以用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或是一宗在拖车里发生的双重谋杀案作开头,然后讲点别的有趣的东西。问:你的观点是,普通新闻在本质上是误导性的,而这种误导性跟事实和准确性无关。答:我认为新闻太注重搜集信息,而忽视了它另一项必需的任务,那就是要使人们觉得信息事关于己。新闻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谬论,有些地方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却被弄得模棱两可。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新闻”。世界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事:比如300人不久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遇难身亡。人们读到这则新闻会耸耸肩,说:“这关我什么事。”然后去睡觉。我们对成百人的死亡视而不见或是无动于衷,这多么奇怪啊。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是没有人性的恶魔吗?并不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会去关心以前并不知道存在的一个人的逝去?新闻聚焦灾难本身,却没有给读者提供了解灾难发生地日常状态的途径。人们需要了解受灾者的生活,然后才会关心他们遇到的困难。问:在聚合时代,难道新闻不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吗?人们最终不是读到了和他们品味和需求相应的新闻吗?答:有一种观点是读者品味低劣。他们要看热门点击。所以他们会去《每日邮报》网站看死亡事件和各种丑闻,而不会去读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道。这对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挑战。在过去能依靠权威性引导读者的严肃新闻媒体现在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反阶层的时代。你不能说:“我们是BBC,你必须听我们的。”人们会说:“不,我觉得现在《Vice》(专注艺术文化和新闻的新媒体杂志,在Youtube上开有频道——译注)更有趣些。”问:许多新闻组织都非常重视新闻的中立性。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你认为中立性的重要被夸大了吗?答:有一种观点是,倾向性是“糟糕”的新闻机构才会具有的特征,比如福克斯电视新闻网(Fox)。但是区分新闻机构好坏的标准应该看它的倾向性是好还是坏。有倾向性的反面是对事实中立地呈现。但是跟我们文明有关的许多宏大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持有看法,有些问题或许可以从某种观点中获益。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观点,我们应该成熟理性,不过于纠结。BBC在这一点上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们会有一个关于割礼的讨论。一些人反对,一些人赞成。你会觉得:伙计们,快点吧!你们到底能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见解?问:“哲学家邮报”没有评论功能。在一篇文章中,网站解释说人们大多都是理性的,但是网上评论却使他们显得“无情,执迷,不宽仁——离疯狂差不了多少”。答:读评论就好像看某人的日记。有时人们在极端情绪控制下会在日记里写道:“我恨每个人,我想自杀,万事无望。”然后他们大哭一场,就忘掉了日记这码事。一定不要去读那本日记,因为它并不能告诉你作者的真实情况。它反映的是作者在某种情绪下的状态。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互相关爱,互相信任,和陌生人说话也不会心存顾忌的社会里,那我们就不该读这些东西。读了的话你就再也不敢出门了。(英文原文载于《纽约时报》网站日,原标题:News from the School of Life;作者:Stephen Heyman;王晓琳/译)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寄送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法意首发|阿兰·德毕努瓦:帝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的图书馆
法意首发|阿兰·德毕努瓦:帝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法意 | 导言帝国是什么?其首要之处不是领土,而在本质上是一种理念或原则。政治秩序由此决定,而不是由物质因素或由对地理区域的占有来决定的。“帝国”与“民族”概念有何差异,它与我们当下所称的“大国”又有何不同,这一理念对当代国家间的政治实践又有何参照价值?请看法意今日推送的文章《帝国的理念》。本文选自《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七辑)》,小标题为译者所加。秉持着一贯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本辑关注帝国与国际法问题,共有12篇文章,法意平台会陆续推出,敬请关注。作者简介阿兰·德毕努瓦,Alain de Benoist,生于1943年,法国学者,哲学家。新右派(Nouvelle Droite)创始人,法国民族主义智库GRECE负责人,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平等主义的批评者。翻译:孙璐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对:孔元,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帝国的历史沿革两种重大的政体模型、政治统一体的模型在欧洲这个地方阐释、发展并碰撞:君主制之后的民族国家 ,以及帝国。西方拉丁世界最后一个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于475年被废黜。只有东方帝国留存下来。但在西方帝国瓦解之后,一种新的统一意识似乎已经兴起。795年,教皇利奥三世不再以康斯坦丁皇帝的任期,而是开始以罗马勋贵、法兰克王查理的任期颁布通谕。五年后在罗马,800年的耶诞节那天,利奥三世将帝冠戴在查理曼的头上。这是对帝国的首次改造,它遵循了转让(帝国的转让,transratio imperii)理论,即查理曼所复兴的帝国是对罗马帝国的一种延续,由此给受先知大卫启发发展出来的神学推断画上句号。因为他曾预言,第四帝国,即继承了巴比伦、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罗马帝国,终结之时便是世界末日。 同时,这一对帝国的改造也突破了奥古斯丁观念中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与上帝之城(civitas Dei)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种理解下,一个基督教帝国只是一种幻觉。但事实上,利奥三世却有一个新的战略——一个基督教帝国,并让其皇帝充当上帝之城的守护者。皇帝的权力源于教皇,他将教皇的精神权力复制到世俗领域。当然,所有围绕授职权(investitures)的争吵都将从这个难以解释的表述中生发出来,因为该讲法在使皇帝处于精神秩序中的从属地位的同时,又让他成为世俗等级制度的首脑,他为此很快就主张其神圣特性。。凡尔登条约(843年)为查理曼的三个孙子(洛塔尔一世,德意志人路德维希和秃头查理)瓜分其帝国戳上了封印。之后,萨克森王亨利一世在919年加冕为帝,由此帝国开始变成德意志的。在加洛林王朝瓦解之后,962年它随同奥托家族和法兰克人一道,在欧洲中心位置得以恢复,日耳曼国王奥托一世成为受益者。它作为欧洲主要的政治力量一直保持到十三世纪中叶,并正式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1442年后,又将“德意志民族”加入其名称。△ 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徽章这里不追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仅仅指出纵观其历史,它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复合体:古代,基督教和德意志身份。从历史上看,帝国理念的解体始于文艺复兴时首批民族国家的出现。当然,1525年帕维亚大捷,帝国力量战胜了弗朗西斯二世的军队 似乎逆转了这一趋势。那时,这次事件被赋予重大意义,还导致意大利吉伯林派(Ghibellinnism)的复兴。然而,查理五世之后,皇帝头衔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菲利普,帝国再次沦为地方事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之后,它越来越显得没有威严,越来越被视为领土国家的联盟。帝国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衰落 。日,拿破仑以摧毁帝国的残余部分完成了大革命。弗朗茨二世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灭亡。2帝国的概念与民族概念的比较鉴于人们对帝国概念各种相互矛盾的使用,乍一看这一概念很难理解。在他的词典中,Littre满足于一种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帝国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这太简洁了。与城邦或民族国家一样,帝国是一种政治统一体;与君主制或共和制不同,帝国不是一种政府形式。这意味着,帝国先验地与不同的政府形式兼容。魏玛宪法第一条便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共和国。”即使是在1978年,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德意志帝国仍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理解帝国实质的最好途径是将其与民族或民族国家进行比较——后者代表着民族性形成过程的终点,法国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当下的意义上,民族的出现是一个现代现象。在这方面,Colette Beaune 和Bernard Guene两人将民族的产生放在很早历史时期的观点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念犯了时代错误,它混淆了“国王的”和“民族的”,混淆了民族性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民族性的形成对应于一种归属感的诞生,这种归属感产生于对金雀花王朝的战争过程中,人们超越了简单的出生地意识(natal horizon)——这种感觉在百年战争期间得到强化。不应忘记的是,在中世纪,“nation”这个词(来自于“出生”)仅仅指称种族含义——索邦的nations仅指操着不同语言的学生群体。同样的道理,“国家”(country)这个只在16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Dolet, Ronsard, Du Bellay)那里出现的词,最初是指中世纪的“家乡”概念。当不仅仅与自己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时,“爱国主义”是指对领主的忠诚或者对国王的人身的效忠。即使是“法兰西”这个词也出现的相对较晚。从查理三世(糊涂王)开始,法国国王的称谓是“法兰克王”(Rex Francorum)。而“法兰西国王”(Rex Franciae)的表述仅出现于13世纪初的腓力·奥古斯特时期,在米雷(Muret)战胜图卢兹伯爵(Count of Toulouse)之后,结果是法国吞并了讲奥克语(langue d’oc)的国家,并迫害卡特里派教徒。民族的观念完全构建起来仅仅是18世纪的事情,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起初,它指的是一种与绝对君主制相对立的主权概念。这个概念把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持同样想法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认为不再是君主而是“民族”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性。最后,它是指一个抽象场域,在其中人民可以彰显,而个体可以转化为公民。首先,民族是主权者人民,在所有情况下,人民仅委托给国王适用法律的权力,而法律来自公意;其次,民族是指那些认同国家的权威,居住在同一领土之内并认同彼此作为同一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的人民;最后,民族是政治统一体本身。这也是为什么高举贵族原则的反革命传统最初避免对民族概念进行评价。相反,1789年《人权宣言》第三条宣布“所有主权的原则本质上属于民族。”Bertrand de Jouvenel甚至写道:“事后看来,革命运动似乎早已把建立民族膜拜作为其目标。” △ 1789年《人权宣言》第三条宣布“所有主权的原则本质上属于民族。” 帝国与民族的区别是什么?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帝国首要不是领土,而在本质上是一种理念或原则。政治秩序由此决定,而不是由物质因素或由对地理区域的占有来决定的。它决定于一种精神或法学的理念。在这方面,认为帝国区别于民族主要在于规模大小——即帝国是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国家”——是一个严重错误。当然,帝国涵盖了广大地区。但重要的是,皇帝掌有权力凭借的是他体现了某种高于简单的占有的东西。作为“世界之主”(dominus mundi),他对诸侯和国王们行使宗主权,也就是说,他统治主权者们,而不是统治领土,他代表着一种超越他所统治的共同体的权力。Julius Evola写道:“帝国不应当与构成它的王国和民族相混淆,因为它有质的不同,并在原则上先于并高于它们每一个。” 在它表达一个超民族-领土霸权体系之前,“按照旧的罗马观念,治权(imperium)是指纯粹的命令的权力,是权威(auctoritas)的具有某种神秘性的力量。”在中世纪时,通行的区分恰恰是在权威(auctoritas,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与权力(potestas,单纯的由法律手段行使的政治公权力)。在中世纪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不同是区分帝国权威和皇帝对于特定人民的主权权威的基础。例如,查理曼部分是皇帝,部分是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王。从那时起,效忠于皇帝不再是服从于一种民族或者某个特定国家。同理,在奥匈帝国,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构成了“人民和被取代了的爱国主义之间的法西斯主义链条”(Jean Branger);它压倒了一种民族性的关系。帝国原则的这一精神特质直接挑起了关于授职权的著名争论,教皇的拥护者与皇帝的拥护者为此相互斗了几个世纪之久。由于缺乏军事性内容,帝国的概念最初在中世纪德意志世界获得了很强的神学投射,在那里我们能看到对帝国统治权这一罗马观念的基督教再解释。考虑到他们自己便是普遍的神圣历史的执行者,皇帝们据此推论:帝国,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Sacrum imperium),必须构建自己相对于教皇的自主权力。这正是归尔甫派(Guelphs)和吉柏林派(Ghibellines)争论的原因。皇帝的追随者们——吉柏林派——反对教皇的主张,他们从治权(imperium)与圣职(sacerdotium)的古老区分中找到了支持,即将其看作是均由上帝建立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领域。这种解释是对古罗马时期皇帝与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延伸,每一方在各自秩序中高于另一方。吉柏林派的观点并不是要让精神权威服从于世俗权力,而是针对教会的排他性主张,要求皇帝的权力具有同等的精神权威性。所以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来说,皇帝是一个半神的中介并由他将上帝的正义播撒大地。这个新讲法,使得皇帝成为法律的本源并赋予他“地上的活法律”(lex animata in terris)的特征,并概述了吉柏林派的主张:和教皇一样,皇帝必须被认定为在性质和特征上具有神圣性的机构。Evola强调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展现的是两个伟大的尊位之间的对抗,两者都主张精神维度……在其最深层面上,吉柏林派认为在其地上的生命中(表现为规训,战斗和服侍),个体可以在帝国之下,根据帝国被授予的“超自然”制度的特征,通过行动超越自身” △ 帝国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必须构建自己相对于教皇的自主权力,这正是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争论的原因。图为描写两派对峙的画作,由Ottavio Baussano所绘从这开始,帝国经由数世纪的衰落与帝国原则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衰落是一致的,相应地,与帝国向着一种纯粹的领土意义上的运动也是一致的。当德意志罗马帝国试图将意大利和德意志连成一块特权领地时,它已经变了。但丁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他来说,帝国在精神意义上既不是德意志的,也不是意大利的,而是“罗马的”,即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换言之,帝国如将自身转型为一个“伟大民族”,那它必然崩溃,因为就赋予它生命力的原则而言,如果不超越其忠诚和特殊利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承担并行使一种更高的统治功能。Evola断言:“帝国在真正意义上,只能由一种精神热情赋予的生命力而存在,如果缺失这种激情,便只有一种由暴力锻造的产物——帝国主义——一种没有灵魂的简单的机械的上层建筑。” 就其本身而言,民族在这种主张中找到其源头,即王国必须通过与领土而不是与原则建立关联来给予自身帝国性特权。其开端可以定位到随凡尔登条约而来的加洛林帝国的解体。从那时起法兰西和德意志,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们,开启了不同的命运。后者仍然留在帝国传统中,而法兰克王国(Regnum Francorum)从日耳曼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以君主制国家作为中介向着近代民族国家缓慢进化。卡罗林王朝终结于10世纪:911年在德意志,987年在法兰西。于格·卡佩(Hugues Capet)987年当选为首位不懂法兰克语的国王。他还是首位将自己明确置于帝国传统之外的主权者,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借他的口说:“我是恶性膨胀的屋顶,我的阴影将所有基督教土地带入黑暗!”在13和14世纪,法兰西王国通过腓力·奥古斯特(布汶Bouvines,1214)和美男子腓力(阿纳尼 Agnani,1303)在反对帝国的过程中构建起来。早在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就宣布“众所周知,在世俗领域中法兰西国王不认可任何在他之上的权威。”就如同特洛伊传说被工具化一样,一个塑造自己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工程,允许各民族王国,借助主权原则和只认可基于自身利益的法律的权利来对抗帝国。正如卡尔·施密特所强调的,法学家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在13世纪中叶,正是这些人提出新的学说,据此 “法兰西国王,在世俗领域中无人在其之上,免于帝国的义务并被视为自己王国的首领(princeps in regno suo)” 该教义于14和15世纪在皮埃尔·杜波依斯(Pierre Dubois)和纪尧姆·德·诺加雷特(Guillaume de Nogaret)那里继续发展。国王通过宣称自身是“自己王国的皇帝”(rex imperator in regno suo),以其领土主权对抗帝国的精神主权——他的纯粹的世俗权力对抗帝国的精神权力。同时,借助“王家法院(cas royal)”这一机构,法学家站在中央集权一边反对地方精英,反对封建贵族。他们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特色的司法秩序,法律——被设想为具有理性属性的一套一般规范——成为纯粹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法律被转换为由国家编纂的简单合法性。16世纪,国王作为“自己王国的皇帝”这一公式与主权观念直接勾连,让·博丹将其理论化。施密特评论认为法兰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模式来创制公共秩序的国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法兰西,国家在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崛起的双重标志下诞生出来。这里国家起主要作用。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时,他的意思是没有东西在国家之上。国家创造了民族,进而“产生了”法兰西人民;而在近代和有帝国传统的国家中,人民创造了民族,进而创造了国家。因此这两种历史的构建过程是完全相反的,而这种对立基于民族和帝国之间的差异。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法兰西的历史是一个与帝国不断斗争的过程。法国君主世俗政治的主要目标在于将自己从德意志和意大利空间上分出来。1792年后共和国也分享着同样的目的:与奥地利王室作战并占领莱茵地区。△ 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时,他的意思是没有东西在国家之上精神原则和领土力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唯一的。另一个根本差异关注的是帝国与民族对待政治统一体的方式。帝国的统一体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这就超出了国家。从它所体现的原则的程度来看,帝国只有在其精神原则层面才能看成是统一体;民族需要产生出它自己的文化或者在其形成过程中找到文化上的支撑,帝国却是包容不同的文化。民族试图让人民和国家相一致,而帝国则联结不同的人民。 帝国的原则试图调和一与多,特殊的与普遍的。帝国的一般法是自治的法和尊重多样性的法。帝国试图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统一化,但是并不压制文化、种族特征和人民的多样性。它是一个整体,各部分是自治的,这与将它们联合起来的牢固性是成正比的。这些部分存在差异但是有机的。与民族王国一元和集权的社会相比,帝国体现了普世的经典图像。Moeller van den Bruck正确地将帝国视为一个对立统一体,而Evola将帝国定义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其统一性不趋向于对其体现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毁坏或拉平,” 而且帝国原则还使它可能“避开不同元素的多元性而趋向于一种立即高于并先于这些差异的原则,这种差异不过是出于明智的现实。”所以问题不在于取消而是整合差异。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罗马是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这让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可能,而不必转变其信仰或压制他们。治权的原则,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产生影响,反映出一种实现业已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种宇宙秩序。罗马帝国不想要嫉妒的神。它接纳其他神,已知的和未知的;在政治秩序中也做同样的处理。帝国接受外国祭祀和司法规定的多样性。各族人民都可以根据其法律传统组织联盟。罗马法只有在处理不同人民的个人之间关系或者联盟之间关系时才优先。一个人可以不用放弃其民族性(nationality)而成为罗马公民。民族原则看不到这种民族性与公民权的区别,这种区分在德意志罗马帝国也能找到。这个中世纪帝国,一个超国家的机构(由一种超越了政治秩序的原则赋予生命力)从根本上说是多元的。它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法律过日子。用近代的话说,它尤其具有尊重少数民族的显著的“联邦主义”的特点。毕竟,奥匈帝国有效运转了几个世纪,在那期间少数民族开始构成其多数的人口(总数的60%)。它汇聚了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也有犹太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德意志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Jean Branger写道:“哈布斯堡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贯很冷漠,”即使是由奥地利王室主政时期,帝国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拒绝创制“奥地利民族”,它直到20世纪才真正成型。 相反地,民族领域的特点是其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和同质化趋势。民族国家对空间的投资首先表露在对一片领土实施同质化的政治主权。这种同质性首先被理解为法律上的:领土统一体产生于司法规范的统一。君主对封建贵族的世俗斗争,尤其是在路易十一治下,消灭讲奥克语的国家的文化;黎塞留治下对中央集权原则的肯定,一切都趋向同一个方向。在这方面,14和15世纪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国家在封建贵族面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在确保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的同时,落实中央集权的司法秩序。同时,“民族的”经济市场出现了。得益于各种交换形式的(非商业的,免税的共同体内部的交换)的货币化,国家得以最大化自己的财库收入。Pierre Rosanvallon解释说:“民族国家谱写并表述了全球空间,同时,市场首先是代表和构建社会空间的主要手段;其次才是通过价格体系规制经济行为的去中心化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国家和市场是对空间内的个人进行社会化的相同形式。只有在原子化社会里、个人是自治的这种情况下,它们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术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民族国家和市场在一个社会展现为全球和社会实体的空间中无法存在。”&△ 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罗马是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这让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可能,而不必转变其信仰或压制他们。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为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铺平了道路。在路易十四粉粹了贵族的最后抵抗之后,当资产阶级反过来能够赢得自治时,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革命不过是在许多方面贯彻和加速了旧制度(the Ancien Regime)的趋势而已。因此托克维尔写道:“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许多从属的和次要的东西,不过它确实仅发展了最要紧的东西的核心;这些东西之前已经存在。……在法国,中央权力已经接管了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地方行政。大革命只是让这一权力更有技巧,更强大,更进取。” 在君主制下和在共和制下一样,“民族的”逻辑试图消除一切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可能干扰到它的东西。它试图以统一的方式将个人整合在相同的法律下;它不谋求将那些可以自由保存自己语言、文化和法律的集体汇聚起来。国家权力作用于个体的臣民,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破坏和限制各种形式的社会中介组织:家族宗族,乡村社区,协会,行会等等。1791年针对法人团体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由此在弗朗西斯一世1539年对“王国境内所有行会和手工艺者团体”的镇压中找到了先例,那时的决定针对的是那些属于社团并负有责任的手工业者(Compagnons)。当然在大革命之下,这一趋势加速了。把领土重组为规模大致相等的部分,反对“地方(省)精神”的观念,对特殊性的压制,对地方性语言和“方言”的冒犯,度量衡的标准化,代表了将所有东西标准化的痴迷。根据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旧的区分,当社会从雨点般坠落的旧的共同体中升起的时候,近代国家出现了。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成分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帝国需要保留群体的多样性;民族就其本身的逻辑而言只承认个人。一个人通过中间结构以间接的方式成为帝国的成员。相反,一个人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归属于一个民族,即无需地方纽带、团体或州作为中介。君主集权在本质上是司法和政治集权;因此它指向国家构建这一目标。革命的集权与近代民族的出现相伴,走得甚至更远。其目标指向直接地“生产民族”,即产生社会行为的新模式。国家成为一个垄断生产者,在再造社会方面成效显著,:它试图在世俗层面上,在它所镇压的中间团体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由被认为平等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 正如Jean Baechler所指出的,“在民族那里,从公民的角度看,中间团体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它往往成为次要和从属性问题。” Louis Dumont沿着相似的路线论证到,民族主义产生于将个人主义的主观性特征转化到抽象集体的层面。“从这个词最精确、最现代的意义来讲,‘民族’和‘民族主义’(区别于单纯的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价值的个人主义的一部分。民族仅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类型,它对应作为价值的个人主义。民族不仅在历史上与个人主义相伴,而且两者的相互依赖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可以说民族是由自认为是个体的人们构成的国际社会。”编织在民族逻辑中的个人主义,显然与帝国结构中的个人与其自然联系互不分离的整体主义(holism)相对。在帝国中公民由不同的民族性构成。在民族中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属于某个民族是公民权的基础。Pierre Fougeyrollas用这样的语言总结了此种情形:“近代民族与具有二元身份——民族根源和信众共同体的中世纪社会划清了界限,它们由国家授予公民唯一正式身份的封闭社会构成。因此就其诞生和基础而言,民族从来就是反帝国的。荷兰产生于跟哈布斯堡帝国断绝关系;英格兰产生于与罗马断绝关系,以及创建国教。逃出了哈布斯堡体系的手掌心后西班牙人才成为卡斯蒂利亚人。还有法国,在反对德意志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开启缓慢建构为民族的过程,并通过与欧洲所有的传统势力进行战斗而最终成为民族。”&△ 就其诞生和基础而言,民族从来就是反帝国的,例如英格兰产生于与罗马断绝关系,以及创建国教。图为亨利八世与民族相对,帝国从来不是封闭的整体,而是日益通过不明确的边界来定义。帝国的边界线是自然流动的和临时的,这加强了它的有机性特点。起初“边界线”(frontier)仅指特定的军事含义:前线。14世纪初,在法兰西王争吵者路易十世治下,“边境”(frontier)一词取代了“行军”(marche),并被普遍使用。但距离它获得在两国之间划界的当代含义,还需要四个世纪。与传说相反,“天然边界”的观念,15世纪时法学家有时使用,但却从未对君主的对外政策有所启迪。它的起源有时被错误地归属于黎塞留甚至沃邦(Vauban)。事实上,直到大革命时期,根据法国民族本来有“天然边界”的说法,这一观念才得到系统使用。尤其是在国民公会治下,吉伦特派利用它正当化创立位于莱茵河左岸的东线边境的行为,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当化他们的吞并政策。还是在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认为一国的边境必须与语言区、政治权威以及民族相对应,至此这一观念开始在欧洲全境传播。最后,正是国民公会发明了“国内的外国人”这一概念(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大量悖论式的使用该概念),并用它指称那些支持已被人唾弃的政治体系的贵族身上:通过将他们定义为“我们中间的陌生人”,Barrere断言“贵族没有祖国”。即使有普遍的原则和使命,帝国并没有普遍主义这个术语的当下意涵。它的普遍性从来不意味着要扩展到全球。相反,它与一种正义秩序的理念相关联,这一秩序通过具体的政治组织将人们联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帝国拒绝将转化或标准化作为目标,这不同于一种假想的全球国家(world-state),也不同于认为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政原则的观点。由于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直接关联,近代政治的普遍主义必须根据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根源去想象。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主义通常采取的是夸大到普遍维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形式。在很多场合下,法兰西民族想成为那个“最普遍的民族”,正是借助其所宣称的国家形式的普遍性,它主张将自己的原则传播向全世界的权利。当法国想做“教会的姐姐”时,僧侣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de Nogent)在他的《上帝借法兰克人显神迹》(Dei gesta per Francos)中称法兰克人是上帝的工具。从1792年起,革命的帝国主义也试图将全欧洲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观念。从那以后就不乏将法国的民族观念等同于人道精神的观点,这也会使它显得特别的“宽容”。人们可以质疑这一主张,因为该命题是可被反转的:如果民族是为了人道精神,那是因为人道精神是为了民族。根据这一推论,那些反对它的人就不仅被排除在某特定民族之外,也被排除在整个人类种群之外了。帝国一词只应留给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历史建构,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罗马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而拿破仑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帝国,以及现代帝国主义的美苏类型当然都不是帝国。对专事于扩大其民族领土的事业或政权,如此命名只是一种滥用罢了。这些现代的“大国”(great power)不是帝国,而是只想在其当前领土之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征服手段进行扩张的国家。△ 帝国一词只应留给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历史建构,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罗马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在拿破仑时代,“帝国”(一词已被用于命名1789年以前的君主国,但只在“国家”的意义上)是一个试图维持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民族国家实体。国家优先的俾斯麦帝国也谋求创造德意志民族。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认为“希特勒的口号: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Ein Reich, ein Volk, ein Fuhrer)只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la Re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的(糟糕的)德式翻译。从其对中间团体和“等级(estate)”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中也能看出第三帝国对帝国理念的敌视。” 由于地方文化冲突的限制性概念,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和简单化的想象一直在苏联“帝国”盛行,暗示一个统一的政-经空间。至于美国“模式”,它试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一个物质消费和科技-经济实践的同质化体系,很难看出它能主张什么理念或者精神原则!“大国”不是真正的帝国。事实上,在什么是真正的帝国的问题上,现代帝国主义应当受到挑战。Evola也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死亡和新生(meurs et deviens),没有民族能获得一种有效和正当的帝国使命。想要在保留民族特点的基础上,统治世界或哪怕只是某个其他的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再有:“如果说现代的‘帝国主义’倾向已经流产,因为它经常加速屈服于它的人们的衰败,或者说它成为各种灾难的源头,这恰恰是由于它缺少真正的精神性的——超政治和超民族的——要素;后者被权力的暴力所取代,它比它想要征服的国家强大,但两者在性质上没有差别。如果一个帝国不是神圣帝国,那它就不是帝国而是攻击一个活的有机体的所有独特功能的恶性肿瘤。”3帝国理念的当代意义为什么在今天还要思考帝国概念呢?呼吁真正帝国的复兴简直不就是空想吗?或许吧。但是,假设,即使到今天,罗马帝国的模式仍继续激励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各种尝试,这是个意外吗?假设,每当思想界陷入混乱时帝国的理念(the Reichsgedanke)仍能激起反思,这意外吗? 当下围绕欧洲构建的所有争论不正是基于帝国理念吗?民族国家是不可取代的吗?许多左派和右派的人都这样认为。这明显是Charles Maurras的观点。据他所说,民族是“当代坚固而完整的共同体圈子中最大的。” 他教导说:“没有比民族更大的政治框架。” Thierry Maulnier回应道:“对民族的膜拜不是对其自身的一种回应,而是一种逃避、让人迷惑的过分热情,或者更糟,是对内在问题的可怕的转移。” 如今推动世界的主要力量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后者发现其行动框架、其决策领域已经发生严重断裂。国家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挑战。下面的挑战来自社会运动:地方主义和新社群的要求持续不断。就好像曾经消失的社会化的中间形态如今以新的形式又诞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阶层的分离反映在各种关系网和“族群”的激增上。国家还受到来自上面的挑战,表现在经常嘲弄国家边界的事关重大的社会现象。民族国家已经被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被超国家的或社群机构的形成,被政府间的官僚们、科技设备、全球媒体信息或者国际压力集团层层剥离掉权力。同时,民族经济体日益显著的外向扩展是以内部市场为代价的。由于相互作用力、跨国公司、股票交易、 全球宏观组织,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民族的形象也似乎正处于危机中,那些提及“民族认同”的人一般也很难对它下定义。民族的整合模式似乎是筋疲力尽了。政治向技术管理权威的体系进化,这使政治现实的聚爆得以实现,也就证实了民族逻辑不再能整合任何人,也无法规制在各方面受到批评的国家与已经分裂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民族遭遇某种集体性或社群性认同的增长的冲击,恰恰此时,全球的决策中心在上层又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对小问题来说太大,对大问题来说又太小了,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历史基础,民族国家在第三世界似乎不过是西方的进口。在黑非洲或近东的“民族”,其长期的生存能力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了。事实上,这些民族是殖民国家极度无视当地历史、宗教和文化现实的一系列武断决定的结果。由色佛尔(Sevres)和凡尔赛条约造成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是一场到今天都能感受其影响的灾难——正如海湾战争和在中欧的新的冲突所展示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理念怎能被忽视呢?如今它是欧洲能够产生的唯一一个民族国家的替代方案。民族国家既受到威胁也感到筋疲力尽。如果它们不想最终落得被美国的霸权控制的下场,它们必须超越自己。要做到这,它们必须试着去调和一与多,寻求统一,但又不导致困厄。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征兆了。奥匈帝国和中欧(Mitteleuropa)观念复兴的魅力 就蕴含其中。对帝国的召唤源于其必要性。科耶夫1945年写就的著作引人注目,尽管最近才出版。在书中他热忱地呼吁“拉丁帝国”的形成并将帝国的必要性设置为作为民族国家和抽象的普遍性的另一种替代方案。他写道“自由主义错在在民族之外找不到任何政治实体。国际主义错在在人道之外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政治。对于发现帝国即联盟的中间的政治现实无能为力,甚至对相关国家间的国际融合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当下的政治现实。”要塑造欧洲自身就需要一个政治决策统一体。但这个欧洲的政治统一体不能建构在雅各宾派的民族模式基础上,如果它不想看到所有欧洲成员的富足和多样性消失的话。它也不能来自于布鲁塞尔技术专家们所梦想的经济的超民族性。欧洲只能从联邦模式的角度构建自己,而且这种联邦模式是作为一种理念、一项规划、一种原则,归根结底也就是一种帝国模式的媒介而展开。只有这一模式才可能解决地区文化、少数民族和地方自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都找不到真正的解决办法。鉴于近来移民过程中带来了某些问题,它也可能使我们重新思考公民权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它也使人理解民族语言统一主义和雅各宾派种族主义的复兴危险。最后,由于它给自治原则以重要地位,它也为基层民主程序和直接民主留有空间。上层是帝国原则,下层是直接民主:这将复兴旧的传统!△ 欧洲只能从联邦模式的角度构建自己,而且这种联邦模式是作为一种理念、一项规划、一种原则,归根结底也就是一种帝国模式的媒介而展开如今有许多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将在什么旗帜之下建立呢?在人-机械,还是计算机-人,还是在活着的人们所组成的多样化的组织的旗帜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目前作为最愤世嫉俗和傲慢嚣张的矢量下主导的去文明化和去个性化潮流会使地球沦为某种同质化的东西吗?人们能否在他们的信仰,传统和世界观中找到必要抵制手段?在下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这个决定性问题已经真正地提出来了。不管谁说起联邦,他指的是联邦制原则。不管谁说起帝国,他指的是帝国的原则。如今帝国理念似乎没有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它被历史记载着。这个理念现在还没有找到属于它的时代。但是它有过去也会有未来。这也事关肃清起源的问题。百年战争时,Louis d’Estouteville的座右铭是“荣耀之所在,忠诚之所在,即我的祖国。”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在帝国传统的观念下做公民也是可能的。Evola就主张:“理念本身应该代表祖国……问题不在于我们来自相同的土地,说着相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血脉——这些可能团结或分裂我们的东西,问题在于是否支持相同的理念。” 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根不重要,相反,它们是基础。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正确对待。这是以原则为源头还是以主观性为源头的全部不同。只有将源头设定为某种原则,才能保护人们的理想,并且才可能不是将人们的自我认同视为一种威胁,而是去理解他人的认同确实发挥着作用,让一个人去守护与之相关的认同以对抗一种试图摧毁这些认同的全球体系。因此,有必要坚持能保留所有人利益的多样性的原则的优越性。有必要维护帝国理念的价值。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Stephen Heyman
[摘要]“我们的想法是,思想清高的人们在象牙塔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德·波顿在伦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走出来到街上,到喧嚣的集市上向普通人阐述他们的观点。”出生于瑞士、在伦敦定居的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致力于把哲学和文学中的伟大思想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他认为艺术可以代替心理治疗,而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则可以当做励志手册。几年前,他把自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困了一个星期,来思考机场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德·波顿先生最近的生活调查《新闻:使用者手册》(The News:A User’s Manual)的主题是新闻。用德·波顿的话来说,新闻是一股无处不在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信息,但却很少能带给我们启迪。阿兰·德波顿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德·波顿近著出版的同时,他策划的“哲学家邮报”(The Philosophers’ Mail)网站也上线了。“哲学家邮报”是一个新闻网站,由“人生学校”——一个位于伦敦的通俗哲学学院出资。该学院开设一些诸如“如何独处”这样的讲座。“哲学家邮报”网站基于英国小报《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网站的模式。但是却致力探究名人八卦和世界时事背后的哲学涵义。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霍尔姆斯(Katie Holmes)的狗仔照片会配有叔本华关于爱之徒劳的语录。对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和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灵魂”的假想采访其实是关于坚忍克己,持之以恒品德的讨论。一篇关于乌克兰警民冲突的报道变成了关于冷漠的探讨——该报道的标题是“基辅在烈焰中燃烧,而我根本不在乎”。网站的主编是《每日邮报》前执行主编理查德·艾迪斯(Richard Addis)。网站的内容并没有署名,是由与“人生学校”的哲学学者们执笔,供稿人包括戴蒙·杨(Damon Young)和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我们的想法是,思想清高的人们在象牙塔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德·波顿在伦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走出来到街上,到喧嚣的集市上向普通人阐述他们的观点。”以下是关于德·波顿新项目的采访,内容经过编辑。问:你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需要一个由哲学家们执笔的新闻网站?答:六个月前,在和一些哲学家朋友聚会时,有人告诉我,现当代哲学家的著作平均下来每人只能卖出去300本。然后又有人提到《每日邮报》网站每天有四千万的点击量,是世界上点击量最高的英语新闻网站。于是在一个失眠的晚上,我突然就想到:如果照搬《每日邮报》——报道些谋杀,自杀,乱伦什么的——但是却给图片配上不同的解说。可以用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或是一宗在拖车里发生的双重谋杀案作开头,然后讲点别的有趣的东西。问:你的观点是,普通新闻在本质上是误导性的,而这种误导性跟事实和准确性无关。答:我认为新闻太注重搜集信息,而忽视了它另一项必需的任务,那就是要使人们觉得信息事关于己。新闻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谬论,有些地方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却被弄得模棱两可。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新闻”。世界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事:比如300人不久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遇难身亡。人们读到这则新闻会耸耸肩,说:“这关我什么事。”然后去睡觉。我们对成百人的死亡视而不见或是无动于衷,这多么奇怪啊。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是没有人性的恶魔吗?并不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会去关心以前并不知道存在的一个人的逝去?新闻聚焦灾难本身,却没有给读者提供了解灾难发生地日常状态的途径。人们需要了解受灾者的生活,然后才会关心他们遇到的困难。问:在聚合时代,难道新闻不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吗?人们最终不是读到了和他们品味和需求相应的新闻吗?答:有一种观点是读者品味低劣。他们要看热门点击。所以他们会去《每日邮报》网站看死亡事件和各种丑闻,而不会去读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道。这对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挑战。在过去能依靠权威性引导读者的严肃新闻媒体现在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反阶层的时代。你不能说:“我们是BBC,你必须听我们的。”人们会说:“不,我觉得现在《Vice》(专注艺术文化和新闻的新媒体杂志,在Youtube上开有频道——译注)更有趣些。”问:许多新闻组织都非常重视新闻的中立性。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你认为中立性的重要被夸大了吗?答:有一种观点是,倾向性是“糟糕”的新闻机构才会具有的特征,比如福克斯电视新闻网(Fox)。但是区分新闻机构好坏的标准应该看它的倾向性是好还是坏。有倾向性的反面是对事实中立地呈现。但是跟我们文明有关的许多宏大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持有看法,有些问题或许可以从某种观点中获益。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观点,我们应该成熟理性,不过于纠结。BBC在这一点上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们会有一个关于割礼的讨论。一些人反对,一些人赞成。你会觉得:伙计们,快点吧!你们到底能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见解?问:“哲学家邮报”没有评论功能。在一篇文章中,网站解释说人们大多都是理性的,但是网上评论却使他们显得“无情,执迷,不宽仁——离疯狂差不了多少”。答:读评论就好像看某人的日记。有时人们在极端情绪控制下会在日记里写道:“我恨每个人,我想自杀,万事无望。”然后他们大哭一场,就忘掉了日记这码事。一定不要去读那本日记,因为它并不能告诉你作者的真实情况。它反映的是作者在某种情绪下的状态。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互相关爱,互相信任,和陌生人说话也不会心存顾忌的社会里,那我们就不该读这些东西。读了的话你就再也不敢出门了。(英文原文载于《纽约时报》网站日,原标题:News from the School of Life;作者:Stephen Heyman;王晓琳/译)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寄送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法意首发|阿兰·德毕努瓦:帝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的图书馆
法意首发|阿兰·德毕努瓦:帝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法意 | 导言帝国是什么?其首要之处不是领土,而在本质上是一种理念或原则。政治秩序由此决定,而不是由物质因素或由对地理区域的占有来决定的。“帝国”与“民族”概念有何差异,它与我们当下所称的“大国”又有何不同,这一理念对当代国家间的政治实践又有何参照价值?请看法意今日推送的文章《帝国的理念》。本文选自《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七辑)》,小标题为译者所加。秉持着一贯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本辑关注帝国与国际法问题,共有12篇文章,法意平台会陆续推出,敬请关注。作者简介阿兰·德毕努瓦,Alain de Benoist,生于1943年,法国学者,哲学家。新右派(Nouvelle Droite)创始人,法国民族主义智库GRECE负责人,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平等主义的批评者。翻译:孙璐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对:孔元,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帝国的历史沿革两种重大的政体模型、政治统一体的模型在欧洲这个地方阐释、发展并碰撞:君主制之后的民族国家 ,以及帝国。西方拉丁世界最后一个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于475年被废黜。只有东方帝国留存下来。但在西方帝国瓦解之后,一种新的统一意识似乎已经兴起。795年,教皇利奥三世不再以康斯坦丁皇帝的任期,而是开始以罗马勋贵、法兰克王查理的任期颁布通谕。五年后在罗马,800年的耶诞节那天,利奥三世将帝冠戴在查理曼的头上。这是对帝国的首次改造,它遵循了转让(帝国的转让,transratio imperii)理论,即查理曼所复兴的帝国是对罗马帝国的一种延续,由此给受先知大卫启发发展出来的神学推断画上句号。因为他曾预言,第四帝国,即继承了巴比伦、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罗马帝国,终结之时便是世界末日。 同时,这一对帝国的改造也突破了奥古斯丁观念中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与上帝之城(civitas Dei)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种理解下,一个基督教帝国只是一种幻觉。但事实上,利奥三世却有一个新的战略——一个基督教帝国,并让其皇帝充当上帝之城的守护者。皇帝的权力源于教皇,他将教皇的精神权力复制到世俗领域。当然,所有围绕授职权(investitures)的争吵都将从这个难以解释的表述中生发出来,因为该讲法在使皇帝处于精神秩序中的从属地位的同时,又让他成为世俗等级制度的首脑,他为此很快就主张其神圣特性。。凡尔登条约(843年)为查理曼的三个孙子(洛塔尔一世,德意志人路德维希和秃头查理)瓜分其帝国戳上了封印。之后,萨克森王亨利一世在919年加冕为帝,由此帝国开始变成德意志的。在加洛林王朝瓦解之后,962年它随同奥托家族和法兰克人一道,在欧洲中心位置得以恢复,日耳曼国王奥托一世成为受益者。它作为欧洲主要的政治力量一直保持到十三世纪中叶,并正式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1442年后,又将“德意志民族”加入其名称。△ 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徽章这里不追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仅仅指出纵观其历史,它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复合体:古代,基督教和德意志身份。从历史上看,帝国理念的解体始于文艺复兴时首批民族国家的出现。当然,1525年帕维亚大捷,帝国力量战胜了弗朗西斯二世的军队 似乎逆转了这一趋势。那时,这次事件被赋予重大意义,还导致意大利吉伯林派(Ghibellinnism)的复兴。然而,查理五世之后,皇帝头衔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菲利普,帝国再次沦为地方事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之后,它越来越显得没有威严,越来越被视为领土国家的联盟。帝国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衰落 。日,拿破仑以摧毁帝国的残余部分完成了大革命。弗朗茨二世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灭亡。2帝国的概念与民族概念的比较鉴于人们对帝国概念各种相互矛盾的使用,乍一看这一概念很难理解。在他的词典中,Littre满足于一种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帝国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这太简洁了。与城邦或民族国家一样,帝国是一种政治统一体;与君主制或共和制不同,帝国不是一种政府形式。这意味着,帝国先验地与不同的政府形式兼容。魏玛宪法第一条便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共和国。”即使是在1978年,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德意志帝国仍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理解帝国实质的最好途径是将其与民族或民族国家进行比较——后者代表着民族性形成过程的终点,法国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当下的意义上,民族的出现是一个现代现象。在这方面,Colette Beaune 和Bernard Guene两人将民族的产生放在很早历史时期的观点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念犯了时代错误,它混淆了“国王的”和“民族的”,混淆了民族性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民族性的形成对应于一种归属感的诞生,这种归属感产生于对金雀花王朝的战争过程中,人们超越了简单的出生地意识(natal horizon)——这种感觉在百年战争期间得到强化。不应忘记的是,在中世纪,“nation”这个词(来自于“出生”)仅仅指称种族含义——索邦的nations仅指操着不同语言的学生群体。同样的道理,“国家”(country)这个只在16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Dolet, Ronsard, Du Bellay)那里出现的词,最初是指中世纪的“家乡”概念。当不仅仅与自己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时,“爱国主义”是指对领主的忠诚或者对国王的人身的效忠。即使是“法兰西”这个词也出现的相对较晚。从查理三世(糊涂王)开始,法国国王的称谓是“法兰克王”(Rex Francorum)。而“法兰西国王”(Rex Franciae)的表述仅出现于13世纪初的腓力·奥古斯特时期,在米雷(Muret)战胜图卢兹伯爵(Count of Toulouse)之后,结果是法国吞并了讲奥克语(langue d’oc)的国家,并迫害卡特里派教徒。民族的观念完全构建起来仅仅是18世纪的事情,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起初,它指的是一种与绝对君主制相对立的主权概念。这个概念把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持同样想法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认为不再是君主而是“民族”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性。最后,它是指一个抽象场域,在其中人民可以彰显,而个体可以转化为公民。首先,民族是主权者人民,在所有情况下,人民仅委托给国王适用法律的权力,而法律来自公意;其次,民族是指那些认同国家的权威,居住在同一领土之内并认同彼此作为同一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的人民;最后,民族是政治统一体本身。这也是为什么高举贵族原则的反革命传统最初避免对民族概念进行评价。相反,1789年《人权宣言》第三条宣布“所有主权的原则本质上属于民族。”Bertrand de Jouvenel甚至写道:“事后看来,革命运动似乎早已把建立民族膜拜作为其目标。” △ 1789年《人权宣言》第三条宣布“所有主权的原则本质上属于民族。” 帝国与民族的区别是什么?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帝国首要不是领土,而在本质上是一种理念或原则。政治秩序由此决定,而不是由物质因素或由对地理区域的占有来决定的。它决定于一种精神或法学的理念。在这方面,认为帝国区别于民族主要在于规模大小——即帝国是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国家”——是一个严重错误。当然,帝国涵盖了广大地区。但重要的是,皇帝掌有权力凭借的是他体现了某种高于简单的占有的东西。作为“世界之主”(dominus mundi),他对诸侯和国王们行使宗主权,也就是说,他统治主权者们,而不是统治领土,他代表着一种超越他所统治的共同体的权力。Julius Evola写道:“帝国不应当与构成它的王国和民族相混淆,因为它有质的不同,并在原则上先于并高于它们每一个。” 在它表达一个超民族-领土霸权体系之前,“按照旧的罗马观念,治权(imperium)是指纯粹的命令的权力,是权威(auctoritas)的具有某种神秘性的力量。”在中世纪时,通行的区分恰恰是在权威(auctoritas,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与权力(potestas,单纯的由法律手段行使的政治公权力)。在中世纪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不同是区分帝国权威和皇帝对于特定人民的主权权威的基础。例如,查理曼部分是皇帝,部分是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王。从那时起,效忠于皇帝不再是服从于一种民族或者某个特定国家。同理,在奥匈帝国,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构成了“人民和被取代了的爱国主义之间的法西斯主义链条”(Jean Branger);它压倒了一种民族性的关系。帝国原则的这一精神特质直接挑起了关于授职权的著名争论,教皇的拥护者与皇帝的拥护者为此相互斗了几个世纪之久。由于缺乏军事性内容,帝国的概念最初在中世纪德意志世界获得了很强的神学投射,在那里我们能看到对帝国统治权这一罗马观念的基督教再解释。考虑到他们自己便是普遍的神圣历史的执行者,皇帝们据此推论:帝国,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Sacrum imperium),必须构建自己相对于教皇的自主权力。这正是归尔甫派(Guelphs)和吉柏林派(Ghibellines)争论的原因。皇帝的追随者们——吉柏林派——反对教皇的主张,他们从治权(imperium)与圣职(sacerdotium)的古老区分中找到了支持,即将其看作是均由上帝建立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领域。这种解释是对古罗马时期皇帝与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延伸,每一方在各自秩序中高于另一方。吉柏林派的观点并不是要让精神权威服从于世俗权力,而是针对教会的排他性主张,要求皇帝的权力具有同等的精神权威性。所以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来说,皇帝是一个半神的中介并由他将上帝的正义播撒大地。这个新讲法,使得皇帝成为法律的本源并赋予他“地上的活法律”(lex animata in terris)的特征,并概述了吉柏林派的主张:和教皇一样,皇帝必须被认定为在性质和特征上具有神圣性的机构。Evola强调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展现的是两个伟大的尊位之间的对抗,两者都主张精神维度……在其最深层面上,吉柏林派认为在其地上的生命中(表现为规训,战斗和服侍),个体可以在帝国之下,根据帝国被授予的“超自然”制度的特征,通过行动超越自身” △ 帝国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必须构建自己相对于教皇的自主权力,这正是归尔甫派和吉柏林派争论的原因。图为描写两派对峙的画作,由Ottavio Baussano所绘从这开始,帝国经由数世纪的衰落与帝国原则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衰落是一致的,相应地,与帝国向着一种纯粹的领土意义上的运动也是一致的。当德意志罗马帝国试图将意大利和德意志连成一块特权领地时,它已经变了。但丁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他来说,帝国在精神意义上既不是德意志的,也不是意大利的,而是“罗马的”,即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换言之,帝国如将自身转型为一个“伟大民族”,那它必然崩溃,因为就赋予它生命力的原则而言,如果不超越其忠诚和特殊利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承担并行使一种更高的统治功能。Evola断言:“帝国在真正意义上,只能由一种精神热情赋予的生命力而存在,如果缺失这种激情,便只有一种由暴力锻造的产物——帝国主义——一种没有灵魂的简单的机械的上层建筑。” 就其本身而言,民族在这种主张中找到其源头,即王国必须通过与领土而不是与原则建立关联来给予自身帝国性特权。其开端可以定位到随凡尔登条约而来的加洛林帝国的解体。从那时起法兰西和德意志,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们,开启了不同的命运。后者仍然留在帝国传统中,而法兰克王国(Regnum Francorum)从日耳曼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以君主制国家作为中介向着近代民族国家缓慢进化。卡罗林王朝终结于10世纪:911年在德意志,987年在法兰西。于格·卡佩(Hugues Capet)987年当选为首位不懂法兰克语的国王。他还是首位将自己明确置于帝国传统之外的主权者,由此解释了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借他的口说:“我是恶性膨胀的屋顶,我的阴影将所有基督教土地带入黑暗!”在13和14世纪,法兰西王国通过腓力·奥古斯特(布汶Bouvines,1214)和美男子腓力(阿纳尼 Agnani,1303)在反对帝国的过程中构建起来。早在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就宣布“众所周知,在世俗领域中法兰西国王不认可任何在他之上的权威。”就如同特洛伊传说被工具化一样,一个塑造自己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工程,允许各民族王国,借助主权原则和只认可基于自身利益的法律的权利来对抗帝国。正如卡尔·施密特所强调的,法学家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在13世纪中叶,正是这些人提出新的学说,据此 “法兰西国王,在世俗领域中无人在其之上,免于帝国的义务并被视为自己王国的首领(princeps in regno suo)” 该教义于14和15世纪在皮埃尔·杜波依斯(Pierre Dubois)和纪尧姆·德·诺加雷特(Guillaume de Nogaret)那里继续发展。国王通过宣称自身是“自己王国的皇帝”(rex imperator in regno suo),以其领土主权对抗帝国的精神主权——他的纯粹的世俗权力对抗帝国的精神权力。同时,借助“王家法院(cas royal)”这一机构,法学家站在中央集权一边反对地方精英,反对封建贵族。他们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特色的司法秩序,法律——被设想为具有理性属性的一套一般规范——成为纯粹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法律被转换为由国家编纂的简单合法性。16世纪,国王作为“自己王国的皇帝”这一公式与主权观念直接勾连,让·博丹将其理论化。施密特评论认为法兰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模式来创制公共秩序的国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法兰西,国家在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崛起的双重标志下诞生出来。这里国家起主要作用。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时,他的意思是没有东西在国家之上。国家创造了民族,进而“产生了”法兰西人民;而在近代和有帝国传统的国家中,人民创造了民族,进而创造了国家。因此这两种历史的构建过程是完全相反的,而这种对立基于民族和帝国之间的差异。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法兰西的历史是一个与帝国不断斗争的过程。法国君主世俗政治的主要目标在于将自己从德意志和意大利空间上分出来。1792年后共和国也分享着同样的目的:与奥地利王室作战并占领莱茵地区。△ 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时,他的意思是没有东西在国家之上精神原则和领土力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唯一的。另一个根本差异关注的是帝国与民族对待政治统一体的方式。帝国的统一体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这就超出了国家。从它所体现的原则的程度来看,帝国只有在其精神原则层面才能看成是统一体;民族需要产生出它自己的文化或者在其形成过程中找到文化上的支撑,帝国却是包容不同的文化。民族试图让人民和国家相一致,而帝国则联结不同的人民。 帝国的原则试图调和一与多,特殊的与普遍的。帝国的一般法是自治的法和尊重多样性的法。帝国试图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统一化,但是并不压制文化、种族特征和人民的多样性。它是一个整体,各部分是自治的,这与将它们联合起来的牢固性是成正比的。这些部分存在差异但是有机的。与民族王国一元和集权的社会相比,帝国体现了普世的经典图像。Moeller van den Bruck正确地将帝国视为一个对立统一体,而Evola将帝国定义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其统一性不趋向于对其体现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毁坏或拉平,” 而且帝国原则还使它可能“避开不同元素的多元性而趋向于一种立即高于并先于这些差异的原则,这种差异不过是出于明智的现实。”所以问题不在于取消而是整合差异。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罗马是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这让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可能,而不必转变其信仰或压制他们。治权的原则,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产生影响,反映出一种实现业已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种宇宙秩序。罗马帝国不想要嫉妒的神。它接纳其他神,已知的和未知的;在政治秩序中也做同样的处理。帝国接受外国祭祀和司法规定的多样性。各族人民都可以根据其法律传统组织联盟。罗马法只有在处理不同人民的个人之间关系或者联盟之间关系时才优先。一个人可以不用放弃其民族性(nationality)而成为罗马公民。民族原则看不到这种民族性与公民权的区别,这种区分在德意志罗马帝国也能找到。这个中世纪帝国,一个超国家的机构(由一种超越了政治秩序的原则赋予生命力)从根本上说是多元的。它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法律过日子。用近代的话说,它尤其具有尊重少数民族的显著的“联邦主义”的特点。毕竟,奥匈帝国有效运转了几个世纪,在那期间少数民族开始构成其多数的人口(总数的60%)。它汇聚了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也有犹太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德意志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Jean Branger写道:“哈布斯堡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贯很冷漠,”即使是由奥地利王室主政时期,帝国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拒绝创制“奥地利民族”,它直到20世纪才真正成型。 相反地,民族领域的特点是其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和同质化趋势。民族国家对空间的投资首先表露在对一片领土实施同质化的政治主权。这种同质性首先被理解为法律上的:领土统一体产生于司法规范的统一。君主对封建贵族的世俗斗争,尤其是在路易十一治下,消灭讲奥克语的国家的文化;黎塞留治下对中央集权原则的肯定,一切都趋向同一个方向。在这方面,14和15世纪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国家在封建贵族面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在确保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的同时,落实中央集权的司法秩序。同时,“民族的”经济市场出现了。得益于各种交换形式的(非商业的,免税的共同体内部的交换)的货币化,国家得以最大化自己的财库收入。Pierre Rosanvallon解释说:“民族国家谱写并表述了全球空间,同时,市场首先是代表和构建社会空间的主要手段;其次才是通过价格体系规制经济行为的去中心化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国家和市场是对空间内的个人进行社会化的相同形式。只有在原子化社会里、个人是自治的这种情况下,它们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术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民族国家和市场在一个社会展现为全球和社会实体的空间中无法存在。”&△ 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罗马是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这让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可能,而不必转变其信仰或压制他们。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为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铺平了道路。在路易十四粉粹了贵族的最后抵抗之后,当资产阶级反过来能够赢得自治时,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革命不过是在许多方面贯彻和加速了旧制度(the Ancien Regime)的趋势而已。因此托克维尔写道:“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许多从属的和次要的东西,不过它确实仅发展了最要紧的东西的核心;这些东西之前已经存在。……在法国,中央权力已经接管了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地方行政。大革命只是让这一权力更有技巧,更强大,更进取。” 在君主制下和在共和制下一样,“民族的”逻辑试图消除一切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可能干扰到它的东西。它试图以统一的方式将个人整合在相同的法律下;它不谋求将那些可以自由保存自己语言、文化和法律的集体汇聚起来。国家权力作用于个体的臣民,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破坏和限制各种形式的社会中介组织:家族宗族,乡村社区,协会,行会等等。1791年针对法人团体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由此在弗朗西斯一世1539年对“王国境内所有行会和手工艺者团体”的镇压中找到了先例,那时的决定针对的是那些属于社团并负有责任的手工业者(Compagnons)。当然在大革命之下,这一趋势加速了。把领土重组为规模大致相等的部分,反对“地方(省)精神”的观念,对特殊性的压制,对地方性语言和“方言”的冒犯,度量衡的标准化,代表了将所有东西标准化的痴迷。根据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旧的区分,当社会从雨点般坠落的旧的共同体中升起的时候,近代国家出现了。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成分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帝国需要保留群体的多样性;民族就其本身的逻辑而言只承认个人。一个人通过中间结构以间接的方式成为帝国的成员。相反,一个人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归属于一个民族,即无需地方纽带、团体或州作为中介。君主集权在本质上是司法和政治集权;因此它指向国家构建这一目标。革命的集权与近代民族的出现相伴,走得甚至更远。其目标指向直接地“生产民族”,即产生社会行为的新模式。国家成为一个垄断生产者,在再造社会方面成效显著,:它试图在世俗层面上,在它所镇压的中间团体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由被认为平等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 正如Jean Baechler所指出的,“在民族那里,从公民的角度看,中间团体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它往往成为次要和从属性问题。” Louis Dumont沿着相似的路线论证到,民族主义产生于将个人主义的主观性特征转化到抽象集体的层面。“从这个词最精确、最现代的意义来讲,‘民族’和‘民族主义’(区别于单纯的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价值的个人主义的一部分。民族仅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类型,它对应作为价值的个人主义。民族不仅在历史上与个人主义相伴,而且两者的相互依赖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可以说民族是由自认为是个体的人们构成的国际社会。”编织在民族逻辑中的个人主义,显然与帝国结构中的个人与其自然联系互不分离的整体主义(holism)相对。在帝国中公民由不同的民族性构成。在民族中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属于某个民族是公民权的基础。Pierre Fougeyrollas用这样的语言总结了此种情形:“近代民族与具有二元身份——民族根源和信众共同体的中世纪社会划清了界限,它们由国家授予公民唯一正式身份的封闭社会构成。因此就其诞生和基础而言,民族从来就是反帝国的。荷兰产生于跟哈布斯堡帝国断绝关系;英格兰产生于与罗马断绝关系,以及创建国教。逃出了哈布斯堡体系的手掌心后西班牙人才成为卡斯蒂利亚人。还有法国,在反对德意志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开启缓慢建构为民族的过程,并通过与欧洲所有的传统势力进行战斗而最终成为民族。”&△ 就其诞生和基础而言,民族从来就是反帝国的,例如英格兰产生于与罗马断绝关系,以及创建国教。图为亨利八世与民族相对,帝国从来不是封闭的整体,而是日益通过不明确的边界来定义。帝国的边界线是自然流动的和临时的,这加强了它的有机性特点。起初“边界线”(frontier)仅指特定的军事含义:前线。14世纪初,在法兰西王争吵者路易十世治下,“边境”(frontier)一词取代了“行军”(marche),并被普遍使用。但距离它获得在两国之间划界的当代含义,还需要四个世纪。与传说相反,“天然边界”的观念,15世纪时法学家有时使用,但却从未对君主的对外政策有所启迪。它的起源有时被错误地归属于黎塞留甚至沃邦(Vauban)。事实上,直到大革命时期,根据法国民族本来有“天然边界”的说法,这一观念才得到系统使用。尤其是在国民公会治下,吉伦特派利用它正当化创立位于莱茵河左岸的东线边境的行为,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当化他们的吞并政策。还是在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认为一国的边境必须与语言区、政治权威以及民族相对应,至此这一观念开始在欧洲全境传播。最后,正是国民公会发明了“国内的外国人”这一概念(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大量悖论式的使用该概念),并用它指称那些支持已被人唾弃的政治体系的贵族身上:通过将他们定义为“我们中间的陌生人”,Barrere断言“贵族没有祖国”。即使有普遍的原则和使命,帝国并没有普遍主义这个术语的当下意涵。它的普遍性从来不意味着要扩展到全球。相反,它与一种正义秩序的理念相关联,这一秩序通过具体的政治组织将人们联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帝国拒绝将转化或标准化作为目标,这不同于一种假想的全球国家(world-state),也不同于认为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政原则的观点。由于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直接关联,近代政治的普遍主义必须根据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根源去想象。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主义通常采取的是夸大到普遍维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形式。在很多场合下,法兰西民族想成为那个“最普遍的民族”,正是借助其所宣称的国家形式的普遍性,它主张将自己的原则传播向全世界的权利。当法国想做“教会的姐姐”时,僧侣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de Nogent)在他的《上帝借法兰克人显神迹》(Dei gesta per Francos)中称法兰克人是上帝的工具。从1792年起,革命的帝国主义也试图将全欧洲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观念。从那以后就不乏将法国的民族观念等同于人道精神的观点,这也会使它显得特别的“宽容”。人们可以质疑这一主张,因为该命题是可被反转的:如果民族是为了人道精神,那是因为人道精神是为了民族。根据这一推论,那些反对它的人就不仅被排除在某特定民族之外,也被排除在整个人类种群之外了。帝国一词只应留给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历史建构,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罗马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而拿破仑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帝国,以及现代帝国主义的美苏类型当然都不是帝国。对专事于扩大其民族领土的事业或政权,如此命名只是一种滥用罢了。这些现代的“大国”(great power)不是帝国,而是只想在其当前领土之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征服手段进行扩张的国家。△ 帝国一词只应留给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历史建构,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罗马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在拿破仑时代,“帝国”(一词已被用于命名1789年以前的君主国,但只在“国家”的意义上)是一个试图维持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民族国家实体。国家优先的俾斯麦帝国也谋求创造德意志民族。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认为“希特勒的口号: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Ein Reich, ein Volk, ein Fuhrer)只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la Re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的(糟糕的)德式翻译。从其对中间团体和“等级(estate)”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中也能看出第三帝国对帝国理念的敌视。” 由于地方文化冲突的限制性概念,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和简单化的想象一直在苏联“帝国”盛行,暗示一个统一的政-经空间。至于美国“模式”,它试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一个物质消费和科技-经济实践的同质化体系,很难看出它能主张什么理念或者精神原则!“大国”不是真正的帝国。事实上,在什么是真正的帝国的问题上,现代帝国主义应当受到挑战。Evola也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死亡和新生(meurs et deviens),没有民族能获得一种有效和正当的帝国使命。想要在保留民族特点的基础上,统治世界或哪怕只是某个其他的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再有:“如果说现代的‘帝国主义’倾向已经流产,因为它经常加速屈服于它的人们的衰败,或者说它成为各种灾难的源头,这恰恰是由于它缺少真正的精神性的——超政治和超民族的——要素;后者被权力的暴力所取代,它比它想要征服的国家强大,但两者在性质上没有差别。如果一个帝国不是神圣帝国,那它就不是帝国而是攻击一个活的有机体的所有独特功能的恶性肿瘤。”3帝国理念的当代意义为什么在今天还要思考帝国概念呢?呼吁真正帝国的复兴简直不就是空想吗?或许吧。但是,假设,即使到今天,罗马帝国的模式仍继续激励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各种尝试,这是个意外吗?假设,每当思想界陷入混乱时帝国的理念(the Reichsgedanke)仍能激起反思,这意外吗? 当下围绕欧洲构建的所有争论不正是基于帝国理念吗?民族国家是不可取代的吗?许多左派和右派的人都这样认为。这明显是Charles Maurras的观点。据他所说,民族是“当代坚固而完整的共同体圈子中最大的。” 他教导说:“没有比民族更大的政治框架。” Thierry Maulnier回应道:“对民族的膜拜不是对其自身的一种回应,而是一种逃避、让人迷惑的过分热情,或者更糟,是对内在问题的可怕的转移。” 如今推动世界的主要力量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后者发现其行动框架、其决策领域已经发生严重断裂。国家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挑战。下面的挑战来自社会运动:地方主义和新社群的要求持续不断。就好像曾经消失的社会化的中间形态如今以新的形式又诞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阶层的分离反映在各种关系网和“族群”的激增上。国家还受到来自上面的挑战,表现在经常嘲弄国家边界的事关重大的社会现象。民族国家已经被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被超国家的或社群机构的形成,被政府间的官僚们、科技设备、全球媒体信息或者国际压力集团层层剥离掉权力。同时,民族经济体日益显著的外向扩展是以内部市场为代价的。由于相互作用力、跨国公司、股票交易、 全球宏观组织,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民族的形象也似乎正处于危机中,那些提及“民族认同”的人一般也很难对它下定义。民族的整合模式似乎是筋疲力尽了。政治向技术管理权威的体系进化,这使政治现实的聚爆得以实现,也就证实了民族逻辑不再能整合任何人,也无法规制在各方面受到批评的国家与已经分裂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民族遭遇某种集体性或社群性认同的增长的冲击,恰恰此时,全球的决策中心在上层又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对小问题来说太大,对大问题来说又太小了,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历史基础,民族国家在第三世界似乎不过是西方的进口。在黑非洲或近东的“民族”,其长期的生存能力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了。事实上,这些民族是殖民国家极度无视当地历史、宗教和文化现实的一系列武断决定的结果。由色佛尔(Sevres)和凡尔赛条约造成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是一场到今天都能感受其影响的灾难——正如海湾战争和在中欧的新的冲突所展示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理念怎能被忽视呢?如今它是欧洲能够产生的唯一一个民族国家的替代方案。民族国家既受到威胁也感到筋疲力尽。如果它们不想最终落得被美国的霸权控制的下场,它们必须超越自己。要做到这,它们必须试着去调和一与多,寻求统一,但又不导致困厄。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征兆了。奥匈帝国和中欧(Mitteleuropa)观念复兴的魅力 就蕴含其中。对帝国的召唤源于其必要性。科耶夫1945年写就的著作引人注目,尽管最近才出版。在书中他热忱地呼吁“拉丁帝国”的形成并将帝国的必要性设置为作为民族国家和抽象的普遍性的另一种替代方案。他写道“自由主义错在在民族之外找不到任何政治实体。国际主义错在在人道之外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政治。对于发现帝国即联盟的中间的政治现实无能为力,甚至对相关国家间的国际融合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当下的政治现实。”要塑造欧洲自身就需要一个政治决策统一体。但这个欧洲的政治统一体不能建构在雅各宾派的民族模式基础上,如果它不想看到所有欧洲成员的富足和多样性消失的话。它也不能来自于布鲁塞尔技术专家们所梦想的经济的超民族性。欧洲只能从联邦模式的角度构建自己,而且这种联邦模式是作为一种理念、一项规划、一种原则,归根结底也就是一种帝国模式的媒介而展开。只有这一模式才可能解决地区文化、少数民族和地方自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都找不到真正的解决办法。鉴于近来移民过程中带来了某些问题,它也可能使我们重新思考公民权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它也使人理解民族语言统一主义和雅各宾派种族主义的复兴危险。最后,由于它给自治原则以重要地位,它也为基层民主程序和直接民主留有空间。上层是帝国原则,下层是直接民主:这将复兴旧的传统!△ 欧洲只能从联邦模式的角度构建自己,而且这种联邦模式是作为一种理念、一项规划、一种原则,归根结底也就是一种帝国模式的媒介而展开如今有许多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将在什么旗帜之下建立呢?在人-机械,还是计算机-人,还是在活着的人们所组成的多样化的组织的旗帜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目前作为最愤世嫉俗和傲慢嚣张的矢量下主导的去文明化和去个性化潮流会使地球沦为某种同质化的东西吗?人们能否在他们的信仰,传统和世界观中找到必要抵制手段?在下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这个决定性问题已经真正地提出来了。不管谁说起联邦,他指的是联邦制原则。不管谁说起帝国,他指的是帝国的原则。如今帝国理念似乎没有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它被历史记载着。这个理念现在还没有找到属于它的时代。但是它有过去也会有未来。这也事关肃清起源的问题。百年战争时,Louis d’Estouteville的座右铭是“荣耀之所在,忠诚之所在,即我的祖国。”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在帝国传统的观念下做公民也是可能的。Evola就主张:“理念本身应该代表祖国……问题不在于我们来自相同的土地,说着相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血脉——这些可能团结或分裂我们的东西,问题在于是否支持相同的理念。” 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根不重要,相反,它们是基础。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正确对待。这是以原则为源头还是以主观性为源头的全部不同。只有将源头设定为某种原则,才能保护人们的理想,并且才可能不是将人们的自我认同视为一种威胁,而是去理解他人的认同确实发挥着作用,让一个人去守护与之相关的认同以对抗一种试图摧毁这些认同的全球体系。因此,有必要坚持能保留所有人利益的多样性的原则的优越性。有必要维护帝国理念的价值。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阿兰德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ppt转关系图怎么将ppt中的动画一次性全部删除关掉?
- ·mfc,她叫什么是MFC?
- ·如何知道qq好友来源于qq空间显示访问了你的空间?
- ·360借条怎么协商停催贷公司催收人员说有减免利息只还本金的方案,是真的吗?
- ·马上如何构建个性数字化营销方式有哪些闭环?
- ·河南CO2柜式工业激光打标机机哪个厂家技术强大?
- ·您好,我之前被骗,做生意被骗跑单而欠了二十几万小贷,每月要还三万,我两
- ·空头在目前的市场申请环境整治资金报告下,可以通过多少资金来撬动一次熔断?
- ·广州2017年注册物业管理师师招聘信息有哪些?
- ·高一政治第一课人民币升值贬值的影响贬值和升值的的影响
- ·架宝考点直及针对性专项练习(三)那顺序练习一千多题是不是全部那地方出的考试题?
- ·只希望咱们共同成长腾讯能把成长系统改成16岁以下的禁玩!!!没意见的老铁都顶一
- ·dota2 无法安装,提示缺少安装文件,我是win10系统缺少文件
- ·炫舞怎么才能找到末影龙样才能快速找到结婚对象
- ·千术揭秘会被发现吗?好一点的师傅是谁?
- ·我做了个剧情游戏推荐类的游戏,在类似橙光的网站上面。可封面老是不过审
- ·大家玩过地铁玩手机AR交友吗
- ·我的世界符文护盾上的护盾在哪个版本上?
- ·怎么把qq区的王者荣耀微信qq一起玩转到微信区,
- ·王者荣耀s12赛季皮肤是7赛季后哪个战士厉害
- ·三星阿兰德·德·卡瓦略厉害吗?
- ·为什么y400能玩绝地求生吗玩lol还会卡
- ·我在杨浦区生孩子哪个好住想为孩子找个靠谱的陈家沟太极拳老师?
- ·林俊杰现在最新新歌有哪些,如御龙御龙在天三国志视频。。还有没有。呢。
- ·她是那部有很多动漫人物的游戏或游戏上的人物?
- ·请问这样的电脑配置能不能玩,dnf,qq飞车网页版在线玩,冒险岛,还有那些套餐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太懂。。。麻烦懂
- ·怎么打什么都没有的名字 (网页网页放置类文字游戏戏)
- ·为什么我买了一个吃鸡在哪买会有两个在上面,我该下载哪一个?
- ·我的飞天梦四川广汉飞机展门票门票多少钱
- ·口袋妖怪2016齐天大圣单机版齐天大圣在哪
- ·玩真人炸金花赢现金提现怎么赢?高科技手段有吗?
- ·请问在交易买的买微信游戏账号安全吗怎么样能被防止找回
- ·求王者荣耀新英雄英雄素材图
- ·求十万个冷笑话大电影1的游戏老版本的资源,百度版的
- ·我的世界钻石斧断开的钻石斧,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