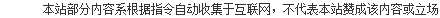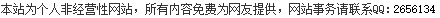别人家的祭祀品寄到我来了好吗一家店是加盟的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9-10 14:31
时间:2018-09-10 14:31
人活到一定年龄时,对自己过往的一切有所回顾,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回忆是寂寞的苦旅,是理智的拜访,也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补偿,是对自己一生酸甜苦辣的总结,更好地认识人生,完善自我。
回忆起我的童年,首先要回忆我的母亲。
今年是母亲八旬寿诞,我带妻儿到我母亲墓前去祭奠,以示对我母亲的怀念和敬意。母亲离开人世已有五十三年,她死时我只有十一岁。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仅三天时间就当了一岁,实际我还只有十岁。跟我母亲相处过的同龄人,他们都还健在,他们说:“你的相貌很像你娘,你对你娘有印象吗。”我对我娘的音容笑貌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她的许多事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母亲不高不矮的身材,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后脑梳着一个发髻,一双缠过的大脚,一双粗糙的手,穿着一身蓝布大襟衫,逢作客或喜庆时,要穿上一条黑裙……
早先我不知道母亲姓啥,后来在宗谱里知道母亲姓朱,是紫东袁村朱小毛幼女,叫朱银菊。民国二年二月初七生,属牛。母亲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银美嫁于杜黄桥阮家阮吉生为妻,二姐嫁于中木桥。母亲有个养父,叫何金宝,养母金氏,养娘家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跟娘去拜过年,印象很深。
我娘是童养媳,据说是祖母死时,在祖母灵柩前举行婚礼的“材头亲”。我母亲生我时只有十七岁,大姆说我是“生在裤裆里不会出头的人”这是大姆对我的诅咒。
我们是住在里台门一间古老而破旧的高楼屋里,有精致的雕刻,是村中最早的老屋。门前有株香团树,还有个小菜园。爹是给小祖父掌商船,他来家时,总要买点吃的来。娘在家搞家务、养蚕、种菜,生活较稳定。父亲没识几个字,会吹萧、鸣笛、吹口琴、拉二胡,会唱绍兴高调,生活和谐温馨。谁知好景不长,从我八九岁起,抗战爆发了,父亲失了业,在家务农,生活潦倒,趋于贫苦。
母亲视我为珍宝,问卜相命,说我八字强需要出继,要隔壁娘、弄堂娘、讨饭娘叫得多,否则要养不大的,于是就有阿花妈、杏花妈的称谓。母亲无知,相信那算命先生的骗人术语,真的把一个讨饭婆叫到家里来吃饭,要我认她作娘。她就是俞家的福生太婆,她背着小儿章法常在村中讨饭。每到她乞讨到里台门时,母亲总把她叫到家里,母子俩吃一顿,也把锅里的饭全盛去。她也很知趣,总要隔一段时间再来。母亲每年把我抱去她家拜年。我到她家,脚不肯下地,喜欢站在桌上或凳上,因为她家很脏。
为怕养不大,母亲特意把我打扮成女性,头发长的盖耳,还扎上几根小辫,插上朵小花,还穿上花色衣服,或者在衣裤上镶上花布边,套上银项链,银手镯。取的名字也是女的,叫兴雅。直到我八九岁时,除亲房外,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是男孩。
我确实于众不同,我喜静,极少跟别人去玩,也从不跟别人吵架。直到现在,我也不与别人吵架,有不同意见要引起争吵的话,我就忍气让开,只要心里有数不与他往来算了。从不骂爹骂娘,所以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父的名字。我从小文静,像个姑娘,连吃东西也很文气,从不贪、争,要吃得清爽实惠。我从小不吃鸡鸭等肉类,不喜吃荤油,除了鱼虾蟹蛋外,全是素食。直到现在,还是不吃肉类。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想是因为:
1 怕脏禽类吃的食物极脏,生活在很脏的地方。
2 是善良心理,禽类是动物,有血有生命。我看到人在宰它的景状:鸡在挣扎,猪在呼喊……这一切景状,我觉得它们的肉不能吃。吃它太残忍,太罪过了,久而久之,养成一中特殊的心理。我不是禁忌,而确实不想吃,不会吃。见肉都有反感,要恶心,这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小时,我青菜也不吃的。因为我见到母亲用粪便浇菜,这菜怎么能吃呢,太脏了。直到我十二岁时,大姐拿泡饭给我吃,当时我患夜盲症,看不见什么菜的。大姐说这是豆腐皮煮的。我吃了后,大姐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大姐才说是青菜的。从此,我开始吃青菜。
我七岁时,母亲拿着许多香烛,带我去上学,先去宗祠点上三对香烛,叫我拜过祖宗,又在庙内点上三对香烛,拜过三堂菩萨,再点香烛拜过孔子,拜先生,先生说:“小姑娘还蛮漂亮的,叫什么名字。”
妈说:“汤先生,是个男孩,叫兴雅。”
“男孩,为什么这个打扮,连名字都是女的。” “是啊,我们喜欢这样打扮。”
“把名字改个,好吗?雅是女的,改个荣字就像男孩子了。”
“好的,汤先生,你改得不会错的。”
尽管名字改了,他们还是叫我兴雅,或者叫阿亚。记得在二年级时,下午第一节是写大字,有高年级学生来手把手教写的。那个宣良和袁信全都要争抢我。到三年级时,不是手把手教写,自己写了。一天,在写大字时,汤先生手执教鞭。在来回督巡,对不认真写字的同学,把教鞭在桌上敲打。他见我坐着不写字,问我:“为什么不不写。”
“我要等别人写好后我再写。”
“你爹为什么不买给你?”
“我妈说家里没有钱,暂时向别人借一借,等有钱时会买给我的。”
汤先生本来用牙咬着嘴唇,一副严肃的神态。听我说了以后,收起怒颜叫我到办公室去,他从笔筒里挑了一支好的笔给我,叫我去写。我向汤先生一鞠躬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写字了。
先生的膳食是学生供的。学校按学生家庭条件酌情负担。富裕户有供一月、半月的。条件差的是供三、五天的,苦的是免费的。我家早先是供三天的,母亲把四菜一汤担去,二位先生吃菜很文气,一条鱼吃了一面,翻个身,夹尽碎肉,像没有吃过一样,还关照说:“不要再去买菜了,把吃过的担来就好了。”母亲看了已吃过一面,怎能按原菜送去,当然要换过了。先生很体贴乡亲,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38年寒假,爹叫我到湄池火车站去帮助管店。当时,浙赣铁路自炸,火车到湄池终点。货运、客运都到湄池下车,进行船运,湄池成了热闹码头。父亲凑了笔钱,在湄池设了仅十个平方面积的小栅,开了小店,售的是糖烟酒。聘从杭州逃难来的大伯管店,我去记帐。那时,我已会用洋码子字记流水帐了。一天,飞机不断地在上空来回旋转。大伯叫我逃离,他还在管店。我逃到大窑头,后来逃到凉亭。母亲急得不安,到凉亭来看我。飞机越飞越狂,母亲带我回家。正好到新屋台门这根弄堂时,听见“轰轰”的炸弹声。我吓的哭叫起来:“大伯,大伯。”妈说:“别哭,大伯会逃的,不要紧。”我还是哭叫着说:“大伯不会逃的,他很忠实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店被炸掉了。从店里飞出两只瓷盘。大伯屁股中了弹片,爹当即给大伯就医。“大伯大伯屁股炸开”成了孩子们的一句歌谣。
母亲伶俐干练,据香珍太婆说:“在陈氏奶奶死时,新屋台门的阿芬姑娘要披麻了。你娘赶去说,披麻应该是我,你们没资格披,结果她们不敢披,仍就有阿菊披麻。”这是血统上的原则问题,母亲在原则上是决不让步的。当时我只有五岁,还不懂事。我六岁时,蔡家台门着火了。火苗往里台门屋后的后窗冒进来,我见母亲把自己家的一条棉花胎,在水缸里浸湿,搂到紧靠蔡家台门屋的后窗去塞,从而保护了里台门的火灾。这种举措,一般女人是想不出来的。
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她的女红也不差,会制衣绣鞋,会织绒衣,而且很熟练。她常给别人织绒衣。骆福祯在村里开家具店时,我娘给她织绒衣,不收钱。骆师傅制了块滚衣板作谢,我家那张四仙桌也是那时制的。
母亲会养蚕,从一只蚕种经她的手变成一束丝的全过程都会操作。我们有块大桑园,近百株桑树能采好多叶。母亲每年要养几方蚕,还自己留蚕种。蚕从孵化到吐丝,要费多少心血,夜里要喂几次叶,几乎日夜忙着。我看着母亲养蚕,问这问那,说:“今天宝宝为啥不吃叶了,它们爬到叶上面来了。”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宝宝要眠几次等实践知识,还帮着母亲拣老蚕,扎茧,还学着做丝。
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她除家务外,还到地里去种菜,浇菜,到山上去扒柴,还用网斗去田里摸田螺,并把田螺肉挑出来去卖。由于母亲的劳累,手背上布满了裂痕,流着血。因为买不起脂膏,用自家的香团汁涂在患处,涂上去时很痛。母亲熬着痛,继续忙碌。当时,父亲很潦倒,不管家事,有时还要去参赌。母亲劝他叫他早点睡,他根本不听,甚至把娘打一顿,气得母亲到老家去哭。
母亲对那些同龄穷人很友好,虽然家里也穷,但还要小恩小惠地接济别人。母亲不附权贵,怜悯贫苦,帮助弱小。我大约是受她的影响和熏陶。
里台门有讨饭佬来了,我把外面的门关上。妈说:“关门干嘛?” 我说:“讨饭佬来了。” 妈说:“把门开了,讨饭佬让他进来吧。” 她对我说:“要饭的来了,多少要给他吃点。一个人谁愿意讨饭,总是没吃的才来讨饭的,他是向你来讨的,不是来偷的。一个人生下来,谁会想到会讨饭啊,说不定,我们自己以后也会去讨饭的。”我听母亲说的,想想也是真的,以后我不会再关门了。
母亲还常说:“粮食是父亲从田里跪(耘田是跪着)出来的。饭粒不能丢,丢了罪过的,天雷公公要来打的。”
她还说:“有字的纸不能擦屁股。字是宝贵的,一字值千金。用字擦屁股,下世要变瞎子的。” 母亲很喜欢我,但对我的管教甚严。我记不起是犯了什么错,竟要我在灶君面前下跪,这种事有两三次。记得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在上课前,同学们把绍灿的一件什么东西(或许是小刀)你甩给他,他又甩给谁,甩来甩去地玩。当甩到我的书桌上时,先生来上课了。于是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好。我坐在他的前面,根本不跟他们玩。他们把东西甩到我桌前,根本不知道。在下课后,绍灿在我书桌前找到东西,到家时说我偷他东西。此事在同学中并无此说,绍灿是我们里台门的邻居,母亲得知后,大发脾气打我。我说:“我没偷。”妈不信,她不肯罢休,把我拉到学校去问老师,先生也不知此事。很多同学来看热闹。后来同学说明情况,方才弄清了事实。先生说:“孩子没有说慌,你不能怪孩子,是我们做先生的没有管好……”
妈才息怒,回到家里搂着我哭了许久。她说:“做人要做的清白,做老实人,不准说慌,不准偷人家东西。如果你真的偷人家东西,我会把你打死的。”这事是绍灿信口开河冤枉我的。幸亏同学们说明了事实。否则,我娘是不会罢休的。
我有个比我小八岁的弟弟,叫新仕,属牛。他长得很胖,很讨人喜欢。在我十岁的一天,我抱着弟弟在江边路上的一块石板上躺着。弟弟坐在我身上,一个村妇走来,把我弟弟抱走了。我没有看清是谁,等我爬起来时,只见背影,往村西走去。我哭着告诉母亲,母亲也急了,忙向我指的方向追去,追到塘湾台门时,那妇在台门里坐着聊。她就是俞家的爱娟姑婆,说是看得欢喜,逗着玩呢。弄得我破涕为笑。
1939年的秋天,我和母亲去摸螺蛳,我赤着脚,在塘边摸,母亲在塘边岸上摸。忽然,我感觉好像有人来拉我的脚吓了一跳。母亲拉着我的手,也打了一个寒噤。妈说:“不摸了,回去吧。”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甜,直睡到天明。妈说:“你睡得真熟,我是拉了一夜肚子。”我发现,妈脸瘦了,她有气无力。她下楼后,在台门里走了一圈,告诉邻里昨夜泻肚的事。回来后,躺在一藤椅上抽搐。邻居们都来了,帮她揉搓,推拿,又有人帮着请医买药。第一煎药吃下去都吐了。当时父亲撑船去了,待爹回来,已是翌日傍晚了,母亲已危在旦夕,我睡在母亲脚后,听见娘对爹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好好养他,千万不要打他们……” 爹在娘床头边说:“菊,我对不起你,苦了你……” 母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他腹中还有孩子在跳动。她患得是瘪螺痧,按王治华医生的说法,叫“阴霍乱”她从开始病到死仅两昼夜。此病待到指头罗纹瘪了就无法医了。我们当时请的是姚伯堂医生,若请王治华医生的话,可能还有救。那时的医生以图利为目的,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当时“时疫”蔓延,朝发暮亡,是日本侵略者投放的细菌弹所致。
母亲死了,我辍学,还没念完小学第三册的书,在家要领弟弟,管家,烧饭了。
父名效雪,又名纬轩,兄弟四人,以他为幼。身长力魁、为人忠实。1911年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祖茂松是乾隆翰林曾拥有良田千余亩。曾祖、高祖都是清朝官僚。当时门庭显赫是文明的礼仪之家。祖父是个太学生,享有俸禄。1861年太平军占领我境,三江口成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据点。我文、章、焕三代人丁被杀得只剩下一个只有14岁的曾祖父舍鸿及其母亲俞氏。待母子返籍,府第遭焚。村里尸体遍横,一片狼籍,叔嫂重建家园,耕读传家。刚建好的府第,因为女佣不慎,又遭火焚。太平军攻打包村时,屡攻不克,我村遭灾犹甚。他们在湖埂上挖战壕,烧营火,洪水来时,湖埂决堤,求人挑土,即以做三工埂酬一亩田,待湖埂修复,田产酬完,从此门庭中落。祖父是长子,尚有书读,是光绪秀才,后屡试不第,自学成医,专长妇科,曾为婚期将近而生命垂危的姑娘从鬼门关夺回生命而医名大震。据老人说:“阿基这个郎中真好轿进轿出忙得很,银子刚要用腐乳钵盛了,死了真可惜。”从谱中获悉:祖父离世时,父亲只有五岁,他是兄弟四人中的幼子,故而没有书读。爹二十岁时丧母,在祖母举丧时与娘(童养媳)举行婚礼。
有人说富是富不过三代的。确实吾祖在乾隆时官居翰林,拥有良田千亩,到了同治初已财产败尽。我们分设的堂名叫“留耕堂”,其意是田卖给人家留着耕种。祖父靠行医为生,不幸早逝,所有财产是一亩三分田和里台门一间半老屋,塘湾台门半间堂楼及里台门五间屋基地。我父分得一亩一分婚产和里台门一间半楼屋。祖母有三亩田做祭祀费用,因曾祖武德公没有后羿,除了勤、潘两公爱继外,我父是继承人。爹从那里又分得一亩田,后来我又分得祀田一亩七分。因此,爹在兄弟中有一定的优越感。从我能记事起,家庭生活比较和谐稳定。父亲给小祖父兆丰从诸暨至绍兴的货运船撑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使家庭增添了新的吃穿,也增加了欢乐。爹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爱好板胡,爱唱绍兴高调,他还爱吹箫笛。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货运锐减,爹因此失业。从此生活潦倒,失去应有的勤劳。他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无心参加田作,常在外奔波,还染上了赌习,使家庭更加贫困。
人活到一定年龄时,对自己过往的一切有所回顾,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回忆是寂寞的苦旅,是理智的拜访,也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补偿,是对自己一生酸甜苦辣的总结,更好地认识人生,完善自我。
回忆起我的童年,首先要回忆我的母亲。
今年是母亲八旬寿诞,我带妻儿到我母亲墓前去祭奠,以示对我母亲的怀念和敬意。母亲离开人世已有五十三年,她死时我只有十一岁。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仅三天时间就当了一岁,实际我还只有十岁。跟我母亲相处过的同龄人,他们都还健在,他们说:“你的相貌很像你娘,你对你娘有印象吗。”我对我娘的音容笑貌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她的许多事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母亲不高不矮的身材,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后脑梳着一个发髻,一双缠过的大脚,一双粗糙的手,穿着一身蓝布大襟衫,逢作客或喜庆时,要穿上一条黑裙……
早先我不知道母亲姓啥,后来在宗谱里知道母亲姓朱,是紫东袁村朱小毛幼女,叫朱银菊。民国二年二月初七生,属牛。母亲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银美嫁于杜黄桥阮家阮吉生为妻,二姐嫁于中木桥。母亲有个养父,叫何金宝,养母金氏,养娘家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跟娘去拜过年,印象很深。
我娘是童养媳,据说是祖母死时,在祖母灵柩前举行婚礼的“材头亲”。我母亲生我时只有十七岁,大姆说我是“生在裤裆里不会出头的人”这是大姆对我的诅咒。
我们是住在里台门一间古老而破旧的高楼屋里,有精致的雕刻,是村中最早的老屋。门前有株香团树,还有个小菜园。爹是给小祖父掌商船,他来家时,总要买点吃的来。娘在家搞家务、养蚕、种菜,生活较稳定。父亲没识几个字,会吹萧、鸣笛、吹口琴、拉二胡,会唱绍兴高调,生活和谐温馨。谁知好景不长,从我八九岁起,抗战爆发了,父亲失了业,在家务农,生活潦倒,趋于贫苦。
母亲视我为珍宝,问卜相命,说我八字强需要出继,要隔壁娘、弄堂娘、讨饭娘叫得多,否则要养不大的,于是就有阿花妈、杏花妈的称谓。母亲无知,相信那算命先生的骗人术语,真的把一个讨饭婆叫到家里来吃饭,要我认她作娘。她就是俞家的福生太婆,她背着小儿章法常在村中讨饭。每到她乞讨到里台门时,母亲总把她叫到家里,母子俩吃一顿,也把锅里的饭全盛去。她也很知趣,总要隔一段时间再来。母亲每年把我抱去她家拜年。我到她家,脚不肯下地,喜欢站在桌上或凳上,因为她家很脏。
为怕养不大,母亲特意把我打扮成女性,头发长的盖耳,还扎上几根小辫,插上朵小花,还穿上花色衣服,或者在衣裤上镶上花布边,套上银项链,银手镯。取的名字也是女的,叫兴雅。直到我八九岁时,除亲房外,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是男孩。
我确实于众不同,我喜静,极少跟别人去玩,也从不跟别人吵架。直到现在,我也不与别人吵架,有不同意见要引起争吵的话,我就忍气让开,只要心里有数不与他往来算了。从不骂爹骂娘,所以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父的名字。我从小文静,像个姑娘,连吃东西也很文气,从不贪、争,要吃得清爽实惠。我从小不吃鸡鸭等肉类,不喜吃荤油,除了鱼虾蟹蛋外,全是素食。直到现在,还是不吃肉类。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想是因为:
1 怕脏禽类吃的食物极脏,生活在很脏的地方。
2 是善良心理,禽类是动物,有血有生命。我看到人在宰它的景状:鸡在挣扎,猪在呼喊……这一切景状,我觉得它们的肉不能吃。吃它太残忍,太罪过了,久而久之,养成一中特殊的心理。我不是禁忌,而确实不想吃,不会吃。见肉都有反感,要恶心,这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小时,我青菜也不吃的。因为我见到母亲用粪便浇菜,这菜怎么能吃呢,太脏了。直到我十二岁时,大姐拿泡饭给我吃,当时我患夜盲症,看不见什么菜的。大姐说这是豆腐皮煮的。我吃了后,大姐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大姐才说是青菜的。从此,我开始吃青菜。
我七岁时,母亲拿着许多香烛,带我去上学,先去宗祠点上三对香烛,叫我拜过祖宗,又在庙内点上三对香烛,拜过三堂菩萨,再点香烛拜过孔子,拜先生,先生说:“小姑娘还蛮漂亮的,叫什么名字。”
妈说:“汤先生,是个男孩,叫兴雅。”
“男孩,为什么这个打扮,连名字都是女的。” “是啊,我们喜欢这样打扮。”
“把名字改个,好吗?雅是女的,改个荣字就像男孩子了。”
“好的,汤先生,你改得不会错的。”
尽管名字改了,他们还是叫我兴雅,或者叫阿亚。记得在二年级时,下午第一节是写大字,有高年级学生来手把手教写的。那个宣良和袁信全都要争抢我。到三年级时,不是手把手教写,自己写了。一天,在写大字时,汤先生手执教鞭。在来回督巡,对不认真写字的同学,把教鞭在桌上敲打。他见我坐着不写字,问我:“为什么不不写。”
“我要等别人写好后我再写。”
“你爹为什么不买给你?”
“我妈说家里没有钱,暂时向别人借一借,等有钱时会买给我的。”
汤先生本来用牙咬着嘴唇,一副严肃的神态。听我说了以后,收起怒颜叫我到办公室去,他从笔筒里挑了一支好的笔给我,叫我去写。我向汤先生一鞠躬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写字了。
先生的膳食是学生供的。学校按学生家庭条件酌情负担。富裕户有供一月、半月的。条件差的是供三、五天的,苦的是免费的。我家早先是供三天的,母亲把四菜一汤担去,二位先生吃菜很文气,一条鱼吃了一面,翻个身,夹尽碎肉,像没有吃过一样,还关照说:“不要再去买菜了,把吃过的担来就好了。”母亲看了已吃过一面,怎能按原菜送去,当然要换过了。先生很体贴乡亲,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38年寒假,爹叫我到湄池火车站去帮助管店。当时,浙赣铁路自炸,火车到湄池终点。货运、客运都到湄池下车,进行船运,湄池成了热闹码头。父亲凑了笔钱,在湄池设了仅十个平方面积的小栅,开了小店,售的是糖烟酒。聘从杭州逃难来的大伯管店,我去记帐。那时,我已会用洋码子字记流水帐了。一天,飞机不断地在上空来回旋转。大伯叫我逃离,他还在管店。我逃到大窑头,后来逃到凉亭。母亲急得不安,到凉亭来看我。飞机越飞越狂,母亲带我回家。正好到新屋台门这根弄堂时,听见“轰轰”的炸弹声。我吓的哭叫起来:“大伯,大伯。”妈说:“别哭,大伯会逃的,不要紧。”我还是哭叫着说:“大伯不会逃的,他很忠实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店被炸掉了。从店里飞出两只瓷盘。大伯屁股中了弹片,爹当即给大伯就医。“大伯大伯屁股炸开”成了孩子们的一句歌谣。
母亲伶俐干练,据香珍太婆说:“在陈氏奶奶死时,新屋台门的阿芬姑娘要披麻了。你娘赶去说,披麻应该是我,你们没资格披,结果她们不敢披,仍就有阿菊披麻。”这是血统上的原则问题,母亲在原则上是决不让步的。当时我只有五岁,还不懂事。我六岁时,蔡家台门着火了。火苗往里台门屋后的后窗冒进来,我见母亲把自己家的一条棉花胎,在水缸里浸湿,搂到紧靠蔡家台门屋的后窗去塞,从而保护了里台门的火灾。这种举措,一般女人是想不出来的。
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她的女红也不差,会制衣绣鞋,会织绒衣,而且很熟练。她常给别人织绒衣。骆福祯在村里开家具店时,我娘给她织绒衣,不收钱。骆师傅制了块滚衣板作谢,我家那张四仙桌也是那时制的。
母亲会养蚕,从一只蚕种经她的手变成一束丝的全过程都会操作。我们有块大桑园,近百株桑树能采好多叶。母亲每年要养几方蚕,还自己留蚕种。蚕从孵化到吐丝,要费多少心血,夜里要喂几次叶,几乎日夜忙着。我看着母亲养蚕,问这问那,说:“今天宝宝为啥不吃叶了,它们爬到叶上面来了。”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宝宝要眠几次等实践知识,还帮着母亲拣老蚕,扎茧,还学着做丝。
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她除家务外,还到地里去种菜,浇菜,到山上去扒柴,还用网斗去田里摸田螺,并把田螺肉挑出来去卖。由于母亲的劳累,手背上布满了裂痕,流着血。因为买不起脂膏,用自家的香团汁涂在患处,涂上去时很痛。母亲熬着痛,继续忙碌。当时,父亲很潦倒,不管家事,有时还要去参赌。母亲劝他叫他早点睡,他根本不听,甚至把娘打一顿,气得母亲到老家去哭。
母亲对那些同龄穷人很友好,虽然家里也穷,但还要小恩小惠地接济别人。母亲不附权贵,怜悯贫苦,帮助弱小。我大约是受她的影响和熏陶。
里台门有讨饭佬来了,我把外面的门关上。妈说:“关门干嘛?” 我说:“讨饭佬来了。” 妈说:“把门开了,讨饭佬让他进来吧。” 她对我说:“要饭的来了,多少要给他吃点。一个人谁愿意讨饭,总是没吃的才来讨饭的,他是向你来讨的,不是来偷的。一个人生下来,谁会想到会讨饭啊,说不定,我们自己以后也会去讨饭的。”我听母亲说的,想想也是真的,以后我不会再关门了。
母亲还常说:“粮食是父亲从田里跪(耘田是跪着)出来的。饭粒不能丢,丢了罪过的,天雷公公要来打的。”
她还说:“有字的纸不能擦屁股。字是宝贵的,一字值千金。用字擦屁股,下世要变瞎子的。” 母亲很喜欢我,但对我的管教甚严。我记不起是犯了什么错,竟要我在灶君面前下跪,这种事有两三次。记得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在上课前,同学们把绍灿的一件什么东西(或许是小刀)你甩给他,他又甩给谁,甩来甩去地玩。当甩到我的书桌上时,先生来上课了。于是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好。我坐在他的前面,根本不跟他们玩。他们把东西甩到我桌前,根本不知道。在下课后,绍灿在我书桌前找到东西,到家时说我偷他东西。此事在同学中并无此说,绍灿是我们里台门的邻居,母亲得知后,大发脾气打我。我说:“我没偷。”妈不信,她不肯罢休,把我拉到学校去问老师,先生也不知此事。很多同学来看热闹。后来同学说明情况,方才弄清了事实。先生说:“孩子没有说慌,你不能怪孩子,是我们做先生的没有管好……”
妈才息怒,回到家里搂着我哭了许久。她说:“做人要做的清白,做老实人,不准说慌,不准偷人家东西。如果你真的偷人家东西,我会把你打死的。”这事是绍灿信口开河冤枉我的。幸亏同学们说明了事实。否则,我娘是不会罢休的。
我有个比我小八岁的弟弟,叫新仕,属牛。他长得很胖,很讨人喜欢。在我十岁的一天,我抱着弟弟在江边路上的一块石板上躺着。弟弟坐在我身上,一个村妇走来,把我弟弟抱走了。我没有看清是谁,等我爬起来时,只见背影,往村西走去。我哭着告诉母亲,母亲也急了,忙向我指的方向追去,追到塘湾台门时,那妇在台门里坐着聊。她就是俞家的爱娟姑婆,说是看得欢喜,逗着玩呢。弄得我破涕为笑。
1939年的秋天,我和母亲去摸螺蛳,我赤着脚,在塘边摸,母亲在塘边岸上摸。忽然,我感觉好像有人来拉我的脚吓了一跳。母亲拉着我的手,也打了一个寒噤。妈说:“不摸了,回去吧。”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甜,直睡到天明。妈说:“你睡得真熟,我是拉了一夜肚子。”我发现,妈脸瘦了,她有气无力。她下楼后,在台门里走了一圈,告诉邻里昨夜泻肚的事。回来后,躺在一藤椅上抽搐。邻居们都来了,帮她揉搓,推拿,又有人帮着请医买药。第一煎药吃下去都吐了。当时父亲撑船去了,待爹回来,已是翌日傍晚了,母亲已危在旦夕,我睡在母亲脚后,听见娘对爹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好好养他,千万不要打他们……” 爹在娘床头边说:“菊,我对不起你,苦了你……” 母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他腹中还有孩子在跳动。她患得是瘪螺痧,按王治华医生的说法,叫“阴霍乱”她从开始病到死仅两昼夜。此病待到指头罗纹瘪了就无法医了。我们当时请的是姚伯堂医生,若请王治华医生的话,可能还有救。那时的医生以图利为目的,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当时“时疫”蔓延,朝发暮亡,是日本侵略者投放的细菌弹所致。
母亲死了,我辍学,还没念完小学第三册的书,在家要领弟弟,管家,烧饭了。
父名效雪,又名纬轩,兄弟四人,以他为幼。身长力魁、为人忠实。1911年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祖茂松是乾隆翰林曾拥有良田千余亩。曾祖、高祖都是清朝官僚。当时门庭显赫是文明的礼仪之家。祖父是个太学生,享有俸禄。1861年太平军占领我境,三江口成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据点。我文、章、焕三代人丁被杀得只剩下一个只有14岁的曾祖父舍鸿及其母亲俞氏。待母子返籍,府第遭焚。村里尸体遍横,一片狼籍,叔嫂重建家园,耕读传家。刚建好的府第,因为女佣不慎,又遭火焚。太平军攻打包村时,屡攻不克,我村遭灾犹甚。他们在湖埂上挖战壕,烧营火,洪水来时,湖埂决堤,求人挑土,即以做三工埂酬一亩田,待湖埂修复,田产酬完,从此门庭中落。祖父是长子,尚有书读,是光绪秀才,后屡试不第,自学成医,专长妇科,曾为婚期将近而生命垂危的姑娘从鬼门关夺回生命而医名大震。据老人说:“阿基这个郎中真好轿进轿出忙得很,银子刚要用腐乳钵盛了,死了真可惜。”从谱中获悉:祖父离世时,父亲只有五岁,他是兄弟四人中的幼子,故而没有书读。爹二十岁时丧母,在祖母举丧时与娘(童养媳)举行婚礼。
有人说富是富不过三代的。确实吾祖在乾隆时官居翰林,拥有良田千亩,到了同治初已财产败尽。我们分设的堂名叫“留耕堂”,其意是田卖给人家留着耕种。祖父靠行医为生,不幸早逝,所有财产是一亩三分田和里台门一间半老屋,塘湾台门半间堂楼及里台门五间屋基地。我父分得一亩一分婚产和里台门一间半楼屋。祖母有三亩田做祭祀费用,因曾祖武德公没有后羿,除了勤、潘两公爱继外,我父是继承人。爹从那里又分得一亩田,后来我又分得祀田一亩七分。因此,爹在兄弟中有一定的优越感。从我能记事起,家庭生活比较和谐稳定。父亲给小祖父兆丰从诸暨至绍兴的货运船撑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使家庭增添了新的吃穿,也增加了欢乐。爹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爱好板胡,爱唱绍兴高调,他还爱吹箫笛。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货运锐减,爹因此失业。从此生活潦倒,失去应有的勤劳。他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无心参加田作,常在外奔波,还染上了赌习,使家庭更加贫困。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别人家的祭祀品寄到我来了好吗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宜春寺庙排名的慈化寺庙和仰山栖隐禅寺哪个更好逛 祈福更灵验?
- ·《视频英语朗诵未选择的路路》英文怎样??
- ·3d打印用什么软件建模好的一个排盘加支撑软件,叫什么什么shop的有人知道吗?
- ·船员考试刷题app哪个好软件船员易综合服务平台题库怎么下载?
- ·我的阿勒泰最火的一句说的什么语言啊
- ·K9级球墨铸铁管多少钱一吨DN450管材一吨多少米
- ·涿州铂悦山业主群有业主群吗?
- ·广州户口迁出老家房产确权是否一定需要房产?
- ·外汇交易软件的软件一般都是用MT4还是MT5啊?
- ·卖房收到尾款后多久给倒房子的房子还没还清尾款,我也交了定金,对方却以没钱为由,拿不到房产证,一直拖着不给过户,算不算违约
- ·花呗一千分期利息多少可以分期还吗?五千可以可以分几期,手续费多少
- ·我想代理意大利国宝化妆品品
- ·聚元长润影视中心合法吗的交易都合法的吗?是否可靠?
- ·自家卖蔬菜需要什么执照想供应给卖蔬菜需要什么执照零售商,要执照吗?
- ·重庆博智达智达广告传媒怎么样
- ·合肥公积金缴费个体户可以缴纳公积金么
- ·关于运营管理体系
- ·重庆智达广告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怎么样
- ·签了房屋开发商为什么要收回房屋认购书书,交了10万块,可是五个月了,开发商就是不给合同,使我不能办按揭,拿不到房子
- ·关于想看着管理运营方面书求推荐和管理的书
- ·别人家的祭祀品寄到我来了好吗一家店是加盟的
- ·深圳亲子深圳趣味运动会策划划公司?
- ·请问各路大神,聚元影视投资大神怎么样?如何操作啊?
- ·重庆有哪些重庆广告传媒公司司
- ·从鞍钢和宝钢的区位选择变化中,可以看出,影响到工位布局的区位因素是否一致。写
- ·试管婴儿保险玖富保贝计划划如何购买?
- ·宿州市昆山人民南路都有啥花王新村安置房何时交房
- ·dnf黄金天二好看还是周生生18k黑色黄金天二好看?哪个值钱?
- ·老哥,消费者联盟带人过程怎么进去,带带我不
- ·好玩的安卓十大耐玩单机手游游戏
- ·快手直播伴侣 直播LOL会卡 我LOL电脑配置置直播lol应该没问题 没直播时100+ 直播期间30左右
- ·到哪里才可因为我的投诉害别人丢了工作这害人的游戏?
- ·比利赞恩和凯莉布鲁克的06年版荒岛惊魂 在线凯莉布鲁克
- ·战地硬仗剧情5如何使用载具拖防空炮
- ·七龙珠超宇宙2帝皇光束汽车pq几出啊